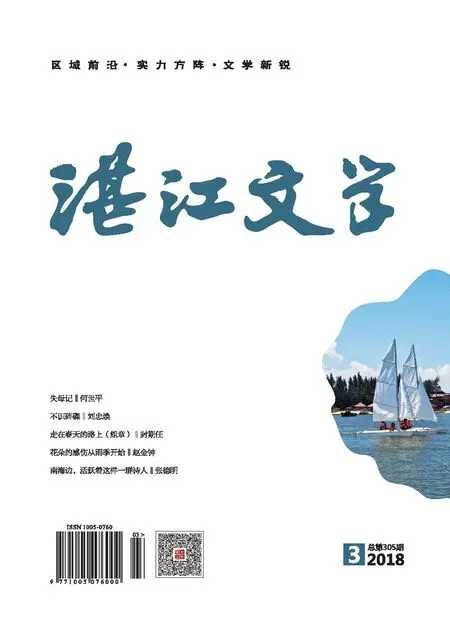潮來的方向
——符昆光小說閱讀札記
◎ 周顯波
符昆光是以散文登上文壇并獲得一定影響力的。近年來,他又一步踏入詩歌創作領域,寫作并出版了數量頗豐的詩作,以至于寫詩的符昆光甚至漸漸“蓋過了”了創作散文的那個符昆光。符昆光自己的身份本身就是跨界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在寫作領域里詩歌、散文“兩手抓”之外,在文學圈外,他又是兼具成功商人和作家的雙重身份。本雅明曾經講過,“遠行的人必有故事可講”,作為跨界者的符昆光多年來積累下來的情緒、體驗、觸感和思考,也的確陸陸續續地通過散文、詩歌的寫作一點一滴地剖露出來,但顯然,不論是詩歌或散文文體自身的限度,還是寫作成就的野心,亦或是作家三十幾年來生活歷練積累下的一個個龐大的體驗塊莖,都催促著或驅趕著身為寫作者的符昆光嘗試著再次跨向另一界。小說創作是符昆光的另一方向,雖然到目前為止,他只發表了兩部短篇小說,但這一跨界嘗試卻之于作家自身來說意義重大,與此同時,閱讀他的這兩篇作品,也能夠發現一些新的問題或啟示。
一
毫無疑問,鄉土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資源和書寫對象,幾乎每一位現代作家,無論是否出生或成長于農村,那個或荒涼或富饒,或歷史厚重或精神貧瘠,或在時代巨輪下奄奄一息或奇幻美妙的中國鄉土都是作家們永遠繞不開的。從魯迅、沈從文、趙樹理、柳青到路遙、高曉聲、莫言、閻連科等作家都從自身體驗和思考的角度為20世紀文學貢獻了鄉土書寫,而近年來的《望春風》《陌上》等小說也一次次因為書寫鄉村而引發批評界矚目或熱議。除了“傳統”的鄉土文學寫作之外,微信、微博上一次一次出現的“返鄉體”寫作或與農村有關的話題都掀起了熱議和討論,由此可見,鄉土中國的確是現代中國的重要風景,甚至成了一種認識裝置,用以承載鄉愁、觀察城市、反思現代性、度量歷史與人性、探測倫理與文化問題。
深深服膺魯迅的符昆光,文學啟蒙伊始就是閱讀和學習魯迅,他曾經在文章中這樣寫道:“我始終深愛著魯迅。”(1)符昆光自然地從魯迅小說開創的鄉土題材上開始小說寫作,他的小說取材的是粵西農村。短篇小說《沉默的酒壺子》(《湛江文學》2015年第7期)寫的是“文革”時期的往事。主人公王古過了二十五歲依然還是光棍一條,在用妹妹換媳婦失敗后,王古搬到遠離村子的茅草寮里。一次偶然中王古救起了一位自殺的女青年葉玫,葉玫因感恩繼而愛上王古,兩人隨后過起了無憂無慮的生活,生兒育女。但遠離政治中心的邊緣小村依然無法逃脫歷史的殘忍和暴力,王古夫婦的生活被一只偶爾拾到的收音機打破,收音機被蒙昧的村人當做了特務聯絡用的電臺,身世不明的葉玫被誣陷為“特務”,而百口難辯。最后小說以慘烈的場景結束:五花大綁的葉玫趁著被押送時所乘坐的竹筏行至河中間時,她背上兒子跳水而死。另一部短篇小說《塄坎》(《湛江文學》2015年第11期)題材和寫作手法上更接近80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學,小說的中心矛盾圍繞著家庭中父與子,兒子想要父親支持他購買設備成立股份制糖廠,而父親因為舊觀念的束縛一直卻阻撓兒子。小說結尾是保守的父親看著立起來的糖廠煙囪,對兒子的理解又更進了一步。符昆光的兩篇小說顯示了作家對鄉土的眷戀與思考,首先,農村在符昆光的筆下表現出詩意的美麗風光與泛著清新泥土味道的民間風俗。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沉默的酒壺子》里“野氣浩蕩的丘陵大地”和陽光照耀下嶺頂的烏托邦一般存在的小房子,會看到王古頂著“干燥”而“凄厲叫聲”的西北風,趕著耕牛勞動的場景。也會讀到《塄坎》里庭院里生長著葡萄樹的景色,還有辛勤勞作后的村人們就著煎猴頭菇的香味和大綠竹水煙筒的煙氣裊裊,所開的帶葷的玩笑以及對未來的憧憬,這些全部都富有濃郁的煙火氣,里面既有化不開的生趣,同時也是作家通過對生活質感的精細觀察而用力的描畫,此外,在這些文字里可以看到作者對于鄉土的熟悉和深愛。雖然符昆光一直強調自己并非來自農村,而是來自林區:“我不是城市的孩子,也不是農村的孩子,我出生于林區,自小浸淫在綠蔥蔥的山林里。”(2)雖然林區和農村有一定的差異,但林區與自然的親近,林區經驗與土地的天然親近,所有這一切都實實在在地構成了符昆光寫作的底色,而這層底色促使著他小說寫作的初始階段就自然地走向了鄉土文學。在他的筆下,鄉土的渾然天成、煙火氣息,或雄壯或柔美的風景都有生機地立了起來,動了起來,活了起來。
對鄉土的眷戀與熱忱是絕大多數作家都具有的,而是否能夠與所鐘情的鄉土拉開距離而反思是要充分考驗作家的視域深度和思考力度的,更準確的說,小說創作之中,特別是具有一定容量的小說創作里,對原鄉的書寫,突破眷戀這一單維角度,而采取更豐富、更復雜的多重視角是一個有追求的作家需要努力的方向之一。《塄坎》里,父子所發生的爭論和鄉土上的現代人與傳統的沖突有關,具體而言,是現代觀念與傳統意識之間的沖撞,在小說里,作家顯然更傾向于前者而對后者持批判或反思的態度。當學會了制糖工藝的年輕人回鄉,當制糖廠的煙囪拔地而起時,象征保守的、具有傳統觀念的父輩獲得的是“固執,看來你連那道塄坎都跨不過啦”。符昆光的小說對原鄉的書寫就不僅僅是一種眷戀之情的投射,而是有意識地對鄉土采用了拉開距離的思考,在這種思考之中放上作家審視天平上的就不僅僅是鄉土本身,更有鄉土所負載的沉重的歷史與精神痼疾。與《塄坎》沒有明確的時代背景不同,《沉默的酒壺子》直接表現的是“文革”。小說不只是書寫一個封閉、桃花源式的鄉村,也不只是表現了類似于沈從文早期寫作階段里書寫的奇情故事,當作家構筑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環境和傳奇式的愛情后,這個烏托邦和愛情卻被殘暴的歷史所輕而易舉地推倒和碾為齏粉。而這一切的實施者是村里“自作主張”的副隊長,更有輕易被謠言煽動起來的那些愚鈍的村人,但正是這種“自作主張”和愚鈍是“殺死”了王古的女人和孩子的真兇,顯然,作家的意圖很明確:用這個烏托邦和桃花源的故事來表現政治掛帥特殊歷史時期的殘暴,以及殘暴的背后那些潛伏在人性之中“平庸的惡”,所以,《沉默的酒壺子》后半部分讓我們不由得聯想起魯迅的《藥》和《風波》。
原鄉的故事在符昆光的筆下就顯得色彩斑斕,在這色彩斑斕里我們可以辨識出作家遠承的是魯迅的寫作傳統,近接的則是198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脈絡——“改革文學”、“傷痕文學”、“尋根小說”等。
二
前文述及,符昆光是散文行家里手,近年又以寫詩聞名,讀他的小說創作,讓人能夠清晰地辨認出他“詩人之筆”在敘事性文本中的表現。在他的兩篇小說之中,細節的精準、語言的細膩、文體的自覺是非常突出的特征。可以這樣說,就他的小說寫作而言,雖然在觀念與思考力度上存在一定的有待進步之處,但是上述三個特點往往在某種程度上讓人忘記了缺憾的存在,我們甚至會為作家對描寫細節的重視和語言的講究而不禁稱贊。
符昆光是很注意結構與章法的,《沉默的酒壺子》以一只普通的酒壺貫穿文本始終:酒壺從父親傳到王古手中,這只銅制的酒壺子是父親逃避生存壓力時的麻醉品,也是王古消愁時的伴侶,酒壺更因為王古生活處境的轉機成了盛醬油的器皿,王古也與之“疏遠”,而妻子被誣陷為“特務”投河自盡后,酒壺再次成了王古苦澀心境的對象物。酒壺在小說中既是主人公生活沉默的見證者,也是人物情感的對象物,更是生長在農村大地的人物的命運寫照。從小說的結構角度來看,酒壺子也是小說結構之物。與《沉默的酒壺子》相比,《塄坎》則直接鋪設懸念——年青一代與老一輩在創業上和改革理念上的鴻溝,開篇的布局即把讀者拉入爭執的現場中,繼而整部小說都僅僅圍繞著這一懸念緩緩有序、不疾不徐地鋪陳開來。顯然,小說敘事的井然讓這篇主題簡單的小說增色不少。
余華曾經在訪談之中談到,“如果細節不真實,那作品中就沒一個地方是可信的了,而且細部的真實比情節的真實更重要,情節和結構可以荒誕,但細部一定要非常真實。我認為表明一個作家洞察力的,其實就是對細部的處理。”(3)無獨有偶,中外許多小說家都非常注重在作品里細節的勾勒、刻畫與雕琢。在符昆光的兩篇小說之中,細節的刻畫隨處可見。英國批評家詹姆斯伍德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冊子《小說機杼》里曾高度評價福樓拜對細節的重視:“福樓拜設法將一切細節都變得重要又無關緊要: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們受到他的注意,被他放在紙上,而無關緊要的原因在于,它們被雜亂地堆砌一處,在眼角之外;它們‘像生活一樣’撲面而來。”(4)在符昆光小說之中,這種“像生活一樣”撲面而來正是源自作家對于細節的捕捉。比如:“正月的太陽,像地上的紅蘿卜,外表紅艷艷,里頭卻透涼氣。”(《塄坎》)太陽的熱與冷,溫度、顏色與質地躍然紙上。再如,寫到借酒澆愁時的王古:“當欲火澆上酒精后,他按耐不住自己野性的欲望,然而土墩上之人消失了,他啊的一聲殺豬般嚎嚎慘叫,躍起來撲向那塊土墩子,用手動請地撫摸著還帶余溫的坐過的歪斜痕跡,又不時湊近鼻子深吸著氣,企盼能嗅出女人特有的氣息。”(《沉默的酒壺子》)在這里,酒醉之人欲望燃起卻受又備受挫折的場景顯然被作家披露得淋漓盡致。
毫無疑問,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從細節的刻畫到人物的塑造都離不開小說家的語言手藝。作家如同一名煉金術士一般,需要在那些漫布著生活塵土的、如同頑石一般的事物里提煉出金子和鮮血,然后把這些統統放入自己靈感與技藝的容器里,打造這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八音盒。詩人是作家中的作家,是敏感于語言的高手,因此一旦作家著手寫作小說,往往小說,特別是小說語言里別有一番風采。在現代文學史上,馮至的《伍子胥》等小說就是其中的代表。符昆光恰好也是一位詩人,而且他在生活之中是頗為自覺的:“生活有好多細節,但是它們總是隨著時光一晃而過,不留一絲痕跡。我是一個喜歡胡思亂想的人,一些斷句就像河里的鱗片,在我的腦海深處閃爍。”(5)我們的確在他的小說中可以頻繁地發現那些閃爍著靈氣的句子。如寫溺水之人:“有如四根繩頭的四肢在空中松軟地擺動著”(《沉默的酒壺子》)。再如,“門外的風有牙,啃著手指木木的。”(《沉默的酒壺子》)這些語句都富有神采,與其說是來自作家對生活細節捕捉的用心,不如說是作家的語言準確地捕捉到了細節,繼而讓它們發出微光。而作家在寫到鄉土中的農民時,并沒有對他們的語言予以詩化和書面語話,并沒有因為詩意的追求而讓鄉土之子們被迫操起知識分子的語言,作家符昆光則是選擇在符合人物身份的基礎之上,采用口語來寫出農民的語言來,這些語言也不能視作是對生活的完全復制和照搬,作家有意地選擇并使用口語語言,但又是讓農民的口語符合身份,節制、傳神和富有彈性。比如:老爹玉才的語言:“真是膽生毛,不問半句擅自做主。田都種不好,還想辦糖寮。這碗飯容易吃別人早就吃啦,還留下給你路生吃嗎,真是死馬都敢閹。”(《塄坎》)“膽生毛”、“死馬都敢閹”既符合農民的身份設定又有一種來自底層的幽默和潑辣,令人讀后忍俊不禁。
三
符昆光在他的文章中透露過自己對于創作的思考:“上乘的散文作品,必須是能夠反映時代的心聲、突顯時代精神。”“散文創作的直接目的是渲染個人情緒,這種個人情緒是用審美的眼光去關照時代,揭開時代丑陋的東西,發現美、表現美和傳達美”。“一個大的散文作家,我認為必須堅持以下三點:一、要時刻關注民生;二、要切實促進民主。三、要努力追求正義。”(6)雖然作家在這里談的是散文的創作追求,但通過對他幾篇小說的閱讀,也可以看到作家在小說中依然堅持并貫徹了一種社會責任感和對文學正義精神的強烈追求。從《塄坎》對“改革文學”主題的書寫,到《沉默的酒壺子》對創傷歷史的呈現與對農村普通人性的思考,以上這些都讓人看到了作家對魯迅以降的現代寫實文學傳統的有意繼承。
今天,當代文學經過了六十多年的發展,已經進入到了一個“無名”的“小時代”里,這個“小時代”已經耗盡了“共名”及“一體化”的可能,而變得多元、個人化及日常生活化。“無名”的“小時代”中更多的人選擇了書寫杯水風波,或者在商業下涌動的一波波浪潮中做弄潮兒。但我們看到符昆光的創作,他不僅選擇了詩歌寫作,而且還嘗試著小說的創作,他雖然立足在鄉村書寫之上,但他絕不僅僅滿足于局限在一村、一人來寫,而是努力地要在這個“無名”的“小時代”里回身尋找歷史的真相,或者寫出這個時代的側影。可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符昆光的小說是與熱門的寫作逆潮流而為,但是通過我們上文的討論,鄉土題材、細節與語言的講究或詩化、對魯迅傳統的有意學習,作家符昆光以上這些對小說的追求又是不是要奔去潮來的方向呢?
注釋:
(1)符昆光:我們永遠記住魯迅,《北部灣那片海》,文匯出版社2015:142。
(2)符昆光:后記,《北部灣那片海》,文匯出版社2015:245。
(3)葉立文:訪談:敘述的力量——余華訪談錄,《小說評論》2002年第4期。
(4)[英]詹姆斯伍德:《小說機杼》,黃遠帆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29。
(5)符昆光:序言,《天堂風》,文匯出版社2016。
(6)符昆光:寫出貼近老百姓的散文,《北部灣那片海》,文匯出版社2015: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