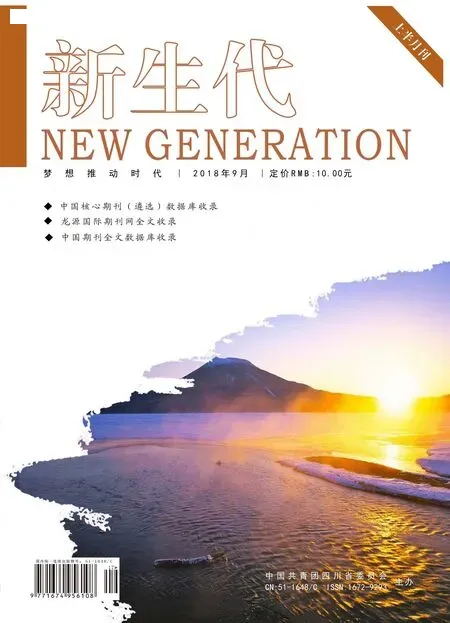“排除合理懷疑”在我國適用路徑探析
呂競一
指導老師:縱博 安徽財經大學法學院 安徽蚌埠 233030
我國“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是基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建立起來的,在學界有“客觀真實的證明標準”之稱。而“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則是普通法系中經典的“主觀性表述”類證明標準的代表。很長一段時間內,學界基本上認為此二者是水火不容的關系。隨著學者們對“排除合理懷疑”的認識逐漸增多,發現了“證據確實,充分”的局限性——片面追求證據完備的法定證據主義傳統。①“證據確實,充分”單一的強調了證明標準的客觀方面,沒有體現出“用證明標準來判斷”作為一個活動本身所具有主觀性——無法脫離司法人員的主觀認知。所以我國法律規范中所規定的“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與司法實踐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錯位。②而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基于事實無法還原的思想,從主觀上避開了客觀事實無法達成絕對認定的弊端,減輕了裁判者的心理負擔,并能夠給主觀判斷合理的空間,以達到主客觀相結合。隨著對兩者研究越來越多,終于,該標準一步步的進入了我國的法律文件中。早在2003年,江蘇省人民法院就頒布了《關于刑事審判證據和定案的若干意見(試行)》中規定了死刑應該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陸續還有其他幾個省份也做出了類似的規定,范圍也從死刑案件拓展為重大刑事案件,甚至所有刑事案件。而2008年江蘇省的另外一份關于證據的試行意見中,更是將“排除合理懷疑”做了進一步解釋:對死刑案件應做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否則不能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一切合理懷疑是指:
(一)現有證據不能完全證明案件事實;
(二)有現象表明某種影響案件真實性的情況可能存在,且不能排除;
(三)存在人們常識中很可能發生影響案件真實性的情況。③
2003年的證據意見得到了適用,并且遇到了解釋方面的問題,2008年的文件便走的更遠。④《法學家》 ,2012,1(5):52-67.]除了地方的規定之外,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印發《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兩個規定,里面明確指出,“證據與證據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⑤,而后面的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和最高院出具的司法解釋,實現了“排除合理懷疑”進入我國法律體系之中。一個來自英美法系的證明標準,演變成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一個規則,注定是一段漫長的歷程。
一、“排除合理懷疑”涵義理解問題分析
理解是適用的第一步,清晰的知道什么是“合理懷疑”,什么是“非合理懷疑”決定此規則能否發揮應有的效果。“排除合理懷疑”是將“證據確實、充分”的判斷最終落點于人的主觀方面要求達到的標準,即“對案件已經不存在合理的懷疑,形成內心確信”,“便于辦案人員把握”。⑥但同樣,由于主觀判斷的“因人而異”性,即使裁判者達成了十分確信的判斷,也可能讓人認為是缺乏根基、非理性、帶有不客觀成分的狀態。我們走訪基層法院調研此規則的適用,受訪的法官重點提出了這個問題。法官認為,合理懷疑的涵義是很難把握的,再加之沒有更嚴格的證據制度,排除合理懷疑的對象本身具有不確定性,法官和檢察官包括和律師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司法實踐中,基本不會直接利用該規則進行判斷,更不會將“‘排除合理懷疑’寫進判決書中”。“排除合理懷疑”只能作為查證事實的一個思路,或者說是中間階段,由思路引導的結果,最終還要證據證實。
之所以“合理懷疑”的程度難以把握,是因為與日常生活中的懷疑程度相混淆。學者認為,如果我們以日常生活中對于某一件事情的一般產生的懷疑程度為參照,會大大降低“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排除合理懷疑”是刑事訴訟中的證明標準,審判的結果與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權息息相關。由于“合理懷疑”沒有合適的定義,甚至根本就很難定義,同樣的案件證據和陳述,不同的判斷者可能有不同的結論,生性敏感的人認為不足以排除合理懷疑,相反,頭腦簡單干練的人可能覺得已經足夠。如果陪審員或者審判人員在審理案件事實時因對“排除合理懷疑”的把握度不夠,不自覺中降低至日常生活中產生的懷疑一般程度,在個案中是對犯罪嫌疑人的不公平對待的表現,是與刑事訴訟中保障人權的理念相違背。其他國家在“排除合理懷疑”的定義方面做出的實踐千差萬別,學界觀點莫衷一是,可見其難。我國向來十分善于“集之大成”,關于此規則的定義問題,可以從吸收其他國家實踐中適用最廣泛的幾種定義中取其精華,編做解釋,為“排除合理懷疑”的判斷創造一個統一模式,以緩解涵義理解問題。
二、“排除合理懷疑”適用階段及適用主體“專業化”分析
明確“排除合理懷疑”適用階段有助于進一步發揮該規則的作用。我國的證明標準,全面適用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立案,偵查,起訴,審判等都通過同一個證明標準來衡量。而在英美法系,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程度的證明標準,而“排除合理懷疑”作為高標準只適用于審判階段。雖然實踐中,司法人員會心照不宣地使用裁量權區分不同階段的證明標準,但其確實存在邏輯上的無法解釋之處。如果任何階段都要達到同樣的證明程度才可以進行下去,也就是說,只要案件立案,就已經達到了“證據確實,充分”,并且“排除了合理懷疑”,可以直接給嫌疑人定罪。但是根據常識,可以判斷出,各個階段采取的措施需要的不是同樣程度的證明標準,是隨著刑事訴訟過程的一步步推進,滿足越來越高的標準。對此,根據我國“審判中心主義”的理論基礎,應進一步規定由審判過程的主體審判者來適用“排除合理懷疑”規則,促進“排除合理懷疑”得到更充分的適用。
專業的司法人員作為“排除合理懷疑”規則的判斷者有利于準確適用該規則。英美法系由“陪審團”進行事實的認定,法官只負責認定法律的適用。我國是由合議庭,或者審判委員會同時進行事實和法律的認定,并確立了以審判為中心原則。雖然沒有12公民進行陪審,但實踐證明,這是該標準適用的一個新的方向。由于“排除合理懷疑”規則難以界定,普通公民組成的陪審團并不能很好的理解此規則。關于這個問題,我們面向大學生群體進行了問卷調查模擬公民審判效果。江蘇省發放問卷和網上回收的有效問卷一共573份,數據顯示,有69%的大學生認為證明標準可以用百分比衡量,并有13%的人認為證明達到50%就能夠認定嫌犯有罪。對于“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大學生在并不知道這是我國證明標準的情況下,有高達94%的認同度。而對于“合理懷疑”涵義的界定,以及證據證明力之間的相互影響程度,則如同現在的學術研究一樣莫衷一是,但89%的人堅定的認為證據的質量比數量更重要。由此可見,雖然對于“排除合理懷疑”規則雖然有些許了解,但普通理性人對證明標準仍然存在重大誤解,在關鍵問題上并不能達到專業法律人士期望他們能夠達到的狀態。所以,具有專業知識的法官更適合作為“排除合理懷疑”的實施主體,法官的專業知識是促進此規則更充分適用的一個優勢所在。
另外,有學者認為,“排除合理懷疑”可以僅僅適用于死刑案件,或者幾類刑法較重的案件,從而保證該規則的高度證明質量,將此類案件與普通的刑事案件分開來。普通法系雖然鮮有法律明文規定社會危害性越重的案件適用更加嚴格的證明標準,但在實踐中確實存在這樣的潛規則。拿美國來說,每年的刑事案件中,有95%的案件是通過辯訴交易完成的,只有罪行較為嚴重的5%會通過審判程序,通過程序之中的3%,才會有陪審團進行事實認定,適用“排除合理懷疑”標準。這樣的適用比例確實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平衡司法壓力。但是鑒于我國的死刑復核制度和再審制度有同樣的效果,都可以保證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更為公平、準確。所以,為可能判處死刑等嚴重刑罰的案件設置更為嚴格的證明標準并非必要。
三、“排除合理懷疑”與“無罪推定”原則適用問題分析
吸收、運用“排除合理懷疑”規則,可以提高“無罪推定”原則的可適用性和適用準確性。“排除合理懷疑”在“無罪推定”原則的落實上面,有“證立”和“排偽”兩個方面的矯正作用。我國規定:只有口供,沒有關鍵證據的案件不能直接定罪。為的是防止“替罪”現象。但此規定也有可能導致罪犯逃脫法律的制裁,在楊冠宇教授和郭旭教授的著作里面提到的小案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六個人合伙經營一家飯館,某晚殺死一位客人,并當即煮化倒進下水道,幾日后,其中一人自首,交代出另外五名共犯,抓捕歸案后,其余五人亦交代了犯罪的經過。但是由于找不到尸體等關鍵證據。公安機關不能進行起訴,只好將六個嫌犯釋放。如果用“排除合理懷疑”的理念分析這個問題,根據六個嫌犯分別供述的犯罪事實,對應細節,找不到尸體等證據的原因可以解釋,沒有其他合理懷疑,就可以認定罪行。由此可見,“排除合理懷疑”規則有利于彌補法律失靈,防止應該得到懲罰的罪犯被免于法律責任。
另外一個方面,“排除合理懷疑”可以正面促進“無罪推定”原則的落實。我們在江蘇訪問的時候,一家知名律師事務所給我們介紹了江西樂平的案件。樂平縣在一年內出現兩起強奸殺人搶劫案,致三人死亡,一人受傷。案件調查無果后,公安機關找到村子里面平時口碑不好的村民,對其刑訊逼供,迫使其承認罪行。一審判決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有:被害人陳述、尸體檢驗報告、人體損傷檢驗鑒定意見、現場勘查筆錄、指認現場筆錄和被告人黃某、方某及程某的有罪供述,IC卡通話記錄及電信公司出具的證明、證人的證言、尸體檢驗報告、現場勘查筆錄和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據此,2003年中級人民法院認定死刑。
上訴后,高院發回重審,2006年中院又一次同樣的判決,四個被告人上訴,高院同樣作出死刑判決。被告人申訴,直到2015年,高院立案審查,補充了三份新的證據材料,16年底作出無罪判決。
其中,無罪判決的基本理由如下:四原審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與上述新證據及原審卷宗內其他證據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和無法解釋的疑問,四原審被告人有罪供述的真實性存疑;同時,本案不能排除存在指供、誘供的可能,四原審被告人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存疑。且本案缺乏能夠認定四原審被告人作案的客觀證據。因此,原判據以定案的證據沒有形成完整鎖鏈,沒有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法定證明標準。原審認定四原審被告人犯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四原審被告人有罪。⑦
判決中明確指出,現存證據之間有“無法排除的矛盾”和“無法解釋的疑問”。雖然沒有明確使用“合理懷疑”字樣,但其“排除合理懷疑”的審判思想顯露無疑。由此可見,“排除合理懷疑”規則可以正面促進“疑罪從無”原則的落實。
結束語
“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解釋“證據確實,充分”證明標準的規則出現在刑事訴訟中,無疑是全面對證明標準進行升華過程中的一個進步。顯而易見的,該規則可以彌補現行證明標準的客觀強調證據,忽略主觀活動的瑕疵,也能提高“無罪推定”原則的適用度。但同時也存在著涵義難以解釋等問題。“排除合理懷疑”本土化的過程中,要切合的結合我國的國情,規避“排除合理懷疑”在英美法系適用中的一些弊端,充分的發揮我國特色刑事訴訟法律體系的優勢,方能有機地把“排除合理懷疑”規則融入到我國法律體系之中。
批注:
①楊宇冠,郭旭.排除合理懷疑在中國適用問題探討.[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5,33(1):159-166
②王戩.論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中國意義.[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5,18(6):103-114
③《關于刑事案件證據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蘇省人民檢察院、江蘇省公安廳、江蘇省司法廳2008年3月31日發布
④關于地方頒布的關于刑事案件中引入“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的具體對比可見李訓虎.“排除合理懷疑”的中國敘事.[J]《法學家》 ,2012,1(5):52-67.
⑤出自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國家安全部 司法部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條。
⑥李昌盛.反思排除合理懷疑標準[J]《南京大學法律評論》 ,2013(1):181-199.
⑦材料引用自http://wenshu.court.gov.cn/裁判文書網,(2016)贛刑再1號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