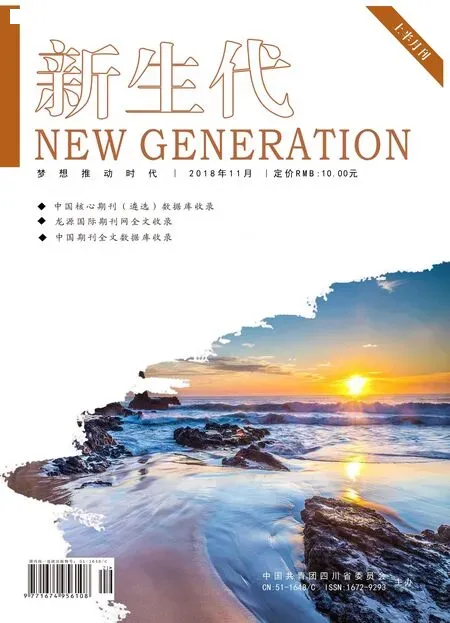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最新發展和完善建議
高凱 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檢察院 重慶 400010
一、2017年《規定》的主要亮點。
(一)進一步界定非法證據的范圍。
1.將刑訊逼供中經常出現的肉刑的含義界定為使用暴力方法,并將“毆打、違法使用戒具”列舉為典型行為,對于實踐中認定刑訊逼供提供了更為準確的模式。
2.《規定》首次將威脅方法列為非法證據排除對象,是有效制約偵查權,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
3.明確了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相比以往,將采取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方法收集的供述,證言和陳述列入非法證據排除范圍。
(二)確立了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
《規定》對爭論已久的是否排除重復性供述的問題確立了排除規則及其例外情形,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該刑訊逼供行為影響而作出的與該供述相同的重復性供述,應當一并排除。將排除重復性供述前提的非法取證行為限于刑訊逼供,而不包括其他非法取證行為。還要求排出的重復性供述必須和之前的刑訊逼供具有直接因果關系,為此《規定》設定了兩種隔斷因果關系的情況,第一是:偵查期間,根據控告、舉報或者自己發現等,偵查機關確認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而更換偵查人員,其他偵查人員再次訊問時告知訴訟權利和認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第二是: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和審判期間,檢察人員、審判人員訊問時告知訴訟權利和認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的。由此可見,《規定》確立的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是原則加例外,當重復性供述與先前的刑訊逼供具有因果關系時,予以排除,但當出現偵查階段主體變更和訴訟階段主體變更時,則推定因果關系被阻斷,此時取得的重復性供述不予排除。
二、2017年新《規定》的實施情況和思考。
(一)《規定》的實施情況。
從重慶市司法機關公布的工作總結中了解到,2016年度全年全市檢察機關共啟動非法證據調查程序50起,排除因采用刑訊逼供、疲勞審訊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詞證據46份,收集程序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物證、書證4份,因排除非法證據共對18人作出不起訴決定。2017年度共啟動非法證據調查程序51起,排除因采用刑訊逼供、暴力、脅迫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詞證據27份,排除因收集程序違法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物證、書證24份,排除非法證據后對23人作出不起訴決定。從中不難看出《規定》實施先后,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數量未見明顯變化,這值得引起我們的思考。
(二)對《規定》的思考。
1.是否應將變相肉刑和疲勞審訊納入排非范圍?
由于嚴禁刑訊逼供的政策推行多年,在司法實踐中采用暴力毆打留下傷痕的典型刑訊逼供已極少見到。但與此同時,非法取證并未禁絕,且手段多樣,推陳出新,常見的就是采用疲勞審訊或者凍、餓、曬、烤等方式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倍感痛苦,或者是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長期保持某種姿勢而變相折磨,這些訊問方式雖然不像刑訊逼供那樣直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體造成直接的疼痛從而使其違背意愿作出有罪供述,但是這些訊問方式的效果不亞于暴力手段,其往往挑戰人的生理承受極限。比如:科學研究顯示,長時間的睡眠剝奪可導致認知能力下降、記憶力損害、警覺下降及注意力難以集中、最佳反映能力下降等被訊問者往往為了早日脫離這種身心俱疲的狀態,只得作出偵查機關“滿意”的供述,而且這種變相肉刑和疲勞審訊往往難以查找證據,隱蔽性更強,往往難以查證。這可能就是《規則》實施前后司法機關非法證據排除數量未見明顯變化的原因之一。
2.是否需要對重復性供述排除制度進一步規范?
《規定》在確立重復性供述排除制度時還設立了兩種例外情形,其中一種是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根據控告、舉報或者自己發現等,確認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而更換人員,其他偵查人員再次訊問時告知訴訟權利和認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視為前面的刑訊逼供行為和后面的供述不存在因果關系。在未改變偵查機關的情況下,僅改變辦案人員真的能夠切斷之前刑訊逼供的影響嗎?在“趙作海冤案”中,當事人趙作海在28天里被迫作出9次有罪供述,他曾向媒體講述了他在公安局受到的非人折磨:辦案民警對他拳打腳踢,用搟面杖一樣的棍子敲頭,敲得他發暈;還在他頭上放鞭炮,把他拷在凳子上,30多天不讓睡覺。根據趙作海的說法:“當時打的我真是,活著不如死,叫我咋說我咋說。”設身處地想一想,在遭受如此殘酷的折磨后,縱使偵查機關變更訊問人員,不再刑訊逼供,重新告知其權利義務和認罪的后果,但是對于趙作海來說,對于刑訊逼供的教訓是如此深刻,他仍舊不敢翻供。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現代精神醫學和心理學研究已經證實,刑訊逼供等殘酷、不人道的取證手段,一經實施,不僅會對被刑訊逼供者的肉體造成直接傷害,而且會對被刑訊逼供者的心理層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當該心理創傷一旦形成,則可能在較長時間內繼續持續。所以,僅僅改變訊問人員是不能夠隔絕刑訊逼供的影響。除了更換人員、告知權利外,還應當引入更多的機制確保其再次供述的自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