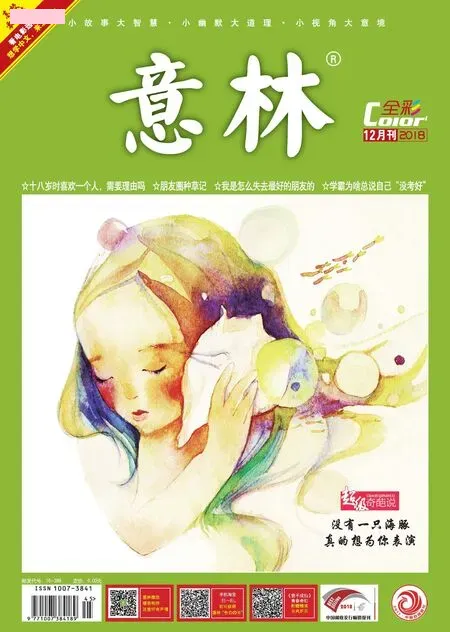朋友圈種草記
□塔 庚
翻閱你的朋友圈,可知朋友們已經暗中種下多少草。
單純曬娃已經out了,大家曬的都是新玩法:騎馬射箭攀巖高爾夫,重要的不是看見娃,而是娃所在的環境讓人艷羨不已:這是哪里啊?mark一下,快把路線發來。
單身女青年也不甘落后:精致的早餐,美好的早晨,每天不重樣的餐盤。她們在向全世界宣告,單身女青年的生活,常態就是如此啊。惹得媽媽們哀嘆,還是單身好!餐盤哪里買的?
男人才不屑于曬這些,都是小女人的把戲。搏擊、柔術、登山、旅行、馬拉松,這才是他們的賽場,當然賽場里的游戲規則也大抵相似:種草,以及拔草。甚至有人說,我們現代人的生活,就是每天種草拔草的過程。
我隨手翻出我的月度賬單和購買清單,發現它們都偷偷變長了,我在不知不覺間買了很多以往并不在視野內的東西。
草的特點是易生長但根基淺,不像大樹那樣難以拔起,所以我們會把買東西比喻為種草拔草,大致意思是說這件事不用花費什么力氣,輕易就可以完成。
我們都喜歡在朋友圈推薦好東西。這意味著你搶先接觸了這件東西,你知道肯定有追隨者,而追隨者證明了你的品位,同時也增加了你在朋友圈中的種草能力。這種能力太重要了!工作能力只有你的同事能看到,種草能力輻射的可是整個朋友圈泱泱幾千人啊,這幾乎等同于人格魅力。
而從社會學意義上來說,我們人類天生就是愛模仿的動物,當我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時候,朋友們正在干什么就是最重要的參照。朋友中認可度比較高的人,總能讓你心癢難耐:哎呀,這剛好就是我需要的。
法國社會學家塔爾德曾在其《模仿律》一書中提出三個模仿定律,即下降律、幾何級數律、先內后外律。也就是說,人們更愿意模仿比自己社會地位更高的人;跟風一旦形成,會讓更多人呈幾何級數式跟進;在熟悉的人中間更容易產生種草心理,因為我們傾向于相信跟自己關系密切的人。
我的先生最近安排了一趟家庭旅行,這次旅行很突然,我幾乎來不及反應。細究下來,我知道這個線路是他的朋友設計的,而且兩年前他就有興趣,只是沒安排在暑假,不適合我家讀小學的女兒。最近這個朋友又刷了朋友圈,于是先生毫不猶豫報了名。他不是一個容易被影響的人,但這并不妨礙他門前也會有草,偶爾需要拔一拔。
這就是為什么熟人種草總是讓人心生愉快,這意味著更高的情感連接和信任度。好像擁有了同樣的物品,你們就擁有了同樣的生活。
我最不喜歡的是被商家種草,什么東西沾染上營銷,讓你頓生反感。但有些人的文章寫得就是漂亮,讓你乖乖就范。一個我喜歡的男作者,他把自己的減肥經歷寫得風生水起,往往看到最后,偷偷一樂,順便也會看下他推介的產品信息。他花3個月時間減掉的脂肪,讓我覺得他不是信口胡說。
當然也有麻煩。
羅胖在2018深圳跨年演講中說,現金支付調動的是大腦皮層的理性決策,而移動支付調動的是一個叫蜥蜴腦的部位,也被科學證實是掌握本能的古老部分。
也就是說,當你看到朋友分享,覺得有些草即刻要拔,點開移動支付,指紋一識別,錢唰地就轉走了,這個過程完全沒有理性參與,你是在憑本能操作。這太可怕了!
這跟我們的父輩太不一樣了!他們在算著發工資的日子,盤算手里的錢該怎么花。他們的院子里從來沒有那么多草可拔。我清楚地記得,20世紀80年代,在我長大的那個小城市,父親用一個月工資給我買了一架電子琴,那棵草起碼在我心里長了一年。那一天記憶特別清晰,我和父親來到商場柜臺前,買走了最后一架電子琴。我坐在父親的自行車后座上,緊緊抱著它,風從我耳邊飛馳而過,那似乎是憋了一整年最快樂的一天。
而今我們在朋友圈里彼此感知,形成興趣,建立連接互動溝通,然后完成行動購買,最后分享你的體驗。我們的種草周期變得越來越短,欣喜和沮喪也消失得越來越快。
臨睡前我們刷刷朋友圈,看看哪些草是不拔不快的,畢竟齊整整綠油油的草坪是要經常打理的。
只是我們不再有場景,也不再有故事,我們在朋友圈種種草,拔拔草,悄悄地完成了消費迭代。
(遠煙碧摘自《中國青年報》圖/蟈菓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