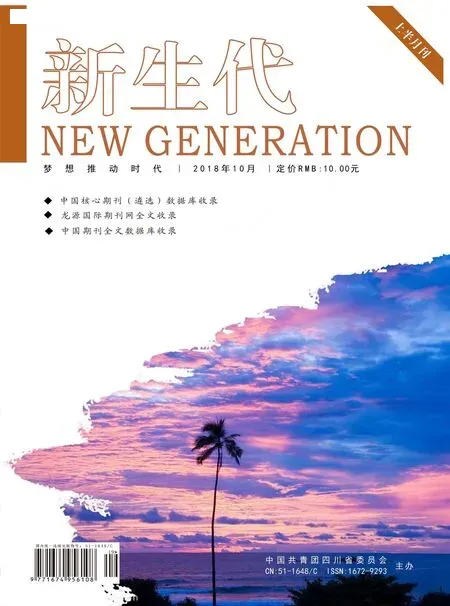學前教育階段虐童行為的法律監管體系構建
馬超 張心宇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2017年,是在2015年十八屆五中后,全面“二孩”政策實行的第三年。新生人口的增加,市場經濟蓬勃發展,卻迎來了早教問題的突然“井噴”。“攜程親子園”、“紅黃藍事件”的出現引發了包括各類媒體、社會組織以及廣大網民的口誅筆伐,這不禁讓人提出疑問,為什么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確立以后,公眾零容忍的虐童事件卻未能沒有停息。法律應該如何起到在國家治理規則起到它應有的規范作用和社會作用。
一、虐童行為的刑法規制
(一)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的確立
在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的確立之前,學術研究以及司法實踐中,往往面臨如何對虐童者進行刑事追責的問題。雖然刑法中有故意傷害罪和虐待罪對虐待、傷害行為作出了相應的法律規制,但現實案件中卻難以處理,施虐者的行為事實難以入罪,因為故意傷害罪要求受害人生命健康權的損害達到一定的標準,一般的虐待兒童行為只是造成一些肉體疼痛,不能以故意傷害罪論處。而根據虐待罪的犯罪主體必須是家庭的成員的規定,對于一些幼師虐童案也不能用虐待罪進行處理。由此而導致的結果是,在浙江溫嶺幼教虐童案發生以后,溫嶺公安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罪逮捕了施虐者顏某,后來卻又因為難以定罪,該案被依法撤銷,前后實施虐童行為兩年的顏某,僅被拘留了十五日以后就被無罪釋放。
隨著幼師虐童,或是看護人員虐待老人這種案件在全國范圍內的發生愈發頻繁,在輿論與學界的呼吁下,2015年8月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九條規定,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六十條之一:“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殘疾人等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虐待被監護、看護的人,情節惡劣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這一罪名的確立,可以說在刑法上彌補了關于虐待罪立法的不足,將非家庭成員對未成年人、老年人的虐待行為劃入到了刑法保護的范圍。
(二)法律效用
在此之前,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殘疾人等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虐待被監護、看護的人的行為,被限定在了家庭成員之間。即除第二百六十條針對虐待家庭成員的行為規定了虐待罪,第二百四十八條對被監管人規定了虐待被監管人罪以外,如需對虐待家庭成員以外的被監護、看護對象專門治罪,一直存在著刑事立法方面的缺失,在現實中即使發生了類似行為,同時需要運用刑事法律調整時,也多以“尋釁滋事”進行處罰。這導致了其他施虐對象產生虐待行為時,要試圖去套用其他罪名。但這往往會出現不適用或者嵌套不能完全吻合的情況,從而會降低施虐者的罪行。浙江溫嶺的幼師虐童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這樣的后果是,不僅不能對于虐童行為實施有效的打擊,同時也不利于學前兒童等特殊群體的合法權益保護。
2015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正是在此基礎上一方面要實現對于除家庭成員以外的其他施虐群體的有效打擊,同時也是以法律的形式來嚴格規制監護人、看護人等群體的行為以實現對于這類特殊群體的權益保護。
二、虐童行為的原因分析——仍未消減的法律思考
(一)刑法規制的局限性
刑法修正案(九)確立了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是立法工作的進步,彌補了刑法有關方面的缺陷,也是國家對兒童保護,人權保護十分重視的重要表現。同時,刑法是制裁方式是最為嚴厲的,通過對犯罪人員的生殺予奪來約束人們的行為,通過刑法來規制有關的虐待行為,從邏輯上來說,應該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從2015年11月1日“刑九”生效以來,關于虐童案件的報道仍然頻繁出現了公眾視野之中,2015年11月,30多名四平市紅黃藍幼兒園的兒童被針扎,2016年11月,寧夏銀川市興慶區一民辦幼兒園教師疑似拿針管扎學生。2016年12月,河北深州一所幼兒園的幾位保育員涉嫌虐待孩子。2017的“攜程親子園事件”以及“紅黃藍事件”的發生更是震驚全國。但是實際上,我們卻發現,在司法實踐中,對幼兒園虐童行為適用于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判例仍然較少,在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檢索中,目前僅有五例關于幼兒園虐童最終適用于虐待被看護人罪的判例①。在已有的判決中,我們發現存在著罪名適用混亂的現象,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作為一項選擇性罪名,在對幼兒園虐童行為應是“虐待”,但是最后判定的罪名卻是“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和“虐待被監護人罪”。同時,還存在處罰力度較輕,附加刑中的職業禁止制度的適用不規范的現象,應該說這是和此罪確定的時間較晚,條文內容不明晰,在司法實踐中應用不夠充分有著比較重要的關系。
(二)相關立法建設不完善
從不同法律的性質來看,刑法具有謙抑性,是保護社會利益不受侵害的最后一道屏障。只有在民法、行政等法律對法益的保護不夠充分時,才會把“刑法”作為有效保護的最后手段,所規制的行為是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侵害社會利益的行為②。在接連不斷的虐童事件發生以及司法實踐中,使得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的規定中,處罰標準沒有階梯變化,刑罰方式的單一,缺乏整個法律體系的支持的缺陷暴露了出來。
而且目前整個針對學前教育的監管體系建設并不完善,相關的立法包括國務院批準發布的《幼兒園管理條例》(1989),教育部批準發布的《幼兒園工作規程》(2016),《幼兒園辦園行為督導》(2017)等,在各地還有專門的《學前教育條例》,同時還有一些學前教育的規范散見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乃至于《憲法》中,總體來說,立法數量不少,但是缺乏整體的規劃,尤其是在對比已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對初等、中等、高等教育都進行全面的規制。學前教育作為《憲法》中明確規定的四個教育階段之一,卻沒有一個專門的、系統的、層次較高的法律進行學前教育的規范。同時,國家在0—3歲的托兒所的監管方面缺少立法規范。國務院的《幼兒園管理條例》只對3歲以上的幼兒園,這個立法空白也給給了一些利益集團上下其手的空間。
總的來說,雖然相關規范很多,但大多是指導性的,只是從宣傳和號召上發揮作用,缺乏對實際操作的規制,有些區域還存在著立法空白。關于學前教育的法律監管體系沒有形成,沒有從多個層面形成系統化多元化的學前教育領域的法律保護與規制。
(三)行為主體缺乏從業資格
從目前我國已經發生的虐童事件來看,大部分事件的發生都與幼師隊伍的素質有著直接的關聯。因此在這一環節當中尤為重要的就是幼師隊伍的素質,幼師的不負責任,打罵行為會對兒童的身心健康產生直接威脅。虐童事件的不斷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相關的從業人員缺乏兒童權益保護意識,沒有專業教育,學前教育教師隊伍缺乏較嚴格的準入門檻。許多早教機構為了快速斂財,多采用“先上崗,再考證”的辦法,讓沒有教師資格的工作者進入到從業領域,從而直接導致了這些未經專業訓練的工作人員對兒童做出了暴力行為。
在另一方面,一些托兒所、幼兒園經營十分“隱蔽”地進行經營,這些“黑幼兒園”無牌無證,缺乏必要的安全、消防設施,辦學條件堪憂,有些地區經濟不發達,早教資源缺乏,也難易符合相關的從業標準。
(四)缺乏有力的監管體系
幼師準入門檻的缺失,市場經營的混亂,反映出早教機構的監管力度仍然有待提高,尤其是在“攜程親子園事件”中,這種早教機構的監管不到位的問題暴露得淋漓盡致。在2015年,攜程曾經開辦幼兒園卻因為沒有相應資質而被叫停,但在年底,因為上海婦聯的牽頭介入,上海《現代家庭》雜志旗下“為了孩子”學苑與攜程合作成立“攜程親子園”。這其中到底存在著什么樣的利益糾葛我們難以知悉。現已查明占有《現代家庭》雜志社100%股權的股東正是上海市婦聯,同時親子園負責人張葆葆有著橫跨政商多界的復雜背景,這些信息也更加讓人疑惑。那么這恰恰說明了我國目前在監管方面存在的短板問題。相比較于發達國家,我國的學前教育的師資以及監督管理都存在缺失。隨著我國逐漸放開二胎,供需之間矛盾逐步產生,一系列學前教育機構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但正是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準入門檻,教委和工商部門卻都有準入的權利,這使得準入和管理都出現了齊頭并進現象,從而使一些資格并不健全的教育機構鉆了制度的空子。
三、學前教育階段虐童行為規制中法律體系的構建
規制虐童行為可看做是對于兒童的一種保護,目前狹義的兒童保護是指國家通過司法救濟、社會救助和替代性養護等措施,對已受到或可能受到摧殘、忽視、虐待、剝削及其他形式傷害的兒童提供的一系列救助和安全保護,以使兒童能在安全的環境中成長。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這就要求不論是在法律、監管還是學前教育等各個方面都要各司其職,才能切實做好兒童的合法權益保護工作,使兒童可以在安全的環境實現自身的成長。
(一)完善虐童行為的刑法規制
我國刑法在對虐童行為本身的規制上并不存在法律缺位的現象。但目前存在的問題在于執法未必嚴、量刑未必夠以及懲治未必準的現象,這種客觀存在的現象使得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立法最初目的。因此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定罪以及處罰的針對性以及震懾力問題。
具體到《刑法》第二百六十條之一,就是要從罪名的認定標準的確認、兒童證言的效力、兒童證人的保護以及提高虐待被看護人罪的法定刑,并且規范職業禁止制度的適用。
這些問題解決的主要路徑一方面在于立法層面加進行相應的調整,另一方面在,在司法實踐的過程形成更具權威性的法律解釋或是指導性案例,通過總結案例來討論措施并廣泛推廣,解決目前關于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如何適用的問題。從而最終加強定罪針對性以及提高懲處效力。
(二)推動《學前教育法律》的立法工作
在2018年2月教育部所公布的工作重點中,已經提到要推動《學前教育法》的起草,去彌補目前缺少一個專門、系統、高位的《學前教育法》的空白。新的《學前教育法》應該在宏觀層面上完善學前教育領導體制、管理體制、辦園體制。并且要積極地引導國家關于學前教育方面經費投入、保障幼兒教師的正常待遇和規范不同地區辦園條件的標準等方面,從而推動整個國家學前教育的健康發展。
(三)建立完善的法律監管體系
有了基礎立法并不能夠足以解決的實際的問題,為了解決學前教育領域的資源稀缺、從業主體不規范、幼師隊伍良莠不齊的現象,有必要建立一個完善的、系統的、動態的法律監管體系
法律是在封建宗法制度退化以后,由傳統的倫理秩序向現代的法治秩序轉型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主要內容[2]。同時也是現代國家發展主要的管控工具。然而,由于立法技術的限制,以及法律本身需要保持一段時間的穩定性才可能保持法律的權威的特點。從早教市場擴張的速度來看,或者說各個市場領域所出現的新型的商業模式,采用立法手段進行全面規制,其立法成本將會非常高昂,或者說基本上不現實,對于其法律規制來說是一種極大的挑戰。
因此針對辦學、監督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不僅僅需要政府部門的強行打壓,同時也需要專業的監督部門來加強引導,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實現監督的合理有效運行。法律規制必須克服其所具有的靜態化、穩定性的特征而與整個社會脫節的缺陷,去不斷加強法律規制的適應能力,要能及時解決在整個社會進程中所產生的矛盾。
虐童事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這種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現象所形成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因素導致的,映照在法律方面,就是就整個學前教育監管體系的設置不夠完善,而且虐童案件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兒童作為國家未來的希望,虐童案件的受害兒童精神損害難以回轉,所以對于虐童行為,必須從根源上尋求解決辦法,如果不從一個整體的,系統的視角出發,只是依靠刑法的規制,或者基礎法律的統籌那么,法律本身所應有的教育功能和救濟功能就難以得到實現。
1.提高幼師隊伍的準入門檻
《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明確指出:“教師應把保護幼兒生命和促進幼兒健康放在頭等重要位置。”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章第21條規定:“學校、幼兒園、托兒所的教職員工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不得對未成年人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這些法律法規的制定從教師層面對其行為作出了概括性的規定。
在對幼兒園的日常教學過程,幼師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地影響到了兒童的身心健康。也是虐童案件發生后的直接行為人。那么若要提高教師隊伍的素質,首先就要提高這一隊伍的準入門檻,從幼師的培養入手來將強對于幼師的專業素質及心理素質、道德素質培育。此外,我們不能忽視的一點是,嚴懲虐童行為幼師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幼師的心理落差以及降低幼師的職業認同度,那么如何培養幼師隊伍以及提高幼師的待遇,也成為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對于幼師的待遇,另一方面要提高幼師的準入門檻,加強幼師上崗資格審查,定期考核以及定期培訓,同時要將幼師隊伍加入到整個教師隊伍的統一管理,保障其應有的福利待遇,定期進行培訓,從幼師的培養以及認同度等方面入手,加強幼師隊伍的綜合素質,有助于為學前兒童創造良好的身心環境,保護兒童的合法權益和身心健康。從學前教育作為啟蒙教育,以及幼兒園所需要承擔保護、教學的多重任務,在幼教與幼兒之間,不應該只是單純的“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關系,同時也是兒童權益與兒童心靈的“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系。
2.規范學前教育機構的市場經營行為
截止到2016,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為77.4%②。學前教育的缺口仍然很大。學前教育的市場仍然是一個供給方市場,所以對于學前教育機構的經營行為,必須要加以規制,對于營利性與非營利性的幼兒園進行分類管理。
進行學前教育機構從事教育活動必須要有嚴格的行政許可、審批程序,只有嚴格完成這些程序的教育機構才有資格從事相關的行業,對于一些區域,政府應該扶持幼兒園的發展,投入相應的資金,使不規范的幼兒園朝著規范的方向發展。而對于辦學條件特別差、無證無照的“黑幼兒園”、“黑托兒所”要堅決地予以取締。
3.建立起系統的安全防控機制
從學前教育的相關行為主體出發,在幼兒、家長及幼兒園建立完善的聯動機制,通過包括微信、短信、錄像、實時監控等多種手段,讓家長能夠及時地了解到孩子目前的實際情況,同時也有利于園方進行管理。
另一方面是從不同階段出發,在事前要加強預防,建立信息流通機制以及定期兒童報告機制,把握兒童安全、幼教行為等關鍵控制點。在事中要加強控制,確定負責幼兒監管的機構,在事后的救助上,要及時將虐童行為人引入司法程序,形成司法震懾,并且在虐童案件的處理上,要考慮兒童心靈的脆弱性,推動偵查、審判機關對被害兒童實行 “一站式”詢問,在專門區域,由專門的偵訊人員進行詢問,避免對兒童造成二次傷害。
四、總結
2017年發生的兩起影響巨大的虐童事件,一個發生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全國知名的連鎖幼兒園,另一個發生在中國經濟水平最高,現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并且在國內知名的互聯網公司的親子園內。也讓人不禁想象,在沒有發達媒體報道的地區,學前教育的環境目前會有多糟糕。
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生活節奏的不斷加快,學前教育事業迎來發展的黃金期,越來越多的父母因為工作的原因開始將自己的子女送入各類托兒場所之中,但隨著而來的問題就是,早教教師的培養卻難以跟得上早教市場擴張的腳步,學前教育的機構建設水平難以跟上因為教師的素質教育可不像資本一樣可以迅速膨脹,早教教師對幼兒的耐心與同理心的培育也不是一日而成。根據上海總工會的一項數據顯示:2015年,上海市獨立設置的托兒所只有35所,而上海0到3歲的嬰幼兒人數卻達到了80萬。在供求失調的早教市場中,有許多托兒所,幼兒園“無證半血”托兒所遵從市場規律,選擇降低教師的準入門檻,實行“先上崗,再考證”,使得許多非專業教師、不合格教師進入幼兒隊伍,導致幼師隊伍整體素質降低,資本涌動比法律規制要更加地洶涌。
在這種情況下,法律不應再僅僅扮演一種維持“底線”的角色,也要起到批準者與保護者的作用,要能擔負更多的責任。應該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立法方式,要多在源頭上深挖,通過多種法律規范齊頭并進的方式。首先要提高各個群體關于兒童權益保護意識,讓兒童本身、家長還是幼師隊伍,都應該清楚何謂虐待以及如何防止虐童行為的發生,當發現此類問題時解決問題的路徑以及相應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以及行政懲罰等。在頂層設計方面,要加強各方面制度的完善,辦學更為規范并納入正軌。同時要加強監控力度,實現整個學前教育透明化、制度化。對于現有隱患要及時排查,對于未出現問題的要防患于未然,以頂層設計帶動整個社會的行動,構建起保護兒童的法律體系,立法體系建立了,關系理順了,才是對于打擊虐待兒童犯罪的最好解決辦法。
注釋:
①任靖、劉志娟一審刑事判決書《(2016)內0105刑初516號》;宋瑞琪、王玉皎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一審刑事判決書 《(2016)吉0302刑初138號》;宋某虐待一審刑事判決書《(2017)冀0102刑初127號》;王某某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刑事判決書《X2017)遼1322刑初101號》;邢某虐待一審刑事判決書《2017)冀1026刑初312號》。
②參見文獻:陳興良:《刑法總論精釋》,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第3版,第16頁。
③參見國家統計局2017年10月發布的2016年《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統計監測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