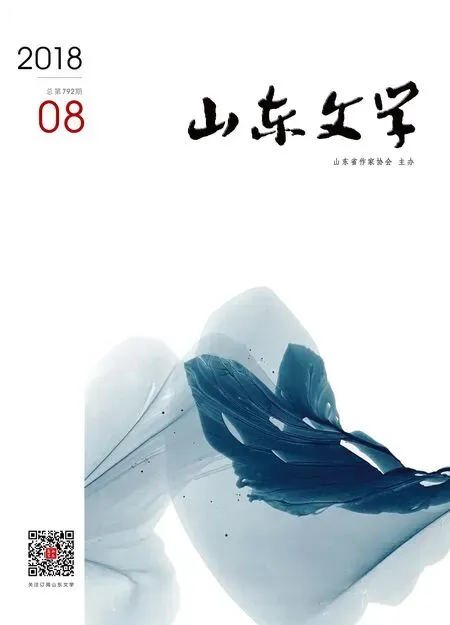自有它的個性
高維生
世界上最偉大的蔥
北碚客居的日子,隔一兩天去永輝超市,有時上江邊農貿市場買菜。賣大蔥攤位上的牌子,寫著山東大蔥,從蔥的形象,一看就是外來品,不是當地的蔥。我每次買蔥,拿在手中,想到黃河岸邊的家。
物流發達的今天,山東大蔥來到西南的北碚,不是什么新鮮事。蔥應是章丘大蔥,從它的植株高大,似梧桐樹狀,所以稱“大梧桐”。這種蔥,“辣味稍淡,微露清甜,脆嫩可口,蔥白很大,適宜久藏。”去年冬天,文強送我一盒“大梧桐”,一棵株高達一米多,白長有三分之二,直徑粗,學者吳耕民教授在專著《中國蔬菜栽培學》中贊美道:“世界上最偉大的蔥。”
章丘大蔥的最早品種,于公元前六八一年,由西北傳入齊魯大地,已有近三千年的歷史。早在公元一五五二年,就被明世宗御封為“蔥中之王”。
章丘大蔥,屬百合科蔥屬,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稱菜伯、和事草。《爾雅》《山海經》《禮記》《齊民要術》《清異錄》等古籍,對于蔥都有載錄。大蔥有山東章丘大蔥、陜西華縣谷蔥、遼寧蓋平大蔥、北京高腳白大蔥、河北隆堯大蔥、山東萊蕪雞腿蔥、山東壽光八葉齊蔥,又稱四季蔥、菜蔥、冬蔥。這一類的大蔥適宜烹調,辛香味厚。
章丘大蔥在明代,在女郎山西麓一帶普遍栽培,此蔥長得高大,植物莖長,脆生生,甘甜真醇,所以人們叫它“蔥王”。
三月的北碚,玉蘭花剛凋謝,西南大學僧雨樓前的紫荊花又盛開,引來許多人拍照。下午陽光充足,打開窗子讀書,只要向外望去,就能看見縉云山觀景塔。讀梁實秋的《雅舍談吃》,其中一篇《烤羊肉》,他寫到濰縣大蔥,就是現在的濰坊大蔥。這里有個問題推測,從地理位置上講,濰坊離青島近,由于當時交通不便利,商品的成本關系,青島人吃濰坊大蔥合情合理。從另一個角度講,梁實秋是大學問家,又是作家,對生活的觀察與一般人不同,他不可能不知道,響當當的章丘大蔥。他在文章中寫道:
我在青島住了四年,想起北平烤羊肉饞涎欲滴。可巧厚德福飯莊從北平運來大批冷凍羊肉片,我靈機一動,托人在北平為我訂制了一具烤肉支子。支子有一定的規格尺度,不是外行人可以隨便制造的。我的支子運來之后,大宴賓客,命兒輩到寓所后山拾松塔盈筐,敷在炭上,松香濃郁。烤肉佐以濰縣特產大蔥,真如錦上添花,蔥白粗如甘蔗,斜切成片,細嫩而甜。吃得皆大歡喜。
二〇一三年十月,放長假的幾天,踏上去青島的旅途,我不是湊熱鬧游覽,而是為了寫梁實秋,拜訪他的故居。二〇〇八年,我到過重慶,住在北碚西南大學附近的旅館。我住的前面有一條街,每天非常繁華,順街往前走經過雅舍。房子建在半山腰上,一看就是修復后的新居,但梁實秋在這里生活過,這片土地上留有他的蹤跡。
青島對于我是陌生的城市,在友人的陪伴下,費盡周折找到魚山路三十三號二號樓。鐵柵欄的大門半掩,門邊的方形石柱子上,掛著黑底燙金字的牌子。讀著英漢兩種燙金文字的說明,這些簡單的介紹,心中升起蒼涼。我觸摸到被陽光曬得溫暖的鐵門,一聲吱嘎的聲響,門讓我推開,左側有一棵斜倒的大樹,生命極其頑強,它的根系扎在大地上。
進了大門,是一段下坡的窄小路,一道不高的水泥墻,隔出梁實秋故居的二號樓,大門右側掛著 “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院子里的空間極小,中間立一根柱子,從漏水管拉出的繩子系在上面,曬一些衣服。窗前不大的花池子里,種著一株大葉子花草。借院墻接出的小倉庫,占據大半個院子。
故居是一座舊樓,印滿時間的痕跡,探出的陽臺,水泥皮脫落露出紅磚。當年梁實秋在這里居住,陽臺不是封閉,而是開放式的。翻譯累了,站在上面,呼吸新鮮的空氣,伸腰擴胸,活動筋骨,感受吹來的海風。
一九三〇年夏天,受到楊振聲的邀請,梁實秋到青島大學任外文系主任。隨后全家從北平遷到這里生活,他們的小女兒梁文薔在青島出世。梁實秋從北平訂制烤肉的鐵箅子,認為這個烤器,在青島獨一無二。他從山坡上撿松枝和松塔回來,在寒冷的日子烤肉,宴請聞一多等諸友品嘗。
二〇〇八年,我第二次去重慶來到北碚,住在西南大學附近的旅館,距離雅舍不遠。我是在下午拜訪雅舍,衡門上的斗拱下,有一塊黑色嵌金字的“梁實秋故居”的匾牌,里面是一條縱伸的青石臺階。
過去的建筑消失,重構的空間發生變化,被賦予新的意義。老的雅舍為我們提供了當時的歷史情景。
我來的時候,兩扇傳統的木門敞開,站在大門前,注視“梁實秋故居”幾個大字,身后是一條繁忙的馬路,人流和車輛穿行而過,耳朵中沖滿各種噪音,很難讓心靜下來。雅舍在上面的平臺,我要攀登長長的石階。這條石階路,不是為了創造景觀而設,是采取因地制宜。
初到重慶,這里的自然環境和民風民俗,自與古老的北平不同。濃重的當地話,梁實秋聽起來費力,有的話猜半天,才明白講的什么意思,尤其住的重要,總不能天是房地是床,睡在露天中。梁實秋對當地的建筑感興趣,覺得此地建房容易,最經濟實惠。磚不是用來砌墻,卻用來代替柱子,四根磚柱互不牽連,上面搭上木頭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單薄得可憐;但是頂上鋪了瓦,四面編織竹篦墻,墻上敷泥灰,遠遠地看過去,沒有人能說不像是座房子。”這樣的房子在北平,只能作為儲存雜物的倉庫,薄薄的竹篾墻,遮住人的目光,擋住風雨,不能抵擋冬天的酷寒和風雪。梁實秋住的“雅舍”,用唐代白居易的詩比喻:“吾亦忘青云,衡易足容膝。”
梁實秋生活在古老的大家庭中,長大以后,又考入清華大學,然后去美國留學。他經過歐風美雨的洗禮,見過大世面的人,吃過正宗的西餐,住過大洋樓,看到過不同的建筑,“我的經驗不算少,什么‘上支下摘’‘前廊后廈’‘一樓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間’‘茅草棚’‘瓊樓玉宇’和‘摩天大廈’各式各樣,我都嘗試過。”梁實秋對于每到一個地方,很快地融入進去,不會得水土不服。人無論住在哪里,對那所房子一定發生感情的變化。這段生活是梁實秋的重要經歷,雅舍是一個文本,不是獨立的信息,綜合地反映歷史,以及時代的蹤影濃縮其中。寫出的文字,孩子們的打鬧聲,朋友們喝茶聊天的話語聲,人身體的氣味,構成雅舍的復雜空間。在戰亂的年代,梁實秋來到后方重慶,遠離炮火的危險已經幸運。他和友人建起“雅舍”,其目的不是享福,只想生存下來,不存有大的奢望。雅舍是一所陋房,梁實秋將它安排的有條理,賦予它浪漫詩性的名字。住進去兩個多月,梁實秋對空間多了情感。陰灰的雨天過去,一朵陽光從窗子投映進來,使房子里有了溫暖的關懷。人們搭建簡陋的屋子,建筑的材料、竹子、茅草、泥土,脫離開大地,經過雙手的構建,實現想象的形式。窗欞上的每一根竹子,顯現時間印記。在一天中,光纏繞其上,夢的韻律,奏出光與物的序曲,喚起人的情感。他感覺房子有家的暖意,不僅是蔽風雨的空間。有窗子能向外眺望,看著挑擔走過的人,注視風雨的無常變化,有了創作的沖動。“然不能蔽風雨,‘雅舍’還是自有它的個性。有個性就可愛。”
最宜月夜——地勢較高,得月較先。看山頭吐月,紅盤乍涌,一霎間,清光四射,天空皎潔,四野無聲,微聞犬吠,坐客無不悄然!舍前有兩株梨樹,等到月升中天,清光從樹間篩灑而下,地上陰影斑斕,此時尤為幽絕。直到興闌人散,歸房就寢,月光仍然逼進窗來,助我凄涼。
我來到雅舍,回味描寫的文字,從中發現寧靜中的美。重慶多雨,濛濛細雨之際,雅舍被水濕包圍,有了朦朧的詩意。梁實秋寫作累時,推開窗子向外眺望,霧一團團地堆積,吸一口潮濕的空氣,看不到幾米外的東西。下雨的天氣,窗子不能敞開,聽雨的清脆聲,只能透過玻璃看。雨天的人容易傷感,雨絲愁思一般,牽扯人的思緒走向遠方。人的情感脆弱,經不起雨聲的折磨。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梁實秋故居在西南大學一號門不遠處,走出大門,沿著天生街往右拐,走過一個路口,馬路對面是梁實秋的雅舍。
八年后,又是在下午,我和高淳海拜訪梁實秋故居,沒有多大的變化,院子里梁實秋的塑像,他似乎剛喝完茶,坐在院子里休閑。右手的梨樹,白色的花在凋謝,地上鋪滿白色的小花瓣。左手是一棵粗大的黃葛樹。在玻璃柜里,有一副梁實秋戴過的眼鏡,夜晚寫作使用的油燈,清晨刮臉的剃須刀。這些實物帶著他的體溫,在雅舍里,太陽從縉云山上滑落,夜色降臨。
梁實秋在雅舍掌起玻璃柜中的油燈,戴著這副眼鏡,在微弱的燈光下,回憶中寫出在青島的生活。
至于梁實秋的濰縣大蔥,還是章丘大蔥不重要。我在北碚的日子,經常去菜市場和超市買菜,買山東大蔥時,回想梁實秋離開青島,來到北碚時,如果在菜市場買到山東大蔥,他會問一下,是不是濰縣大蔥,或者章丘大蔥。做菜熗鍋的蔥香味,彌漫在雅舍里,在心中游蕩。
永川秀芽
早飯后,窗外的大霧仍不散,天空灰蒙蒙的弄得人的情緒不高。坐在窗前,目光穿越兩樓中的空間,向遠處縉云山眺望,什么都看不清,一片云霧籠罩。
我客居的斗室,身邊是一張床,窗臺、床頭柜、床頭全是堆的書,一臺筆記本電腦,一盞臺燈,逼仄的空間,沒有多余的東西。我在這里生活、寫作、讀書,有四個多月,今天是2015年的第二天。從山東帶來的“日照綠”,喝得所剩不多。思家的情油然生長,每喝一口,加重回家的心切。昨天淳海買回重慶的名茶。泡了一杯 “永川秀芽”,看著清新的茶湯,茶葉上下翻滾,香氣在空中彌漫。
喝茶需要心境,安心靜氣,飲一口在舌尖上回味,這期間生出許多的滋味。這么多年,我偏愛綠茶,淡淡的香氣,不濃烈,不火爆,有綿長的意蘊。那種繚繞的香,隨著水濕氣,滲入人的記憶中。每次高淳海放假回家,給我帶回幾包“西農綠茶”,有一段時間,每天用黃河水,泡著山城重慶產的綠茶。一南一北的結合,塑造出一個個美好的時光,貯藏在情感之中。
來重慶后,茶葉桶換了幾個,現在使用的是竹茶葉筒,這個笨重的家伙,倒拴住我的心了。眼瞅著茶葉見底,昨天是元旦,高淳海從街里回來,買回一包“永川秀芽”。淡綠色的包裝,溪水、茶農、大山,構成古樸的田園畫面,與綠菜的風格相匹配。我打開袋子,聞到撲鼻的清香,送來山野的氣息。
永川這個地名,不是一包茶葉,我不會知道的。永川區在重慶的西部,“城區三河匯碧、形如篆文‘永’字”,諸葛亮賜名“箕山”,這個號稱“天下第一隱山”的地方,位于永川區城以北2公里處,擁有大面積的茶園與竹海。獨特的地理環境,形成茶竹相依的自然景觀。
永川歷史悠久,厚重的人文歷史,使它在西南有重要的意義。自古以來為川東南和渝西地區重要的交通樞紐。
一杯茶帶來厚重的歷史,宛如打開一部大書。綠色的茶湯,每一個水分子中,深藏著自然的氣息,也有人文的積淀。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品茶不僅是解渴,它能養生,品味修身養性,咂摸人文歷史。茶是博大的,一片葉子,生長在山野中,憑著堅韌的性格,在高處、忍受清寒的寂寞,不同流合污,它清高的品性,也是紅塵世俗人追求的境界。
品各個地方的茶,從茶的名字,就能尋找到它的根源。茶是地緣文化塑造的精靈,當它相遇水時,看似普通的葉子,爆發出的激情,將無味無色的水,燃燒成綠色的火焰。
客居異鄉的日子,一杯綠茶,一本書,伴我度過很多的時間。
有茶相陪,不會感受寂寞。順著茶香氣,走進它的歷史中,尋找大起大落的故事。地點不同,天氣的狀況,品茶人的心情不可能一樣。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日,我獨自坐在窗前,品新買的“永川秀芽”,手機跳出一條短信,電氣通預報,北碚黃色預警信號,將出現小于三千米的霾。我端起茶杯,透過茶湯,注視灰色的天空。
額芬餑餑
早飯后,散步到山東大學校門,它的對面有兩家書店,一家是山東大學出版社的書店,緊挨著的是門面不大的新華書店。我常逛新華書店,這里有一個特價書架,在打折的書中,淘到《文人飲食談》一書。
《文人飲食談》收入端木蕻良的《東北風味》。他是三十年代東北作家群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寫出產生重要影響的力作《科爾沁旗草原》,但他的散文沒有讀過。這一組不長的文字輯在一起,主要回味家鄉的小吃。他談到《玻璃葉餅》,菠蘿又稱波離或波琴,意思是滿語的谷米。端木蕻良在文章中說道:“家鄉有一種樹,葉子很大,葉面光滑,反光性很好,鄉親們都叫這樹的葉子為玻璃葉。用這種葉子包制的餅,叫玻璃葉餅。”端木蕻良說的玻璃葉,是指柞樹葉子,民間把柞樹叫“菠離蕻子”。一些資料上混淆,有的學者誤將椴葉餑餑,用柞樹葉子做成的。陪母親聊天,說起一些過去的事情,她說六〇年困難年代,人們吃代食品。上山采菠離蕻葉子回來,在鍋中烘干搗碎,摻進苞米面中吃。姜劼敏考證中認為,真實的做法,是采用椴樹枝上的葉子,葉大而圓,邊齒小而整齊。采后洗凈,將葉面餡包裹即可。椴樹葉清香能食用。而柞樹的葉窄,折不成半圓形狀,吃起來發苦。《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造做類”條目中,明確寫有“椴葉餑餑”。宮中祭祀時“五月初一日供椴葉餑餑”,每年的農歷四五月間,上山采集嫩椴樹葉,回家洗凈待用。泡好的粘米加水磨成細面,紅小豆煮爛,然后搗成泥餡,包成大餃子形狀。椴樹葉抹好豆油,裹上粘米的餃子上屜蒸。
我祖母出生在烏拉古城,她是旗人,在平常的生活中,遵守老滿族的規矩,給我講過許多的民間傳說,哼唱過古老的歌謠。她喜歡刺繡,俗稱針繡、扎花、繡花、繡云子。滿族女孩子,從十幾歲做女紅,針線活不好,要受別人嘲笑的。一塊撐子上的白布,通過她針線的穿動,一只飛鳥,一條河流,一朵野花復活起來,表達對吉祥幸福的向往。一九八三年,我結婚那一年,祖母給孫子媳婦一針一線,縫了一件緞子棉襖,紅色碎花,盤的是紐袢,至今收藏在柜子中,成為一件傳家的寶貝。妻子偶爾拿出來,欣賞祖母的手藝,更多的是對她的懷念。
祖母手巧,包水餃時能變出花樣,包幾個麥穗和盒子狀。難吃的苞米面,在她的手下做出各種餑餑。苞米面發酵后,鋪在鍋中的屜上,攤成一寸,撒上紅小豆。蒸出的發糕,松軟入口,有淡淡的酸甜味。祖母喜歡粘食,椴葉餑餑,粘耗子,粘豆包。對這些食物的偏愛,是與她接受的民族文化的影響分不開。
二〇一四年六月,我去其塔木拜訪滿族剪紙傳人關云德,觀看了他新創作的作品。他贈送我《親親聊條邊》《九臺文史資料》,兩本書中有他的文章,關云德講了滿族跳餑餑神。
每到龍虎年,滿族人燒香祭祖,要為敬祖準備一些供品。在淘米、蒸米、制作打糕中,扎著神裙子的薩滿,對著天地唱起震米的神歌。在神鼓聲中,古老的歌聲,伴著人們的頌歌完成制作供品。
跳神的吉日,院子中置一張高桌,為擺放供桌。盛滿高粱的斗上蓋著紅紙,屋中的西墻下,家神案前有供桌。上鋪一塊紅布,一對燭臺,兩個香爐,三碟打糕,三杯米酒。懸掛在屋梁,或門框上的大鼓,讓人充滿敬畏之情。南炕上的家神,祖爺匣子,北側的索口袋,外屋的佛多媽媽,院中升斗案前,有一只木制年祈香爐。年息花滿語是“松吉爾花”,植物學上的名字叫野杜鵑,它是民間稱的迎春花、干枝子梅、年息花。這種花長在石砬子的峭壁上,叢生小灌木,每年早春時節開花。四月至五月初,此葉香味濃郁,長在大山的深處。因為味道強烈,在空氣中散播,鳥兒都忍受不了香氣,躲得遠遠的。人們結伴攀上山頂,掐年息花做香,這就是民間所說的“掐春”。家神案前有兩個香爐,分別是燃年息香和漢香,擺上供果,酒杯倒滿酒。由男孩子點燃香,俗稱的上香童子,每燃著一炷香,叩一次頭。火鐮點燃香燭,香煙裊裊飄升,這是美好的寄托。大薩滿和助手敲響皮鼓,祈禱祭祀開始,跳起餑餑神。
《滿族餑餑》是一首滿族情歌,以粘糕為主題,歌頌年輕人的愛慕之情,同時讀出餑餑在滿族人心中的重要位置:
黃米糕,粘又粘,紅蕓豆,撒上面,
格格做的定情飯,雙手捧在我跟前。
吃下紅豆定心丸,再吃米糕更覺粘。
越粘越覺心不散,你心我心黏一團。
“餑餑”的滿語是額芬,它是滿族人對面食的稱謂。滿族常年在野外捕獵和征戰,隨身帶的粘餑餑,既省事,又能抗住饑餓,養成吃餑餑的習俗。祭祀祖先和敬神,多用各種餑餑。滿族的餑餑種類繁多,常見的有蘇葉餑餑、豆面餑餑、牛舌餑餑、椴葉餑餑、同心餑餑、清明餑餑、肉末燒餅、酸棗糕、淋漿糕、五花糕、芙蓉糕、綠豆糕、五花糕、宵而卷、馬蹄酥、豌豆黃、牛舌餅、四葉餅、淋漿糕、豆擦糕、油炸糕,還有涼糕、小酥、盆糕、發糕、打糕、鏃餅等。餑餑的食材主要有兩種,白面和粘米面,制作工藝多為烘、烤、蒸和烙。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帝東巡至大烏拉。當時他年方二十九歲,是一位年輕的皇帝,表現出非凡的統治才能。經過八年的艱苦斗爭,平定“三藩”的叛亂,便目光遠大地率眾北上,視察東北邊陲,加強邊界的備戰,準備迎擊沙俄入侵者,康熙這次東巡的最終目的地是吉林、大烏喇兩城。
衣食住行是東巡中重要的部分,接駕恭賀皇帝所貢的餑餑,一部分用來吃的,同時是上供用的供品。餑餑一部分,除由吉林將軍府果子樓提供外,康熙皇帝駐蹕大烏拉虞村,余下的是打牲烏拉衙門提供。由于打牲烏拉衙門不設供應餑餑的機構,便分派給當地糕點商鋪和大戶人家制作。二〇一五年八月,我為了看烏拉打牲衙門第三十一任總管趙云生的私宅后府,來到烏拉街,就是歷史上叫大烏喇的地方。站在后府的園子間,望著遠處的苞米地,想象當年康熙皇帝東巡,來到這里的情景。
四月末的平原,陽光豐沛,樓下鄰居家的小狗,一陣狂叫。書房的窗子前,吊掛的綠蘿,垂下的莖蔓,在陽光的擁抱中,散發旺盛的生機。讀端木蕻良的文章,想起夏丏尊說過:“在中國,衣不妨污濁,居室不妨簡陋,道路不妨泥濘。而獨在吃上,卻分毫不能馬虎。衣、食、住、行的四事之中,食的程度,遠高于其余一切,很不調和。中國民族的文化,可以說是口的文化。”夏丏尊的眼光獨到,抓住國民的心態,他將吃列為高于一切的位置。
端木蕻良寫的三個小文章,短小洗練,讀起來回味無窮。母親把一塊熱玻璃餅,放在一個小碟中,怕他燙著時,深情地說出:“我這‘老’兒子”,這個老字,濃縮高度的情感,此時發生裂變。清香的玻璃餅,不過是被一片樹葉包裹,但在端木蕻良的心中,卻是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