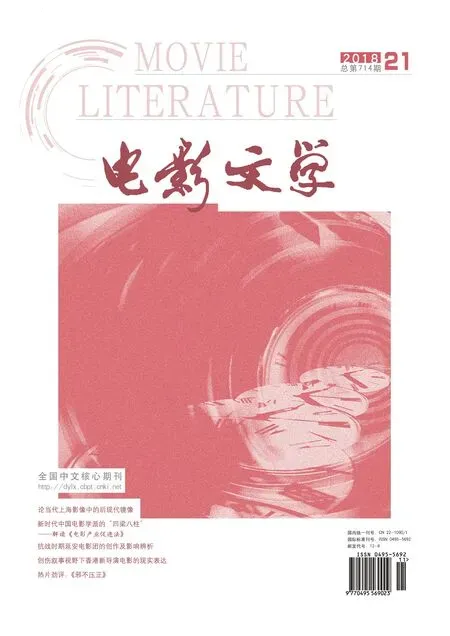抗戰時期延安電影團的創作及影響辨析
張 杰
(山東工藝美術學院 數字藝術與傳媒學院,山東 濟南 250300)
一、延安電影團的創立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促使國共統一戰線的形成。為了更好地應對戰時特殊環境下的輿論宣傳,在思想上有效統一戰線,1938年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在武漢正式成立,陳誠任政治部部長,周恩來任副部長。陳誠是黃埔系的職業軍人,副部長周恩來在黃埔軍校創立之初就擔任校政治部主任,是共產黨高層中主持文化宣傳和情報工作的專家。因此,抗戰宣傳的大部分工作實際上是由副部長周恩來和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具體負責的,逢此機緣,周恩來與奮戰在抗戰后方的文化工作者便有了諸多交流與溝通。
1938年8月28日,同樣通過周恩來的指示,有著“千面人”稱譽的上海電影演員袁牧之和攝影師吳印咸攜帶著他們剛從香港采購來的新設備,連同荷蘭紀錄片大師伊文思無償捐贈的“埃姆”攝影機、2000尺膠片,由武漢出發歷經艱難抵達八路軍總政治部報到,眼看人員、物資、設備日漸完備,八路軍總政治部延安電影團(簡稱延安電影團)在1938年9月正式宣告成立。延安電影團直接隸屬于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由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兼任團長,八路軍總政治部延安電影團是由中國共產黨所創立的首個電影制片機構,1938年正值建黨十七載,中國共產黨終于在延安革命根據地開展了屬于自己的電影事業。成立之初,當時電影團的全部家當包括:一臺由荷蘭電影導演伊文思捐贈的能拍35毫米膠片的“埃姆”;一臺16毫米的“菲爾姆”,購于香港;三臺相機,一臺是徐肖冰的,另兩臺是吳印咸拿出自己的積蓄買的,大家戲稱之為“兩呆三動”,條件可謂彌足艱苦。
延安電影團成立之初,僅有六名成員:參加過長征的李肅擔任政治指導員,袁牧之具體負責總體把握藝術創作,吳印咸和徐肖冰擔任攝影工作,而后又從延安抗大抽調來葉倉林和魏起。素有“千面人”之稱的袁牧之有著豐富的表演和編導經驗。1937年,袁牧之擔任編劇并導演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馬路天使》,這部由周璇、趙丹主演的電影被認為是中國有聲電影藝術走向成熟的標志。吳印咸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就在上海擔任電影布景師的工作,后來改為攝影,與袁牧之合作拍攝了《風云兒女》《都市風光》《生死同心》《馬路天使》。草創時期的延安電影團,具有電影從業經驗的成員僅有袁牧之、吳印咸兩人,而袁牧之和吳印咸都是從事前期制作,無法完成電影后期制作的相關工序。1939年后,電影團又相繼調入吳本立、馬似友、周從初、錢筱璋、程默等人。錢筱璋1933年后任“明星”“中制”“大地”等影片公司剪輯師。剪輯的影片有《十字街頭》《馬路天使》《孤島天堂》,紀錄片《抗戰特輯》等。周從初1932年即到上海明星公司學習洗印、錄音技術,是延安的膠片洗印專家。至此,人員的補充完整地銜接了電影團前期編導、攝影與后期剪輯、洗印的制作流程。
二、電影人的精神涅槃
像袁牧之、吳印咸這樣從上海的“亭子間”來到延安的電影人,是經歷了截然不同的兩種生活環境和思想意識形態的洗禮,在來延安之前,上海電影人在對待一部電影的創作方向上遵從商業市場的一般定律,拍什么,怎么拍具有一定的創作自由度,其他行業的文藝創作者也是如此。抗戰時期的延安實行的是戰時共產主義供給制,采取軍事化或準軍事化的管理,知識分子的自由創作身份在無形中被共產體制消解掉了,陜甘寧邊區所有出版機構、報紙、書刊甚至書店、紙廠都是公有的,因此,電影人隨同進入延安的其他文藝工作者一同被劃為了共產主義體制內的“公家創作者”。吃著“公家”的糧,穿著“公家”的衣,心懷崇高的共產主義革命理想,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延安時期電影藝術創作類型的固定模式。
1939年12月,毛澤東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闡明了知識分子對于革命的作用:“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許多軍隊中的干部,還沒有注意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還存在著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一切戰區的黨和一切黨的軍隊,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校,加入政府工作。要將具備了入黨條件的知識分子吸收入黨,對于不能入黨或不愿入黨的知識分子,也應該同他們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關系,帶領他們一道工作。”該決定加強了知識分子與黨的聯系和溝通,提升了知識分子在延安的地位。但也從思想和意識形態提出了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要求,強調知識分子的“自由化”思想要統一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下。中國知識分子的“革命化和群眾化”和“工農干部的知識分子化”論題的提出,是亭子間的知識分子如何融入延安農民文化中的問題;也是亭子間文人在延安農民文化和共產主義思想雙重洗禮下,從資產階級“舊文人”到為工農兵服務的“革命者”所必須經歷的精神涅槃。
以上觀點在毛澤東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論文《五四運動》中闡述的非常詳細:“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群眾相結合。”“愿意并且實行與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經過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共產黨領導下的多次思想和行為改造,從城市來到延安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終于在艱苦的勞動和思想歷練中,因獲得了“農民身份”,有了“勞動人民的情感”而重獲新生。
三、延安紀錄電影的類型溯源
延安電影團的電影創作并沒有遵從上海電影那約定俗成的“劇本—導演—攝影—剪輯”前后期規范化制作,“影片的具體內容和完整的構思是在拍攝過程中逐步形成的,這就是一面采訪熟悉生活,一面進行拍攝,一面完成整體構思”。這一方面限于延安電影團初期有限的電影制作能力,另一方面是由延安特有的政治環境決定的。
抗戰時期,延安獨有的公有體制是實行戰時的軍事化或準軍事化的管理,其特征是講求成員行動的高度紀律性與規范性。公有體制下的所有生活資料都歸屬于“單位”統一分配,而非延安以外的區域那樣,員工通過與雇主之間的約定獲取或多或少的勞動薪酬。在1943年整風審干階段,延安最桀驁不馴的作家蕭軍因其所屬的“文抗”單位被撤銷,在延安的蕭軍成了一個沒有“單位”的人。“蕭軍一家住的地方改為中央組織部的招待所,蕭軍實際上成了寄食者和寄住者,因與所長發生口角,被所長下了逐客令,蕭軍遂于1943年12月上旬到延安縣川口區農村落戶,12月底延安縣長來通知今后停止大人孩子的所有供給,這實際上等于開除了蕭軍的公職,蕭軍不得不暫借老鄉的糧食過冬并計劃來年春天開荒種地維持生計,但開荒種地對慣于拿筆的知識分子而言談何容易,多虧了老鄉們的熱情幫助,蕭軍一家東挪西借才勉強維持到1944年3月。后來胡喬木以路過的名義來探望蕭軍并請其回城,蕭軍于3月7日回到延安,參加了黨校三部的文藝界組織,他的公職也就恢復了。這次下鄉充分顯示了蕭軍的氣魄和個性,但同時也使他明白離開了‘公家’的日子不好過。在中央黨校期間,蕭軍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外來知識分子在生活配給上的標準化使得個體對于生活、理想的趣味、需求漸趨同一,正如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成員趙超構在實地考察延安時所指出的:“這是由于生活決定了意識,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在近代城市資本主義土壤中生長并繁榮的中國電影,到了延安的公有制環境中,自然就剝離了電影的商業屬性。電影的創作標準及取向不再以由個體審美意識組成的觀眾群體喜好為衡量尺度。在公有制與軍事化主導的延安生活環境中,電影的政治意識形態屬性被放大并成為延安電影的唯一歸屬。而適用于政治意識形態宣傳最為直接、最具時效性,且又最能節省資源的便是影像的紀錄形態。
另外,抗戰時期的延安電影團不僅電影專業人士相當有限,所持有的膠片總共才只有1.8萬尺,如果裝載16mm電影攝影機只能拍攝總共大約500分鐘素材,35mm則減半,對于像袁牧之、吳印咸這樣的上海電影人來說,在延安拍攝電影,每一尺膠片都彌足珍貴。因此,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延安電影團都不具備拍攝故事片的條件,而如果站在觀眾接受的角度,對于邊區文化理解水平普遍較低的農民群眾來說,紀錄影像畫面配合解說詞的視覺表達方式無疑是最通俗易懂的“大眾化”表達方式。毛澤東曾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延安文藝作品的大眾化論題,將知識分子“不懂聽眾的語言”闡釋為延安知識分子急需解決的溝通問題:“什么不懂?語言不懂,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么叫作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么文藝創造呢?”在這里,溝通語言的障礙是指在文藝工作者的作品與工農兵的接受認知之間的障礙,自然也包括電影創作者的電影作品。而毛澤東所提到的“大眾化”與孤島電影和香港電影的娛樂“大眾化”有著本質的區別,延安“大眾化”的組成主體是農民,同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主導的城市文化相比,鄉土氣息中的審美體系和言說方式迫使延安電影的創作主體要首先破除亭子間的、資產階級舊文人式的商業娛樂化表達。而直觀、質樸地記錄陜甘寧邊區生產生活的影像語言,無疑就是最適合工農兵聆聽的大眾視覺,反而這種全新的大眾視覺語言應該是更加靈活、自由的,它也不應像上海電影那樣受到商業創作模式的限制。
四、《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的意識形態表征
抗戰時期的延安共拍攝了《延安與八路軍》和《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又名《南泥灣》)兩部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攝于延安電影團成立之初,導演袁牧之早就構思過要拍攝一部反映延安和八路軍生活風貌的紀錄片,讓生活在陜甘寧邊區及邊區以外的人們能夠更深入了解延安與八路軍隊伍。袁牧之負責影片的編導工作,吳印咸擔任電影攝影,這部延安電影的開山之作僅拍攝就耗時1年又7個月,袁牧之把影片的內容分為延安生活和八路軍生活兩大部分,1940年5月,袁牧之和冼星海帶著《延安與八路軍》的大部分底片趕赴蘇聯完成后期制作。但不幸的是,由于蘇德戰爭的爆發,《延安與八路軍》的底片遺失。新中國成立后,八一電影制片廠曾派陳播至蘇聯尋回少數殘存的珍貴鏡頭,但確已無法恢復影片原貌。
根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共同主辦《黨的文獻》雜志2007年第1期所載文章《延安文藝座談會參加人員考訂》所查,吳印咸是唯一一位延安電影團的與會代表,他同時又負責整個活動的拍攝工作,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現場講話應該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因此《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的主要編導創意應該直接來自吳印咸,而王震率領的一二○師三五九旅在南泥灣實行的墾荒生產運動恰好為“藝術為工農兵服務”這一核心思想提供了再合適不過的影像素材。受當時洗印條件的限制,這部使用16毫米膠片拍攝的紀錄片畫面質感略顯粗糲,整部影片除王震在開場不久后和毛澤東在片尾處有幾個單人近景鏡頭以外,13分鐘的影片大部分都是用來表現在南泥灣進行墾荒屯田“工農兵”群眾的,凸顯了政治宣傳的目的,影片從介紹延安的景物鏡頭為開場,大致分為以下情節結構推進。
1.以全景的圖式展現延安風貌,寶塔山—窯洞—延安全貌。
2.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召開干部會議,制訂開荒計劃。
3.農民身份的轉換:浩浩蕩蕩的戰士隊伍在遍地荊棘的南泥灣駐扎下來,適時開荒種地,播種豐收,荒地變為良田。
4.工人身份的轉換: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戰士們在開荒生產的同時,自己挖窯洞、蓋房子、架設橋梁,戰士們利用柳條、樺樹皮編制各種生產生活上的日常用品。戰士們上山伐木材,制造車床;辛勤的雙手不僅可以滿足拓荒的需要,又會紡紗織布;為了政治學習的需要,戰士們用馬蘭草制成紙張,學習革命精神。
5.戰士身份的回歸:三五九旅貫徹農忙時小訓練、農閑時大訓練、突擊生產時不訓練的原則,嚴格的軍事訓練鍛煉了戰士們鋼鐵般的意志。而聲勢浩大的騎兵隊伍充分表明共產黨已經為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做好準備。
6.頭戴斗笠的工農兵在南泥灣的萬畝良田中收割豐收的果實。一垛垛糧食被整齊的隊伍運出田地,成了工農兵們桌上的菜肴。在工農兵的雙手中,南泥灣從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變成了“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陜北好江南,三五九旅是學習工農兵精神的模范,這一切都是因為毛主席和黨中央為中國革命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影片的最后出現了毛澤東的多個單人近景鏡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則明顯地意指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在《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中,影像的意識形態表征顯然是經過精心布置的,質樸的鄉村影像表達完全區別于城市電影中的摩登與喧嘩,英國著名的文化理論家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雷蒙·威廉斯在其著作《鄉村與城市》中表述了鄉村和城市的兩面性:“鄉村和城市,沒有固定的意象、意義和表征,它們在不同的背景中意味著不同的東西。鄉村可以是18世紀英國油畫中美麗的田園詩,也可以是旅游者手冊中令人激動的荒野……也可以被看作是單調和落后的,卡爾·馬克思曾經稱之為‘農村生活的極端愚昧’。相反,城市可以被看作是興奮的和愉悅的地點,或者是罪惡與危險的所在——同時具有肯定和否定的兩面。”《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這部看似簡單、通俗的紀錄片正試圖通過“工農兵”形象的闡釋來建構一個積極向上的延安精神的語言價值體系,從開場處反復出現大的延安精神象征物——“寶塔山”,逐漸過渡到對“工農兵”的行為闡釋,這些既是工人、農民,又是士兵的三五九旅革命戰士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開荒、種田、織衣、造紙、修橋、鋪路……樣樣拿手,無所不能,最終憑借堅韌的精神力量撼動了看似不可逆轉的自然定律,把貧瘠荒涼的南泥灣神奇地改造成了富庶之鄉。
《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組織了一系列連續且富有韻律的視覺符碼,在這部紀錄片的初級指意系統中,所指的是戰士們創造了一個富饒美麗的南泥灣;而在次級指意系統中,所指則表述了一種蓬勃向上的、極具正能量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通過對《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抗戰時期的延安試圖通過影像的視覺表達建立一套適合解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以用于與國民政府代表的城市資產階級文化進行對抗。正如雷蒙·威廉斯在《鄉村與城市》中所提到的那樣,上海電影的摩登與時尚被解釋為奢靡與揮霍,罪惡與昏暗。在大后方生活的左翼作家們則習慣性地把重慶描述成一座“雨霧籠罩下的黑暗之城”,在他們筆下有荒淫無恥的達官顯貴,他們以權謀私、中飽私囊,在色欲、物欲、權欲上表現出無比的貪婪性,在本質上與漢奸實屬無異。還有暴發戶和太太小姐們的紙醉金迷,他們在醉眼蒙眬中大發國難財,在交際場合的假面扮相中盡展丑惡心態。左翼作家筆下的各色人等都帶有明顯的符碼特征,這些有著模式化創作傾向的人物符碼把重慶塑造成了光怪陸離的灰暗地帶。而延安革命精神的成功闡釋則吸引了大批知識分子,在重慶躲避追捕的馮蘭瑞,在接到南方局轉達批準她去延安的消息時,高興得跳起來,理由相當樸素:延安沒有盯梢的,延安吃飯不要錢,延安是自由、民主之地。“根據美國學者約翰·伊斯雷爾和唐納德·W·克萊因的統計,至1938年末,等待批準進入陜甘寧邊區的青年學生有2萬人。到20世紀40年代初期,延安已經形成了一個約4萬人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最終構成了新中國文藝建設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