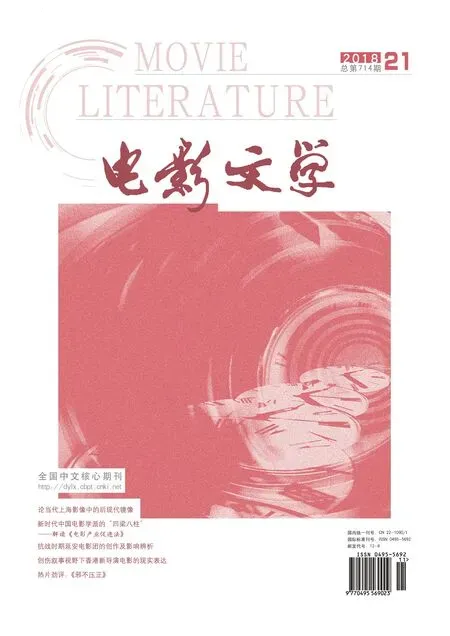論臺灣新新電影中的在地文化空間
劉 騁
(中國計量大學 人文與外語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全球化實際是一種將資本主義相關的各種形式的社會空間組織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和相互交織,這種空間的組合為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流通提供重要條件,帶來的不僅是全球城市空間的同質化,而且會造成全球文化的標準化(美國化),地方文化面臨潰敗,甚至人們的民族生活方式亦可能遭受破壞變得同質性。正是懷著這樣的擔憂,全球化的書寫在后現代化國家或地區處處遭到抵抗。反抗的策略是制造與堅守區域化的差異空間來對抗同質化空間,并賦予區域化、本地化空間以自由與精神慰藉的“烏托邦”的性質。
這種轉變在《海角七號》之后尤其突出。在新新電影中的在地文化空間想象與20世紀70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爭中 “鄉土”概念有著密切的聯系,是將“鄉土”變異拓展后衍生的概念。在新新電影中“鄉土”突破了80年代臺灣新電影中所指稱的與城市相對的內涵,更具有與西方乃至與中國相對的意涵,于是鄉土被拓展為與“在地”“本土”“臺灣主體性”互換的轉喻,并從地理的空間發展出心理的空間。因此所謂鄉土/在地的文化空間是指臺灣以“本土”為核心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包括臺灣宗教信仰、飲食文化、建筑風格、自然景觀、民俗傳統以及多元族群的聲音語調等可以展現“在地意識”的空間,筆者認為就是文化意義上與地理意義上雙重的臺灣人的故鄉。這種所謂在地化的鄉土化的空間本身所蘊含的歷史以及意識形態就是新新電影念茲在茲的“臺味”,也就是臺灣主體性彰顯與生成的場域。在這樣的一個轉喻的鏈條上,制造出鄉土空間/在地特色/文化景觀,并盡力凸顯臺灣的異質性,是引發臺灣民眾高潮,獲得身份認同的G點,亦是當下新新電影最為招人的賣點,所有新新電影票房的成功莫不與此相關。
一、在地人文空間
筆者將非自然空間之外的,由人類創造的文化世界稱之為人文空間,為人類生存的非物質性為主的文化/精神空間,具有心理情感性、精神性,歷史性、地域性,人是其中的核心,不僅因為人的身體就是人文空間的一部分,而且人文空間可以看作是人類精神氣質的外化,是外感官的直觀形式。新新電影中在地文化空間主要通過草根精神、民俗奇觀、飲食文化、宗教儀式、地方語言音樂美術等方面來呈現。
比如魏德圣《海角七號》里在地空間的呈現除了好山好水的自然景觀,更多的是在地的人文景觀的營造。有一段饒有意味的對話,恒春的鎮長說:“現在時代在進步,要有國際觀念,要有地球村的觀念。”針對此言民意代表主席說:“什么地球村,你們外地人來這里開飯店,做經理,土地要BOT,山也要BOT,連海也要給我BOT。我們在地人呢?都出外當人家伙計。”這表達出缺失了在地人的美好的家鄉/空間將被外來經濟/文化侵占引發的憂慮,也是面對全球化資本沖擊下本土群體喪失“自我”的恐懼,反抗的武器就是建構本土化的人文空間,也就是必須在家鄉空間里填充進在地人,構筑在地人對吾鄉吾土的認同,這樣才能從空虛到實有。所以民意代表希望年輕人留下來建設鄉土,并強力支持組建一支恒春本土的業余樂隊作為演唱會暖場的樂隊。這支樂隊可以看作是“在地人文景觀”的烏托邦呈現,不同世代(三代人使用的樂器古今雜糅)、不同族群(客家、閩南、原住民)、跨越國界(中日)組成的樂隊展現后現代奇觀:混雜性、差異性、多元性、國際性的文化沖撞與并置,最后統一在“在地性”的意識形態的訴求之下,偷渡臺灣族群撕裂現實而為觀眾呈現多族群可以達成多元性和諧共處的人文景觀愿景;樂隊成員來自各行各業的失意小人物,共同努力達成夢想的結局凸顯臺灣草根的生命力觀眾在這種草根神話中尋找到自我存在感,呼應高漲的在地意識,獲得身份認同;樂隊各族群成員中外省人的缺失意味著臺灣在地人文景觀試圖漸漸稀釋中原文化的濃度,而有意讓日本人的加入則除了刻意展現跨越國界的眼光之外更將媾和的欲望融入身份想象,如此種種,營造出臺灣深具的多元、“包容性”、開拓性、充滿活力的臺灣文化的精神氣質——在地人文空間的內在魂魄。這就是阿嘉所追尋和回歸的精神家園/空間。
這種人文精神空間的塑造同樣呈現在葉天倫的《雞排英雄》(2011)中。影片將臺灣文化的精神氣質附著在臺灣世俗空間——八八八夜市和底層小人物的擺攤生活中,是一部以“臺灣味”取勝的影片。雖然電影沒有表明故事發生的具體地點,夜市也是虛構的,但是從夜市的形態可以明確是臺灣南部的夜市,同樣暗合著南部建構在地文化空間的想象,引人注意的還有夜市被劃分為臺北、臺南、彰化、高雄以及美食聯合國等區域,服務臺前有臺灣地圖,顯然夜市是被作為凝縮的虛擬空間來像喻臺灣的。(臺灣夜市一般分為兩種形態:一種是街道型,店面是從臨街的一樓向四周擴散,比如臺北的士林與通化、臺中的逢甲等;另一種是空地型,就是在空地上到夜晚攤販自行聚集,這種夜市多在臺灣南部,比如高雄的瑞豐、臺南的花園等,八八八夜市屬于后者。)八八八夜市熱氣騰騰,人聲鼎沸,燈光璀璨,擺攤的老板都是草根小民,為謀生互相競爭但是也相互幫襯,一派世俗熱辣的生活場景噴薄出濃郁的人情味、生命力和世俗草莽氣——也就是所謂的“在地精神”。在巴赫金看來,在吃美食的活動中,人與世界的相逢是歡樂的凱旋式的,由于原始時期集體在與自然世界爭奪食物獲取勝利后往往要飲食歡慶,因此吃喝飲食與歡慶勝利的集體無意識就深入到人類的基因中,并具有狂歡的意味;同時吃喝是人類的基本訴求,不僅建構強健的身體,而且從本性上具有強烈的非官方性質,飲食與歡笑與“任何的現實的官方嚴肅性對立,從而造成親昵的人群”。從這個角度來看,夜市作為生產加工美食以及老百姓吃喝的場所,就成為草根族群身體反叛與狂歡的空間。當運行城市更新計劃夜市面臨拆遷之時,他們團結在夜市自治會會長(投票選出來的,意味著臺灣的民主)陳一華身邊,高喊“拯救八八八夜市,拯救在地精神”的口號,顯然電影將小攤販的勇于反叛斗爭、眾志成城和一致對外的精神氣質外化為“在地精神”,與作為臺灣濃縮空間的夜市一同構建出在地精神空間,這是臺灣人生存之根基,最終以庶民勝利狂歡的結局講述了基于在地人文空間的勝利神話。
另一部將飲食吃喝與塑造“在地精神空間”聯系在一起的影片是陳玉勛《總鋪師》(2013)。與《雞排英雄》從吃喝中尋找草民的反叛精神不同,《總鋪師》則試圖在飲食中尋覓臺灣文化的傳統之根,在“在地文化”的空間基礎上試圖延長臺灣歷史/時間。為此影片用傳奇的方式(比如三百年的醬油、人、鬼、神三大總鋪師)刻畫總鋪師的三代師徒譜系,并借用吳念真的出場凸顯歷史記憶的連續;同時電影將美食的最高訴求歸之為古早味,詹小宛尋找古早味就是尋找臺灣文化的原初,而通過美食技術的失傳與重獲之路表達年輕世代對歷史的傳承。需要注意的是影片所呈現的“美食”都是平民化的,諸如炒米線、番茄炒蛋、菜尾湯這類庶民美食、家常食品,以此傳達出臺灣文化的草根性、世俗化特點。總之電影用色彩明亮鮮艷的鏡頭語言,嬉笑打鬧的喜劇方式為我們刻意呈現俗辣鮮活、飽含人情溫度與歷史意味的臺灣本土人文空間。
真正為本土人文空間賦予“歷史感”的是鈕承澤的《艋胛》(2010),這是一部講述幫派斗爭并隱藏著身份訴說的電影,影片的成就之一是將過往的時間空間化,以浮世繪的方式重塑了20世紀80年代的艋胛(臺灣最早的居住地,是臺北曾經最繁華的三市街之一,本意是平埔族語小船的意思)風貌,將后壁厝和廟口的楚河漢界,角頭紛爭的歷史搬上了銀幕。影片為我們展現了艋胛喧嘩熱辣的草根世界/空間,使觀眾從文化歷史空間中重溫曾經的集體記憶,尤其是由花襯衫、喇叭褲、墨鏡、人字拖構成所謂的“臺客文化”背后蘊含的尚勇斗狠的男性荷爾蒙,為“在地文化空間”賦予了父性陽剛氣質,這是其票房的成功最重要原因之一。
為在地人文空間賦予陽剛氣質和自我革新精神的還有馮凱的《陣頭》(2012)。電影將臺灣民間信仰中神圣的儀式——“陣頭”搬上銀幕,作為一種鄉村藝術表演,陣頭多出現在廟會酬神等宗教民俗活動中,形式包括舞龍舞獅、八家將、融入現代元素的電音三太子、電子花車等。這些民俗宗教中往往與幫派有著聯系,因此體現出江湖氣和陽剛氣。電影描寫阿泰以執著的信念和改革的勇氣,帶領著年輕一代將三太子和八家將等臺灣民俗宗教活動予以新的生命力,并作為首演受邀參加了臺中國際(有西方人面孔)文化節,以青春血勇之氣,奔放現代之態呈現在世界面前,用生命與存在的吶喊表達“不一樣”的自我,完成了“被看見”“被注意”的愿望。經過年輕世代改革后陣頭不僅消弭了上一代的仇恨,而且最終年輕一代終獲父輩認同,現代與傳統達成諒解,完成了年輕一代對傳統臺灣本土文化的繼承。總之影片以陣頭這樣的傳統宗教民俗展現的人文空間,成為臺灣人精神之“家”的象征,挖掘其中包容、開闊、革新與陽剛的臺灣本土文化的精神,并將現代性注入傳統之中,使傳統與現代融合,以特殊性和被看見為訴求,譜寫了一曲在地文化的浪漫小夜曲。
這種營造“在地人文空間”類型的臺灣新新電影明顯受到《海角七號》的影響,基本是在其敘述模式的基礎上修修補補的產物。比如電影基本都有一個從臺北回歸或者固守“在地空間的”的模式。年輕的主人公都是失意者小人物,《總鋪師》中的詹小宛在臺北打拼,想成為一名模特,《陣頭》中的阿泰本來在臺北學習音樂,最后都與《海角七號》中的阿嘉一樣在臺北落敗,背著行囊被迫返回故鄉/鄉下。這個模式中臺北作為全球化都市空間被隱喻異化為生命之場所,在臺北無法找到生存的家/空間,逃離的目的地是南部故鄉,暗示著在地文化空間與南臺灣之間的精神關系。在臺灣的政治版圖上,北與南分別代表著藍與綠的鮮明對立空間政治格局。臺北為中心的北部被看作是外來政權統治臺灣的政治中心,并且作為經濟最為發達的地方,由于聚集了大部分的“外省人”,體現著典型的漢族中心主義,而南高雄為核心的周邊多聚集著“本省人”和高山族群等所謂“在地人”,其身份認同指向為臺灣中心主義,因此在影片中阿嘉們的從北到南不僅僅意味著從身體在都市的錯置中回歸精神的原鄉,也意味著從漢族中心的文化空間向“本土文化空間”的臺灣性回歸。這種轉向在新新電影中成為重要的空間修辭手法。再如主人公在故鄉陰差陽錯之中都被迫以領導者的身份或重操試圖逃離的父輩舊業,或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沒想到卻由此改變命運,阿嘉回到恒春做了一名郵差,被要求在短期內組織一支業余樂隊;小宛則不得不像父親一樣做總鋪師,代表臺南參加了臺北的辦桌大賽;阿泰被一場賭局推上了九天鼓隊的團長,不彈吉他,做陣頭改敲鼓,最后主人公都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獲取了生活的目標并遇到愛情,講述一個圓滿的本土人文空間神話。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電影在聲音表達上都采用以閩南語為核心的聲音景觀,以凸顯與國語(普通話)為核心的文化空間的差異性;同時在營造在地人文空間的同時都包含青少年的成長主題與父子沖突的模式,通過青年主人公的眼睛重新審視“在地文化”(審父),在經歷最初對鄉土文化與傳統(父親)的不屑、厭煩、矛盾之后,通過發現、獲益,最終認同了在地性,與之達成和解并完成主體的成長。可以說主人公的成長之路就是回歸、發現與呈現“在地人文空間”之內涵和魅力的精神歷程,亦可以看作是“尋父”“認父”的精神歷程,這與侯孝賢《童年往事》、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李安《喜宴》、蔡明亮《河流》、張作驥《美麗時光》等影片中所展示的下一代對父輩(外省人身份)的審視甚至“弒父”的精神向度顯然不同。由于“父親”的在地/本省的身份印記,在地人文空間與精神之父互為指涉的像喻關系,這些新新電影中傳達出認同父親/在地的新走向。影片中的年輕生命在本土人文空間之中獲得智慧和生存意義的滋養,最終認識并完善自我,回答了自20世紀80年代新電影以降臺灣電影所刻意追尋的“從哪里來”的歷史命題,而本土人文空間因年輕生命的注入得到拓展與新生,也解答了“到哪里去”的方向困惑。這些影片在建構本土人文空間中有著同質化的敘述痕跡,筆者認為除卻臺灣電影原創精神的匱乏和視野狹窄的原因之外,更應該關注的是埋藏在相似性敘述框架之下的精神內涵——都是臺灣身份的國族寓言,這也是臺灣電影逃不出去的宿命表達。
二、自然地理空間
自然空間與人文空間共同構建出臺灣的文化空間,如果說人文空間是臺灣人的精神家園與心理空間,那么地理空間就是臺灣人精神家園的物質載體——地理空間的家園。新新電影在新世紀之后對于在地空間的表達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美化在地/鄉土空間,除卻上文論述的精神家園烏托邦化,其對自然地理空間的表達由于刻意排除了其自身具有的危險力量亦呈現出詩意與理想化特點。新新電影從楊德昌、蔡明亮描繪的狹小封閉的現代都市空間逃離,在廣闊的自然空間中舒展被壓抑的心靈和身體,在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中使身體與精神得到療愈。臺灣美麗的自然風光是臺灣精神與氣質的源頭,也是發現自我,尋找自我,建構昂揚、自信、舒展自我的場所,這樣自然地理空間就具有精神與文化的意味,與在地人文空間共同構成臺灣人的原鄉。
首先,是通過由城市到鄉村自然的空間轉換表達主人公對現代城市以及學校教育壓抑人性和自由的厭惡,自然空間成為現代人逃離都市、學校為代表的壓抑空間獲得精神庇護和慰藉之地。比如陳正道的《盛夏光年》、九把刀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李啟源的《河豚》、陳玉珊的《我的少女時代》、張柏瑞的《志氣》,人物總是在學校、家庭或者工作場所受挫之后,來到阡陌縱橫的鄉間,在起伏的丘陵、滿田野的野花、波光瀲滟的水面、鵝黃嫩綠的稻田、飛舞的蜻蜓所構成的自然空間中獲得心靈的釋放。善于描寫生存逼仄空間的張作驥,為身體困境尋找的出口在《美麗時光》中設置為宜蘭的大海(空間),影片最為精彩的一幕是當小偉和阿杰兄弟二人被仇人追殺無路可逃只能跳到家門口那條黑水溝中,此時原本污濁的水幻化成一片清澈蔚藍的大海,寬闊浩渺的大海使人的生命得以片刻的舒展,宜蘭因此具有原鄉的意味,療救枯萎困頓的生命,在空間的轉換中暗含著影片的精神向度。
其次,展現自然地理空間最為重要的方式就是環島旅行,通過人在客觀空間的位移,將臺灣的自然景觀一一呈現,并且串聯起整個臺灣島的空間,使觀眾獲得臺灣在地空間的家園感和認同感。
通過環島展現自然空間的電影比較早的是李志薔的《單車上路》(2005),電影展現的是蘇花公路沿途的壯美風景,把青春陽光、美景融合在一起,引導觀眾一寸寸地審視腳下的土地。還有林靖杰的《最遙遠的距離》(2006)通過三個遇到人生困境的人進行一場身體的旅行,從都市逃離不約而同在東臺灣的好山好水中獲得心靈的寧靜。臺灣的山水成為修復創傷獲得新生的療愈之地。不過在自然空間與療愈之外真正賦予環島自然空間以文化精神氣質的始于陳懷恩的《練習曲》(2006),主人公明相從臺東出發,經過七天六夜的騎車環島行再回到臺東,途中遇到的人和事串聯起整個敘事框架。之所以這樣來設計旅行的方向,導演認為“臺東的太麻里是臺灣最早的日出,對于臺灣任何事物的生長都有重要意義”,可以獲得一種重新的開始。主人公在這個具有新生意義的騎行之旅中不僅得到了精神慰藉,更獲得對于臺灣及自我的認知。影片刻意營造新鮮明亮干凈清澈的光影效果,將臺灣的自然空間櫥窗化展示,也滿足了觀眾的“在地化”想象(影片唯一的都會景觀是用俯視鏡頭呈現的高雄)。行走有如人生,美麗臺灣是人生的寄托之地,更是臺灣人熱愛的故鄉。同樣的環島電影還有澎恰恰的《帶一片風景走》(2010),故事主要講述了工人智輝與患小腦萎縮、人生所剩時間不多的妻子秀美,為了留下最美好的回憶和不虛此生而進行一場感傷而美好的環島旅行,智輝推著輪椅上的妻子,兩個人在臺灣大自然風光中緩慢地行走,這是一場將生命融入自然空間的旅行,智輝為妻子講述沿途荷蘭、西班牙以及日本殖民時期留下的空間遺跡(福柯稱之為補償的異類空間),在歷史空間尋找身份,在自然風光中療傷。通過臺灣的海風夕陽獲取心靈的寧靜,生于斯而葬于斯,足下的土地是臺灣人的源起與最后的歸宿,表明了對這塊空間的認同與熱愛,并賦予臺灣地理自然空間以生命本原的意義。
《陣頭》是一部將自然空間與人文空間結合很好的影片,電影中最為關鍵性的一個場景就是阿泰帶領著團隊,背著鼓進行一場環島行走。在行走過程中城市、鄉村、平原、高山、海濱構建出臺灣美麗富饒的自然空間。正是自然空間賦予了鼓隊創作激情和靈感。他們看到了太平洋,裸體縱身投入蔚藍色的大海,自由遨游,他們共同努力翻越高山,他們在大海的沙灘上打鼓,背后是浩瀚的海洋,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是在地人文景觀與在地自然景觀的合一,也就是所論述的在地文化空間的圖像化。鼓隊在自然中鍛煉了身心,汲取了養分,發現自我、完善自我并張揚了自我,當自我與自然合一,達到物我兩忘,他們的陣頭就“不用開臉,不用扮裝,不用請神明”,他們就是哪吒三太子,他們就是在地精神,他們就是臺灣,在這里影片用藝術化的方式為我們呈現自然空間并不僅僅是客觀的外在于人的空間,而是可以賦予生命和精神的空間。
對于臺灣好山好水的自然空間營造與展示,直接催生了一個新新電影中的類型:觀光影片。這也是受到了《海角七號》熱映帶來的墾丁旅游熱潮的影響。這類影像是經濟政治文化融合的產物,畫面明媚,清澈,有俊男美女加持,拷貝《海角七號》某些模式,往往借用一個諸如戀愛的框架,行銷臺灣在地風光。不過與《海角七號》借愛情故事偷渡殖民歷史的吊詭不同,這類影片著重以小而美的風格營造當下“小確幸”的臺灣幸福感,推進旅游收入的同時,也塑造新臺灣形象,激發愛臺灣的在地情懷。比如林育賢《對不起,我愛你》,日本女明星田中千繪(在《海角七號》中的女主角,似乎想延續海角帶來的熱度)飾演一位來臺灣學習的日本留學生與本土青年相愛的故事,爛俗的框架下,展現高雄風光。是一部風光做主角的電影。同樣的情形還有展示臺南迷人的古舊風味的《夜夜》;展示金門風光的《星月無盡》與《夏天協奏曲》;而《跳舞時代》則將云林的西螺老街,浸信宣教神學院等具有懷舊色彩的風光呈現出來。這類影片極力將臺灣自然空間景觀圖像化,成為建構臺灣空間的一個重要圖證。
臺灣新新電影的在地文化空間是基于鄉土與庶民/草根指向而建構的空間,對故鄉的浪漫化想象,使在地文化空間魅力十足,這里風景絕美、民風淳樸,充滿了人情味和原初的生命力,與逼仄、隔絕、荒蕪冷酷并造成孤獨自我的城市空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地的民俗以及日常生活歷史所蘊含的“傳統”與精神彰顯臺灣人的身份意識,并且在傳統中注入現代化因素,形成所謂具有“海洋意識”的空間,使之成為草根得以施展抱負,并能夠在全球化中尋找到自我存在意義、實現主體價值的場所;同時當身體走出隔絕,與“在地文化空間”融為一體,會產生類似回歸母體的自得其樂,逍遙自在的幸福感,因此,在地文化空間不僅是凝聚著國族身份認同的場域,并且是展演身份想象的烏托邦場所。
由于本土/在地文化空間與庶民、民族成為互為指涉的關系,都是所謂“臺灣自己/本土自我”的殊異性表達,空間影像轉化為一種政治語言,呈現出抵抗性和自戀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建構臺灣文化空間就是一個臺灣自我主體的轉喻,根本目的是以之對抗外來支配性的他者——西方帝國主義或者中華文化的空間壓迫,可以看作在“后現代”多元、差異、碎片化的外表之下建構一個整體性概念——“在地性”的空間呈現。
注釋:
① 對于臺灣新電影之后的稱謂和分期有爭議,學界一般將《光陰的故事》(1982)、《兒子的大玩偶》(1983)作為臺灣新電影浪潮的開端,1987年《臺灣新電影宣言》作為新電影的終結。焦雄屏在《臺灣電影90新新電影浪潮》一書中指出臺灣電影在80年代后期與90年代初期在主題、美學及世界觀上都呈現相當的變化,老的導演在進行新的嘗試,新的導演勇于與舊的體系暌離,并斷言臺灣新電影的第二次浪潮形成,將之命名為“臺灣新新電影”,或者臺灣新新浪潮電影,有學者稱之為“后新電影”,新電影之外/后,這些指稱均指向自20世紀 80年代新電影結束之后所生產創作的臺灣電影,作者本人基本認同焦雄屏的命名。
② 新電影中“鄉土”體現為與城市/現代相對立的概念,被描繪為受到現代工業文明所腐蝕的空間,即使滿含留戀,個體/臺灣為了成長從“落后”的鄉村空間轉移到代表著“先進”的現代都市文明空間是不可逆的歷史走向,因此關于鄉村的書寫大多是唱一曲哀婉的牧歌。
③ 侯孝賢的《東東的假期》展示出自然是溫柔與兇猛并存力量,張作驥《假期作業》也展示出自然吞噬生命的可怕性,但是大部分以歌頌在地性為目標的新新電影顯然有意避免對在地人文與自然空間進行現實主義的關照,而是對其進行浪漫主義的裝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