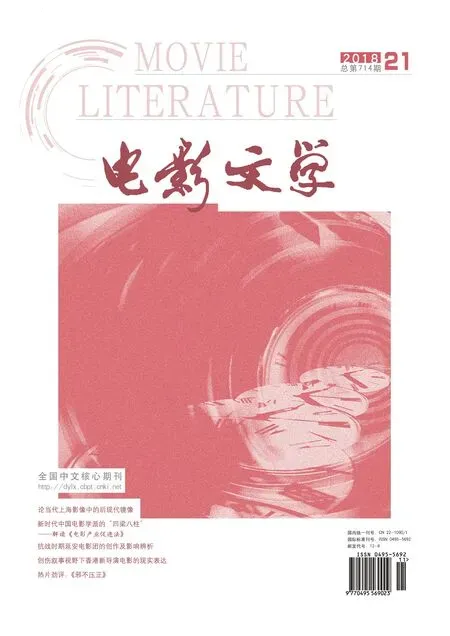中興期李行電影:子一代的“鄉土”回歸
袁晚晴
(西安文理學院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5)
20世紀70年代,蔣經國開啟民主政治革新之旅,臺灣經濟也隨著“十大建設”迅速騰飛發展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劃時代巨變必然體現在電影創作之中。70年代的臺灣前后出現了一批以人道主義立場關懷底層民眾,以回歸鄉土的創作傾向抵御西方現代文明的作品,如陳映真的《將軍族》《夜行貨車》,王楨和的《嫁妝一牛車》,黃春明的《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只老貓》等。70年代末80年代初,臺灣剛剛經過鄉土文學的第二次大論戰。70年代臺灣地區鄉土文學的本質是現實主義文學,偏重于文學的社會功能,隱含著或直接表現出對社會和文化的批判,體現出鄉土作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李行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奉持者,一向注重電影的“社會功能”和“教育功能”,李行第二階段的創作滲透著對傳統、民族及國家的認同觀念。
一、身歸鄉土:從城市到鄉村
1978年,李行又重新把目光投射在廣袤的鄉土之上。《汪洋中的一條船》《原鄉人》《小城故事》《早安臺北》四部影片再次把李行推向臺灣電影領航人的位置。鄉土社會有一種生于斯、長于斯的內在穩定性,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相比,農耕人口的流動性比較低,人們在肥沃的農田上世代耕種、繁衍形成村落。年輕一代的人往往會產生脫離鄉土的想法,城市化與現代化像彩色糖紙般包裹著巨大的誘惑。作家路遙在小說《人生》中刻畫的農村知識青年高加林渴望脫離鄉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走向城市,最后卻不得不失意地返回鄉土。同樣,李行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鄉土電影也刻畫了一批有知識的年輕人,《汪洋中的一條船》中的鄭豐喜,《原鄉人》中的鐘理以及《小城故事》中的陳文雄,《早安臺北》里的葉天林和唐風,這些作品中皆體現出了年輕人對鄉土與傳統秩序的“回歸”,這種對鄉土的依戀和對傳統的回歸具有極大的主動性,體現了一種天然的親近性。
農民之子鄭豐喜因小兒麻痹落下雙腿殘疾的毛病,歷盡波折后考上了中興大學法律系,與同學吳繼釗相愛。兩人不顧家人反對結婚后回到鄭豐喜的家鄉教書,出版小說《汪洋中的一條船》使鄭豐喜的事跡廣為流傳,獲得了臺灣十大優秀青年的稱號。電影《原鄉人》由鄉土文學奠基人鐘理和自傳性著作改編,鐘理和與在鐘家農場做工的鐘平妹相愛,但客家風俗不允許同姓的人結婚,他便離家出走遠赴沈陽求學,后帶著鐘平妹私奔到沈陽。抗戰勝利后,鐘理和帶家人回到家鄉美濃,在與病魔做斗爭的過程中寫出了《故鄉四鄰》《原鄉人》等鄉土文學作品。鄭豐喜與鐘理和的人生軌跡都體現出了“鄉土—城市—鄉土”的路徑,能夠在城市生存卻選擇主動回到與自己有著血緣之親的鄉土社會之中。鄉土不是無瑕的美玉,存在著封閉、陋習與不公。鄉土也曾帶給他們傷害,鄭豐喜六歲時被父母遺棄又在大雨中險些喪命,鐘理和因為“同姓不能結婚”的封建陋習不得不遠走他鄉,但中國人心中對于故土的眷戀始終是令人魂牽夢繞的情結,兩人在家鄉結束生命也是落葉歸根。在傳統的中國文化里,如若不能死在家鄉,便是“客死異鄉”,萬分凄涼,只有想辦法把身體或骨灰帶回家鄉安葬才算“魂歸故里”。
《小城故事》里的陳文雄在監獄中結識了老雕刻匠賴金水,陳文雄出獄以后放棄了讀大學的機會,也拒絕了富家女友林月華的求愛,毅然決然地去鄉下和賴金水學手藝,最終與賴金水的女兒啞女阿秀相愛。在陳文雄心里城市是嘈雜的,林月華熾熱的愛,蘇醫生耀眼的前程還有虐待姐姐的姐夫的暴力都讓剛出獄的他感到窒息,陳文雄去鄉下和賴金水學木雕手藝,和啞女阿秀的愛意讓他獲得了心靈的寧靜。陳文雄的選擇是在自我認知后對鄉土帶有的淳樸、自然之氣生生不息的向往。與文雄形成對比的是大師兄阿坤,阿坤認為賴金水僅靠手藝吃飯腦袋不靈活,于是負氣丟下老婆孩子去城里闖事業。阿坤對傳統師承關系的反叛,對鄉土生活的不滿,對家庭的遺棄代表了新一代人對待鄉土的態度,恪守儒家傳統的李行自然對阿坤持否定態度。
二、精神之所:傳統文化的精神認同
李行電影的主人公除了在身體上選擇回歸鄉土,在精神上也主動順從于傳統的家庭倫理及儒家道德。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體現的不是人與人之間的公平協作,而是以自我主義為中心的道德體系。在差序格局中最主要的道德出發點就是“克己復禮”,“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所有道德都是“推己及人”的,最先推進的親屬便是親子與同胞,與之相配最重要的道德要素便是孝和悌。孝、悌、忠、信四個字概括了孔子“仁愛”精神的具體要求,“悌”指的是尊敬兄長。《小城故事》的陳文雄之坐牢便是因為打傷了虐待姐姐的姐夫,姐夫在陳文雄出獄后反省了錯誤和陳文雄重歸于好就是一種變相的對兄弟關系的認同。葉天林和唐風是一對好友,孤兒出身的唐風白天上課晚上擺攤忙著掙錢救濟孤兒院,常常讓最信任的好友葉天林去陪自己的女友蘇琪。天林對蘇琪關懷備至,兩人的愛情急速發展,礙于中國人情感“欲說還休”的含蓄和對兄弟之情的珍惜,天林和蘇琪只能壓抑內心的感情,不愿做被倫理道德所批判的“背叛者”。即便在唐風去世后,兩個人也沒有在一起。他們不愿意背叛的不僅是身兼好朋友身份與男朋友身份的唐風,更是不愿意打破現有的倫理道德。道德精神的和諧與完滿是李行作品主題一貫的、先驗的歸宿。所以,李行的大多數作品,不是“現實”的,而是理想的;不是再現的,而是象征的。李行對傳統文化的服膺讓他影片中的主人公在“仁愛”精神、忠恕之道的感召下,回歸于倫理與普世道德,回歸于老一輩的經驗與認同,所有問題都消弭,隔膜被穿透,距離被拉近,誤解、矛盾都在笑與淚中走向圓滿,其電影塑造了一個“仁者愛人”的理想鄉土。
“孝”存在于父母與孩子之間,也可用于具有威望的長者與后輩之間的類親子關系。李行講:“我的作品重點,多半強調父母子女間的親情,這一點,與我的家庭環境極有關系,在我的感覺里,上一代與下一代應該是協調的,不應該是叛逆的、相抵觸的,人類感情,沒有比父母對子女更真誠無私。我的父母,都是虔誠的佛教徒,是傳統保守的中國人典型,所以我最服膺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是受了他們很大的影響。”《早安臺北》沒有《養鴨人家》《原鄉人》等對農村風光的展現,反而把視角投向了城市生活里的青年人身上。葉天林在酒吧賣唱的時候被父親發現,身為教授的父親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兒子放棄學業去酒吧“賣唱”呢?隨之而來的自然是一段父子的爭吵。社會存在著世代之隔,雖然子一輩要繼承父一輩的生存經驗生活與成長,但時代的變化總會在新一代身上留下印記,給予他們不同的生活經驗。中國傳統的家“既是個綿續性的事業社群,它的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在婆媳之間,是縱的,不是橫的”。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的鄉土社會所形成的文化傳統中,“孝”字是最為重要的一環,所有試圖與傳統父權相對抗的皆可以用“不孝”為之定罪。葉天林辜負父親的期望,休學跑去唱歌即是不孝;鐘理和不顧鄉俗要與同姓女子私奔結婚是不孝;吳繼釗不顧家人反對要嫁給殘疾人鄭豐喜是不孝;賴金水認為陳文雄偷了他的錢騙了他的女兒也是不孝。在對社會世代間矛盾的處理上,無論劇中存在多么劇烈的內在或外在沖突,無論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多么疏遠、多么隔膜,最終都會走向人際和諧的圓滿。葉天林與父親和解,放棄了當歌手的道路重回校園;鐘理和帶著平妹重回家鄉獲得了家人的原諒;吳繼釗也在生育后獲得了母親的諒解;陳文雄以自己的堅持獲得了賴金水的信任和阿秀的愛,叛逆的年輕人仍需要傳統道德秩序的確認和接受。儒家注重的“孝”道實際上就是承認父一輩的長老權力,從而維持鄉土社會的穩定,對于一切可能動搖當下社會結構和統治基礎的新分子都試圖通過長老權力去強制進行教化。當社會在經濟文化巨變之時,長老權力便開始縮小,兩代人的矛盾愈發凸顯,甚至出現“父不父子不子”的情況。
三、苦難鄉土:延續傳統的悲劇審美
20世紀70年代的李行力求在電影的形式上求新求變,《汪洋中的一條船》采用人物傳記的影片樣式,《原鄉人》引入內地關照兩岸情結,《早安臺北》更是以緩慢的情緒主導敘事,淡化人物關系,為日后臺灣新電影運動奠定了基礎,但作為秉持傳統觀念的老導演,李行的電影依舊延續著早期中國電影的苦情風格。李行鄉土作品中的人物不僅遭受“棒打鴛鴦”“牢獄之災”“家破親離”等苦情模式的考驗,還以死亡和犧牲作為結尾,以此解決情節矛盾或以悲情去起到感化、教化的功能。苦難敘事廣泛存在于民族文藝作品中,早期大部分影片片名都含有“淚”“孤”“苦”“盲”“悲”“弱”等字眼。早期的《王哥柳哥游臺灣》是一部閩南語滑稽電影,雖在商業上獲巨大成功,在李行的代表作品中卻鮮有人提及,真正開始奠定其導演風格的是1962年的《街頭巷尾》,影片里朱珠和養父石三泰的生活就充滿了苦難。
李行電影的苦難元素之一是主人公與生俱來的缺陷,這種缺陷表現在“非親生”的人物關系設定上。中國的鄉土社會關系除了地緣關系之外更重要的是以血緣關系為主線的家庭的建立,而血緣關系在鄉土社會中穩定的組織便是家族。非血緣關系的不穩定性容易產生隔閡與誤解,這樣親密又敏感的關系的維系,勢必需要主人公付出更多的努力、耐心及寬容,這些美德都是李行電影中加以贊頌的倫理主題。《小城故事》中的陳文雄無父無母出獄后拜賴金水為師。中國有句古話: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說的就是對師父要像對父母般敬重,親密的師徒關系就是一種類親子關系。沒有兒子的賴金水對文雄投入的愛和信任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這也是他誤會文雄道德上的“瑕疵”(在城里有女朋友,偷錢)以后大發雷霆的原因。《早安臺北》的唐風成長于孤兒院,悲苦的童年使得他在課余拼命賺錢,當同是孤兒的小彈珠逃學出去玩以后,唐風給予了嚴厲的懲罰,并一再用言語教育小彈珠“你是孤兒,你和其他孩子不一樣”以確認其孤兒的身份,唐風在此扮演的便是類似于父親的角色,并最終死在為孤兒院籌款的途中。
死亡是李行電影苦難的另一種表現。《汪洋中的一條船》的鄭豐喜兒時父母雙亡歷經苦難,年僅32歲時因肝癌去世。《原鄉人》中的鐘理和戰后剛剛遷回臺灣就得了肺病,手術后仍于1960年去世。這兩部作品均改編自真實人物生活,選擇悲劇性人物和極具代表性的人生歷程作為創作的材料,能夠使觀眾產生震撼及感動的觀影感受。蔡楚生說過,“在電影的制作上,假如只提供一些‘平淡無奇’的東西,無論如何是不能引起廣大的注意”,應該“在描寫手法上加強每一件事態的刺激成分,和采取一些中國特點的刺激素材”。而所謂“中國特點的刺激素材”往往就是死亡帶給人的震撼。《早安臺北》對死亡這一苦難元素的使用更加突兀,當三人間的關系面臨道德的束縛出現無解的局面時便安排唐風在為福利院籌款時車禍喪命,既渲染了唐風的悲劇宿命,又巧妙化解了三人間交織的愛情、友情的矛盾。比起影片前半部分舒緩、清新的“新電影”風格,后半部分安排的情節突轉有些匠人的斧鑿之氣。也難怪當侯孝賢、楊德昌等一批年輕電影人在20世紀80年代嶄露頭角之時,李行、胡金銓、白景瑞合作的《大輪回》敗下陣來,李行自此進入藝術生涯的衰落期。李行之后,20世紀80年代侯孝賢、王童、陳坤厚、萬仁等一批新導演開啟了臺灣電影最輝煌的“新電影”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