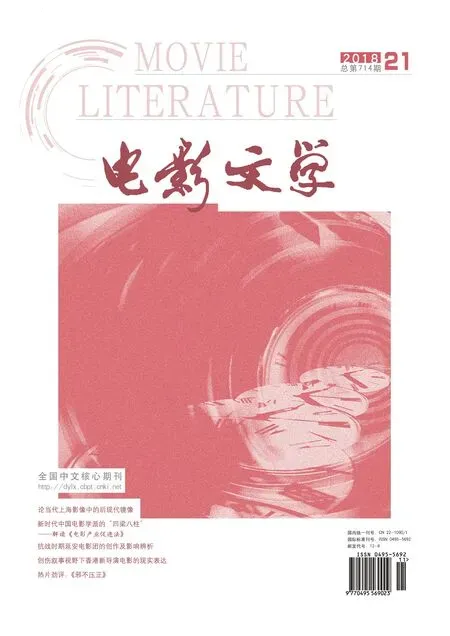論《暴裂無聲》的現實主義電影美學
徐 楠 王 馨
(江南大學 數字媒體學院,江蘇 無錫 214122)
中國電影發展百年,現實主義電影一直是重要的構成部分。隨著中國現實主義電影的發展,其美學表現在不斷流變革新。中國新獨立電影代表人物忻鈺坤的作品《暴裂無聲》是一部犯罪懸疑片,也是一部以現實主義為內核的電影。電影講述在一個北方的村莊,啞巴礦工張保民尋找失蹤的兒子磊子,卻意外摻到富豪老板昌萬年與律師徐文杰的非法采礦案中,后意外找到徐文杰的被綁架的女兒,而徐文杰與昌萬年隱瞞了殺害磊子藏尸的罪行。忻鈺坤將《暴裂無聲》背景設置在以礦產資源為支柱的村莊,塑造了三個不同階層的典型人物,表現現實生活中的矛盾,關注社會矛盾中的人性選擇。本文試分析《暴裂無聲》的處理形式和影像內容生成的語義,探究其現實主義電影美學表現。
一、真實題材的藝術化處理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現實主義電影受到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影響,出現了冷峻的“硬核”現實主義風格電影。該類電影將視角轉向社會底層小人物,多用寫實的語言直面呈現社會矛盾和人性表現。如《小武》強調在敘事策略中通過主題的批判性去直面現實,又如《秋菊打官司》強調視聽風格的無修飾自然寫實主義,更強調攝影機本體意義上的現實主義風格。在當代主流審美、體制環境與商業利益訴求不斷嬗變的背景下,《暴裂無聲》避開純粹的“硬核”風格,其現實主義內涵借助類型片的語言形式呈現,對真實題材藝術化處理:保留題材的真實細節,著重于講述被裁選和重構后的故事,倚用影像語言的技巧表達,以此完成對社會狀態的透視、人性的思考。
《暴裂無聲》處處體現著對社會現實的關照,這些細節源于忻鈺坤對于家鄉包頭的真實觀察,2004年前后的包頭正在經歷大規模煤礦資源開發。片中,有村民因水源被污染而患病,知情的村長只喝礦泉水;翠霞和母親在磊子失蹤后求助于“大仙兒”,燒符紙祈求兒子平安歸來;富豪老板的悍馬越野車、律師的現代轎車與底層礦工的破爛摩托車體現著清晰的階層差異。基于真實細節的構建,《暴裂無聲》的人物形象生動真實且典型,借助了敘事手法、剪輯技巧呈現極富懸疑性的故事,情節的戲劇性發展將“社會矛盾”轉移到“人性選擇”,探究利益面前的眾生相。片中,啞巴礦工張保民在尋找兒子的過程中遇上各種意外情況,由于自身缺陷和身處社會底層的局限,張保民只能通過拳頭來向現實發出怒吼。律師徐文杰在張保民救了自己女兒的情況下,仍然選擇包庇隱瞞昌萬年殺人藏尸的罪行,而不知情的張保民處于雙重“失語”的境況,無法、無處發聲,暴裂歸于無聲。
二、共時性的非線性敘事手法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現實主義電影追求簡單直觀,多選擇樸實無華的線性敘事結構。之后,現實主義電影受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出現了非線性敘事結構。相較于線性敘事的前后不間斷地緊密相接,非線性敘事的結構和技巧有所改變,但其敘事本質沒有變。非線性敘事打破單一的時間向度,這種敘事從“歷時性”變為“共時性”,進入多維度的空間敘事層次。
《暴裂無聲》整體采用非線性敘事的復調結構,多人化的敘事視角、多線性的敘事模式將故事重構,多線脈絡之間相互關聯但并不融合。首先,影片設置了三條線索脈絡:一條是張保民尋找失蹤兒子;一條是昌萬年的非法采礦案;第三條是徐文杰尋找被綁架的女兒。三條線索先是平行地各自展開,原本毫不相干的人物因偶然性逐漸發生碰撞、產生關聯:昌萬年因為非法采礦案綁架了徐文杰的女兒,張保民找兒子過程中無意解救了徐文杰的女兒,徐文杰最后包庇了昌萬年射殺張保民兒子的罪行。三條線索共時進行,直到影片終處才顯現其中關聯。其次,影片中磊子在山坳放羊的情節雖然與上述三條脈絡有著明確的時間順序和特定的因果關聯,但被分解成三個部分,不完全按照邏輯地放置于片中。第一部分磊子在山間放羊出現在影片初始,連接張保民得知磊子失蹤,引出下文;第二部分插敘在張保民山坳尋子的過程中,相同空間中時間狀態短暫倒退;第三部分出現在結尾徐文杰的回憶視角中,對主角和觀眾的判斷進行了有效的干擾。非線性敘事手法將時間分解重新拼接,多線情節同步發展且往往懸而未決,使故事更為撲朔迷離。
除此之外,《暴裂無聲》還使用了閃回手法,即劇情發展中插入相關片段,增加其他時間視角敘事,共時敘事。一方面,閃回的共時性服務于補充故事情節。影片中張保民回村后去屠夫羊肉店的片段里,閃回張保民曾與屠夫產生分歧并戳瞎了他的一只眼睛,交代了張保民與屠夫的恩怨,增加了屠夫的可疑性;昌萬年、徐文杰交代罪行的過程中,多次閃回插入二人在山頂交易的場景,還原了磊子被兇殺的真相,回應整個故事的開端。另一方面,閃回的共時性能夠模糊時間狀態,增強懸疑意境的渲染。磊子在山坳放羊的閃回畫面與張保民在山坳找兒子的畫面緊密連接,使用相同的鏡頭語言打破了時間的單向性,引發了觀眾對于磊子生存狀態的猜想。這樣的閃回在時間與情節上為觀眾設置了雙層障礙,致使觀眾從閃回狀態返回到現實狀態后才明白“所以然”。
三、隱喻修辭構建內涵意蘊
隱喻作為影像語言的一種修辭手段豐富多樣,現實主義電影根據旨義需求靈活運用多種隱喻形態,通過多樣的個體意象隱喻塑造人物、推動情節、渲染氣氛,同時以此產生關聯,構建電影的整體內涵關系,表達影片的主旨含義。
常見的個體意象隱喻多是場景中的物件或者人物的面部表情,停留的特寫能夠自然地引起關注,使人產生思考和想象。《暴裂無聲》開頭磊子在信號塔下壘起的金字塔式石頭堆,與漢字“磊”的字形結構相似,暗示著磊子的生命,在后面張保民尋找到此處時石頭堆已經倒塌,意喻磊子生命已經逝去;昌萬年愛好狩獵多年,但在開弓時手抖得厲害,久久不能射箭,放下弓箭時神情凝重,暗示他藏有心事,或與射擊相關。其次,色彩也具有強烈的隱喻性。影片中,大片的紅色燈光與圓桌上大量的生羊肉將昌萬年的談判室營造成昏暗的紅色畫面,刻畫出昌萬年一種壓抑又強勢囂張的人物性格。再者,聲音作為影像語言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元素,同樣具有強烈的隱喻功能。影片中有多處出現羊肉切片機,“聲音中帶有切羊肉時把羊肉放在盤里面有種被碾壓的濕漉漉的感覺,強調了羊被屠殺的殘酷性”,該片錄音指導李丹楓如是說。昌萬年的羊肉切片機被一根骨頭卡住,正是張保民闖入昌辦公室的時候,張保民就是擾亂“秩序”的硬骨頭。
除此之外,《暴裂無聲》的突出之處在于整體關聯隱喻的營造,由個體到整體的關系構建。個體隱喻在通過自身意象縱向拓展語義內涵的同時,也在多個個體之間發生橫向關聯甚至共振,構建整體關聯隱喻。由個體所構建的整體性隱喻貼合影片所要表達的主旨,同時反作用于個體隱喻,是其發生相互關系的基本依據。影片中不斷重復出現關于“羊”的形象,張保民家中瘦弱的小羊,屠夫砧板前的羊頭,村民粗魯啃食的羊骨,昌萬年現切的新鮮羊肉卷,構建起一條弱肉強食的食物鏈。“羊”被宰殺,是代表弱者的符號,張保民室內打斗的場景伴有羊叫聲,暗示著張保民在困境中無聲地吶喊,同時也是象征了整個社會底層的無聲、無力、無奈。影片中的多處細節不斷暗示現實社會中的三個階層關聯與異別。昌萬年、徐文杰、張保民的車牌號分別為“豢A”“豢B”“豢C”,“ABC”呈一個等級順序,意味著明顯的階層差別;同時,歸屬地“豢”字形與拍攝地內蒙古的“蒙”類似,其字原意“喂養”,泛指使用利益引誘他人任其宰割。昌萬年是兇殘的掠奪者,處于食物鏈的頂端。昌萬年用補償款誘惑村民簽訂土地轉讓合同,用大量現金收買徐文杰在非法采礦案中做手腳,用利益讓村長通風報信,最后任自己宰割,是社會上層人物對于中下層人民的“豢養”。整體關聯隱喻同時包蘊了直觀的意象思考和理性的智力思考,在表現影片的原始語境與其審美語義時更為真實,更容易獲得觀眾審美的認同。
四、服務于現實主義的超現實主義元素
電影中的超現實主義元素往往不直接參與敘事,甚至以特異的意象與無邏輯的插敘破壞敘事結構,盡管如此,超現實主義元素的出現并非毫無意義,其強烈的主觀表征和突兀的出場形式能夠服務于影片的現實主義內核。
首先,影片借助超現實主義元素具象表現深層的社會真實。現實主義是對真實物質生活的描摹,更多強調的是獨立于人類理解與感知之外的實際存在。“作為表現這種現實的藝術應該注重偶然性和自發性,致力于‘表現’而不是‘再現’現實。”《暴裂無聲》的故事典型且具有真實性,有理可依,有據可循,完成了其本身的影像能指與概念所指的功能,但這僅是影片的冰山一角。西班牙超現實主義導演路易斯·布努埃爾認為,眼睛看到的一切不是生活本身。影片中的超現實元素站立在理性的能指與所指之上,超越了規矩的經驗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思考范疇,是生動的無法描述的不同人的不同主觀意識。影片中啞巴張保民無法像徐文杰那樣用聲音呼喊,這種失聲讓他失去了兒子。這種解釋無法用科學原則深究,但這超現實的表達將無形的深層社會真實轉化為有形,張保民身體的失聲缺陷正是代表社會底層人物對不公平的無法發聲。
其次,超現實主義元素為觀眾的自我意識留有空間,將其對影像故事的關注轉移至自身的意識,觸發對現實的審視與思考。超現實主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響,意在挖掘潛意識,表達人的精神世界。“人的行為有時往往受心理傾向所支配,自身的意識卻感受不到”。在三人打斗的過程中,磊子解救了山洞中昏迷的媛媛,一路奔跑,在山頂眺望遠處霧靄中的城市。在觀眾對于兩個孩子存活與否的求知欲達到頂峰時,交叉敘事模糊了兩個片段的真與假,誤導了情節發展的方向,但是能夠表達出隱藏的情緒。客觀上磊子和媛媛一個死去一個昏迷,但是二人在山間奔跑的超現實情節不僅僅是兩個父親的期待,更是順從了觀眾內心潛意識的期盼。直到最后徐文杰從洞中抱出媛媛,大聲地喊著她的名字,張保民沉默地望著洞口,觀眾才突然地意識到對二人生死的誤判,超現實與現實的相悖讓觀眾從之前的沉浸中驚醒,感到突兀和迷惑,從而召喚觀眾對影片中原以為常的內容進行思考,不斷回味影片意圖表達的“無法把控”。
五、結 語
在市場與制度的需求下,現實主義電影對影像語言不斷探索與嘗試,嬗變出新的美學表現。《暴裂無聲》為此做出的改變并非一味地妥協,內容與形式的借鑒與創新,既是拓展了現實主義電影美學的可能性與藝術性,又是增強了影片的觀賞性,發揮自身的審美價值,避免傳統現實主義美學的“曲高和寡”。當然,無論現實主義電影美學表現如何更變,最重要的是其內核依舊保持對社會現實與人性真實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