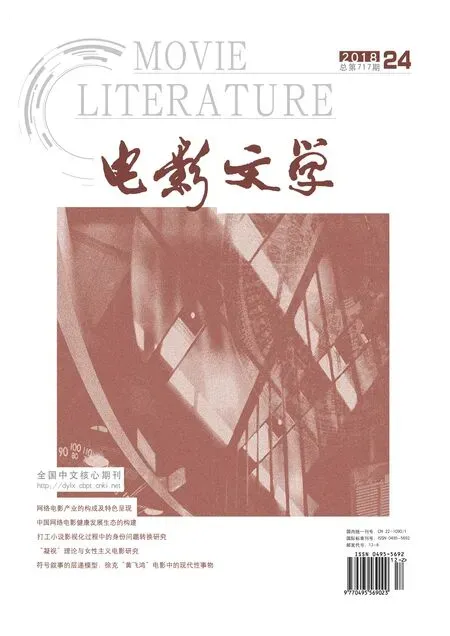中國現實主義電影的創作轉向
趙貴清
(中國藥科大學 文化藝術教育中心,江蘇 南京 211198)
現實主義創作常見于藝術片以及其他非商業化電影當中,其強調呈現事物的本真面貌,在真實、自然的前提下呈現矛盾和問題,展現社會現實、人性復雜往往是現實主義電影的創作落腳點。中國第五代導演將現實主義電影創作推向巔峰,無論是張藝謀、陳凱歌還是田壯壯等人都在各種類型片中踐行著現實主義。張藝謀幾乎是用鏡頭丈量了中國社會的倫理與道德緯度,陳凱歌同樣將視角對準了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眾生相,在現實生活中攫取的真實的一瞬,往往挑開的是當時中國社會的全貌。第五代導演的現實主義創作是常規的、傳統的,在展現中國社會現狀的同時,也進行著極為犀利的批判主義。而在中國電影商業化進程中,傳統的現實主義電影創作逐漸邊緣化,樸實無華的現實主義敘事不夠吸引人,取而代之的是融入類型片中的新現實主義創作。然而,這些電影形式上繁雜多變,卻保留了傳統現實主義創作的核心精神,即真實、自然與批判,新世紀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創作正在經歷著重要轉變,而現實主義創作的轉型也對應著社會大眾思想的轉變,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間接體現。
一、現實主義保守派創作的式微
現實主義是在文學批評中最常用到的理論之一,最早出現在18世紀德國劇作家席勒的理論著作當中,真正作為文藝思潮與文學流派則是在法國文壇。文學憑借與電影先天的文本契合性,諸多文學理論都能應用在電影當中,對于文學文本與電影文本的解構常常存在一種普適性的視角與方法論,于是現實主義也自然而然地應用到了電影藝術當中。
現實主義電影是20世紀30年代意大利電影人發起的電影運動的產物,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意大利電影人急切地想要通過電影來表現社會現狀,在早期的現實主義電影當中就已經包含了濃重的批判意識。現實主義電影發展至今,呈現真實與批判現實是始終不變的。如今提及現實主義電影創作伴隨的往往是樸素的畫面和舒緩的敘事,從現實生活中攫取真實的敘事能量是現實主義電影的核心,于是這些電影往往將鏡頭對準特殊的人群,企圖通過透視他們的生活來表現真實的社會內部景觀,讓觀眾透過鏡頭了解人類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曾經或者正在經歷的一些轉變。
中國第五代導演的早期作品創作時期被看作是中國電影創作的黃金時代,支撐起了中國電影藝術的脊梁,第五代導演的早期電影扎根于民族歷史與社會現實,從民族歷史中梳理民族心理與民族精神,從社會現實中觀望人性。如張藝謀的早期作品在追求寫實隱喻的視覺形式的同時,將身處于社會體制、制度中的人,被時代洪流所左右的人的命運統統呈現在大銀幕之上。《紅高粱》雖然表面上寫意,實際上諸多隱喻色彩濃厚的鏡頭畫面都是在真實地呈現陜北高原的獨特風光,表現陜北農民的不屈的、向上的精神和意志。而從《秋菊打官司》開始,張藝謀電影中的現實主義創作分外鮮明,采用了半紀實的拍攝風格,呈現了一個法制意識覺醒的農村婦女形象,由秋菊一人帶出了當時中國農村的人際關系和倫理道德面貌。《活著》《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等影片都將現實主義踐行到底。陳凱歌的《孩子王》《邊走邊唱》等早期作品也同樣將現實主義視為創作的根本,在不斷以真實的、樸實的鏡頭影像書寫著生命的輪廓。
于是,民族歷史中的民族精神與人文風貌,社會發展、轉型期人們的生存狀態,這些都是以中國第五代導演早期作品為核心的現實主義保守派著重表現的。與之相對應的是,保守派的現實主義作品往往敘事節奏樸實,鏡頭語言唯美卻不華麗,因此第五代導演代表人物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和吳子牛等人的早期作品被視為藝術電影,這些是與好萊塢商業電影氣質不沾邊的作品,用視覺影像書寫現實主義是這些保守派作品的唯一訴求。
從張藝謀拍攝電影《英雄》開始,不僅標志著中國商業大片時代的到來,同時也標志著第五代導演與現實主義創作的疏離。在《英雄》開啟的中國大片時代,視覺帶來的感官刺激才是吸引觀眾走進電影院的關鍵,現實主義保守派的作品顯然無法適應轉型期的中國電影市場。
隨著第五代代表導演的集體轉型,在現實主義電影創作領域,第六代導演的藝術能量開始被凸顯出來,相較于張藝謀等第五代導演作品的商業化,第六代導演依然傾向于紀實性的、批判性的現實主義作品。實際上,早在20世紀末,像賈樟柯等就已經開始拍攝“故鄉三部曲”,張元早已拍攝了《北京雜種》《東宮西宮》《過年回家》等一系列極有分量的現實主義電影。第六代導演將自身成長的經歷融入了電影創作,以自身的成長視角與成長體驗呈現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如果第五代導演仍然希望在現實主義創作中糅入理想化的元素,企圖梳理出民族精神中的積極的、正面的部分的話,那么第六代導演更傾向于直面黑暗,將人性之惡呈現在銀幕之上。于是,改革開放浪潮之下的中國社會風起云涌,社會環境的變化、物質生活的改善直接影響了人們的精神世界,甚至顛覆了存在于中國社會千年的倫理人文,人與人的社會關系重新被梳理,新的社會秩序悄然來臨。
然而,相對于第五代導演而言更加“叛逆的”第六代導演,他們的現實主義創作并未持續進行,步入新世紀之后,隨著中國商業電影市場的不斷擴張,第六代導演也無法做到完全忽視票房而進行藝術片創作,市場化語境下的電影創作始終需要票房利潤的支撐。現實主義保守派創作雖然在第六代導演處得到了繼承與延伸,但是終究需要在商業電影市場的大環境中做出改變,正如賈樟柯在《三峽好人》開始就嘗試超現實主義創作,盡可能地用一些元素去調和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現實主義保守派創作日漸式微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二、現實主義的軟性轉化與間接滲透
如果說第五代導演將中國現實主義電影推向了一個藝術高點的話,那么以賈樟柯、張元、路學長和婁燁等為代表的第六代導演則延續了中國現實主義電影創作的輝煌。現實主義創作成就了中國電影的輝煌,時至今日論及當代中國的經典電影依舊是《紅高粱》《秋菊打官司》《黃土地》《邊走邊唱》等,用現實主義探索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以及用現實主義呈現發展與巨變中的真實的中國社會,現實主義使這些作品成為極其有分量與張力的作品。
中國商業電影市場在21世紀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代,電影的商業化也成為勢在必行的必然趨勢。隨著張藝謀率先轉型成為商業片導演以后,諸多第五代導演陸續加入了商業大片的隊伍當中,強調視覺奇觀效果的商業大片在銀幕上爭奇斗艷,而現實主義電影被劃歸到藝術片的范疇,無法與其他視覺大片在電影市場爭得一席之地。在中國電影商業化的十幾年當中,雖然第六代導演賈樟柯依然堅持現實主義電影的拍攝,如2006年的《三峽好人》、2008年的《二十四城記》都堪稱經典,他依舊堅持著用平凡的鏡頭語言記錄中國社會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并將人與人的關系和故事放置在這一背景下。而在此后的《天注定》和《山河故人》當中都融入了些許的商業元素,觀眾能夠清晰地看到這幾部作品與其早期的現實主義作品的區別,現實主義保守派作品是無法完全與其他商業電影相抗衡的,無法完全被如今的中國電影院線容納。因此,賈樟柯的現實主義創作雖然偏離了保守派,卻始終以此為軸心,盡可能地豐富鏡頭語言,改善敘事結構,以現實主義表現手法為基礎增加戲劇性,使其作品更加適合當代觀眾的審美趣味。
身為第六代導演的張元、婁燁和王小帥也同樣逐漸疏離了現實主義保守派,他們的作品呈現出多元化的類型片風格特色,現實主義以一種軟性轉化的形式融入他們的電影當中,間接滲透在類型片創作里,成為敘事風格的一部分,抑或是成為一種敘事視角出現在電影當中。例如,第六代導演管虎在1992年拍攝了《頭發亂了》、1996年拍攝了《浪漫街頭》,這兩部作品都是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創作。為了順應商業電影的大環境,從2009年的《斗牛》開始,管虎開始了黑色電影創作,突出故事中的戲劇性,集驚悚、懸疑、戰爭、喜劇等多重類型風格于一身。雖然拋開了現實主義創作,但是《斗牛》故事的敘事內核依然富有現實主義的批判意義,現實主義已經融入管虎鏡頭敘事當中,成為創作思想的一部分。在其日后的《老炮兒》當中,保守現實主義與超現實主義共同存在其中,影片對被時代拋棄的頑主六爺的生存境遇的呈現是真實的,是現實主義創作的高度濃縮,而對頑主六爺精神世界的塑造又是超現實的,更具商業電影的審美趣味,可以說是管虎將現實主義敘事與商業電影模式相融合的典范。又如,在婁燁的作品《推拿》當中,真實呈現盲人生活的同時,又在其精神世界的挖掘過程中融入了類型片的內容,現實主義與商業類型片完美融合,批判主題也十分深刻。
因此,當今的商業電影市場上,現實主義保守派的創作已經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融入商業電影框架的現實主義,這種現實主義創作思想影響著商業電影的鏡頭語言,也影響著敘事內容與主題。正是由于對現實的呈現欲和反思欲的強烈,才使當下涌現出一批新黑色電影,這些電影亦真亦假地呈現著現實世界,在戲劇性十足的敘事中反思現實、批判社會問題,最終使商業電影創作起到與現實主義創作目標合二為一。
三、結 語
現實主義保守派電影無疑已經成為當今中國電影中邊緣化的存在,商業電影市場大張旗鼓的擴張加速了電影的商業化,商業電影需要更多的吸引眼球的噱頭,而不是傳統現實主義電影的平鋪直敘。因此,現實主義電影需要以新的面貌出現在觀眾面前,與商業電影類型的融合成為其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張藝謀的《歸來》、許鞍華的《桃姐》、羅啟銳的《歲月神偷》等現實主義電影的成功,也表明了當下觀眾對商業電影多元化的審美需求,以及更廣泛的接受度。由此看來,中國現實主義電影并非進入了創作低谷,電影人應當擺脫現實主義電影類型化心理,換一種思維方式去將現實主義融入商業電影框架當中,使其改變鏡頭語言或敘事主題,進而深化商業電影的藝術性。當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創作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時,轉型勢必會發生,新現實主義電影會在觀眾的審美趣味的轉變、審美能力的提高中形成,而中國現實主義電影的新創作黃金時代也并非遙遙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