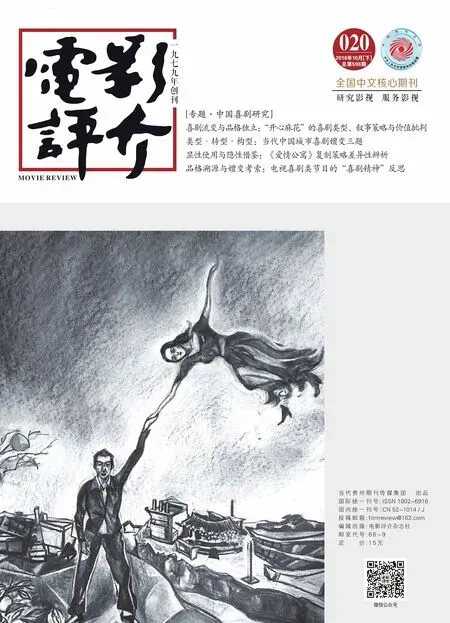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都市電影創(chuàng)作嬗變
都市是電影藝術(shù)重要的表達(dá)空間與場域,電影亦是反映城市文化與市民生活的重要方式。所謂都市電影,即在內(nèi)容表達(dá)與題材選擇上關(guān)注于都市人群的生存狀態(tài)、生活境遇以及情感生活等方面的電影創(chuàng)作。在誕生之初,電影藝術(shù)就與都市文化緊密聯(lián)系在了一起。回顧中國電影發(fā)展歷程,無論是早期的《神女》《馬路天使》等經(jīng)典影像,還是當(dāng)下的《唐人街探案》《我不是藥神》等熱門影片,都市題材逐步發(fā)展成為電影創(chuàng)作的重要種類與方式。特別是在歷經(jīng)改革開放40年后,我國的都市電影從復(fù)蘇自覺再到創(chuàng)作自信,已然生成一套獨(dú)特的鏡語類型與美學(xué)風(fēng)格。“電影的美學(xué)形態(tài)在不同時(shí)期都有其可以追尋的軌跡,其間的變化正是人們精神祈求的遷變所致,得失也影響著創(chuàng)作的樣態(tài)。”由此,結(jié)合當(dāng)下我國電影創(chuàng)作最新態(tài)勢,重新梳理與分析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都市題材電影創(chuàng)作歷程,探討我國都市題材電影在不同時(shí)代的美學(xué)流變具有重要意義。
一、創(chuàng)作梳理
(一)電影“傷城”——都市電影的復(fù)蘇重建(1978-1986)
回顧我國的電影發(fā)展史,都市題材一直是重要的創(chuàng)作類型之一。從初創(chuàng)時(shí)期的《勞工之愛情》《孤兒救祖記》等電影中對(duì)城市場域自發(fā)性呈現(xiàn),到三四十年代的《神女》《馬路天使》等電影對(duì)都市罪惡淵藪的批判性表達(dá),再到“十七年電影”中的《新局長到來之前》《今天我休息》等作品對(duì)建國初期城市建設(shè)以及市民生活的展露,我國都市電影的創(chuàng)作脈絡(luò)以及美學(xué)內(nèi)涵一直在延續(xù)與演變。在“文革”十年動(dòng)蕩中,一方面,以工農(nóng)兵為主題的革命政治題材主導(dǎo)著電影創(chuàng)作,都市電影一時(shí)處于創(chuàng)作空白階段;而在另一方面,也正是經(jīng)歷了長時(shí)期的積壓與沉淀,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電影創(chuàng)作領(lǐng)域的政策扶正與培育,一批具有歷史反思與藝術(shù)實(shí)驗(yàn)性質(zhì)的都市題材電影開始復(fù)蘇重建。“解放思想,實(shí)事求是,發(fā)展社會(huì)生產(chǎn)力,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成為共和國走向新時(shí)代的最大政治和最強(qiáng)烈的要求,電影生產(chǎn)面臨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尤其是對(duì)電影意識(shí)形態(tài)性質(zhì)的重新規(guī)劃與管理機(jī)制的重新定位,很顯然適合于新一代電影人的建構(gòu)性生產(chǎn)。”
在這一階段,較為重要的都市題材電影有《生活的顫音》(1979,滕文驥,吳天明導(dǎo)演)、《天云山傳奇》(1980,謝晉導(dǎo)演)、《人到中年》(1980,謝晉導(dǎo)演)、《小街》(1981,楊延晉導(dǎo)演)、《沙鷗》(1981,張暖忻導(dǎo)演)與《鄰居》(1981,鄭洞天導(dǎo)演)等作品。由于剛從“文革”的動(dòng)蕩苦難中走出,這一時(shí)期的都市題材電影大多呈現(xiàn)出較為濃厚的“傷痕”特質(zhì),主旨多集中于對(duì)“文革”的控訴、批判與反思,電影敘事多被放置于“文革”時(shí)期的都市空間,并且呈現(xiàn)出明顯的“傷城”意向。如電影《生活的顫音》講述了主人公“鄭長河”在“文革”中的種種遭遇,電影的時(shí)空背景為“文革”中的北京;電影《小街》講述了都市青年小夏與小俞二人在“文革”背景下的曲折感情;《天云山傳奇》同樣將敘事放置在具有都市人視角的天云山區(qū)。在這些作品中,都市多為故事發(fā)生地,以一種“背景幕布”式的存在,批斗、迫害與平反等反思“文革”式的敘事成為這些電影作品較為顯著的特征,從都市本體出發(fā)而創(chuàng)作的電影作品較為缺乏。
在這其中,電影《沙鷗》(1981,張暖忻導(dǎo)演)與《鄰居》(1981,鄭洞天導(dǎo)演)值得關(guān)注。作為一部體育題材電影,《沙鷗》講述了在粉碎“四人幫”后都市女青年“沙鷗”努力向上的人生成長故事,這一敘事模式對(duì)后來相應(yīng)的電影創(chuàng)作有所啟發(fā)。而《鄰居》將敘事空間設(shè)置在一個(gè)筒子樓里,關(guān)注于時(shí)代背景下平常百姓的住房問題,真正將敘事的主體與空間落腳在了都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時(shí),電影《鄰居》切實(shí)革新了當(dāng)時(shí)較為陳舊的電影語言——在影片的開端,一個(gè)具有時(shí)代意義的長鏡頭調(diào)度開啟了新時(shí)期的電影美學(xué)觀念,也揭開了都市電影由復(fù)蘇進(jìn)入實(shí)驗(yàn)探索與發(fā)展的序幕。
(二)電影“悲城”——都市電影的藝術(shù)自覺(1986-2000)
進(jìn)入20世紀(jì)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市場經(jīng)濟(jì)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市民生活的興起,城市文化逐步自覺與成長,電影創(chuàng)作亦開始從第五代鄉(xiāng)土表達(dá)的傳統(tǒng)逐步走出,都市題材電影創(chuàng)作進(jìn)入了新的階段,關(guān)注都市人的生活狀態(tài)、情感追求以及價(jià)值觀念的電影開始顯現(xiàn)。第五代與第六代等各類電影人的創(chuàng)作相互交織,共同譜寫出改革開放后國產(chǎn)都市電影的創(chuàng)作年表。這一時(shí)期,出現(xiàn)了很多值得關(guān)注的都市電影創(chuàng)作風(fēng)向,重要的作品有《給咖啡加點(diǎn)糖》(1987,孫周導(dǎo)演)、《頑主》(1989,米家山導(dǎo)演)、《本命年》(1990,謝飛導(dǎo)演)、《北京,你早》(1990,張暖忻導(dǎo)演)、《站直啰、別趴下》(1993,黃建新導(dǎo)演)、《北京雜種》(1993,張?jiān)獙?dǎo)演)、《陽光燦爛的日子》(1993,姜文導(dǎo)演)、《頭發(fā)亂了》(1994,管虎導(dǎo)演)、《民警故事》(1995,寧瀛導(dǎo)演)、《有話好好說》(1997,張藝謀導(dǎo)演),《長大成人》(1997,路學(xué)長導(dǎo)演)、《甲方乙方》(1997,馮小剛導(dǎo)演)、《小武》(1998,賈樟柯導(dǎo)演)、《蘇州河》(2000,婁燁導(dǎo)演)等電影。
整體來講,這一時(shí)期的都市電影逐步脫離第五代自《黃土地》以來的鄉(xiāng)土電影創(chuàng)作指向,在創(chuàng)作體量以及藝術(shù)探索方面都取得較為長足的發(fā)展,比較突出的創(chuàng)作有“黃建新電影”“馮小剛電影”與“賈樟柯電影”等。從《黑炮事件》走出的黃建新,進(jìn)一步將創(chuàng)作視域聚焦于都市人的生活細(xì)節(jié)與內(nèi)心狀態(tài),《站直了,別趴下》《背靠背,臉對(duì)臉》(1994)、《紅燈停,綠燈行》(1996)的電影手法平實(shí)自然而又內(nèi)涵深刻,在整體上顯示出濃郁的都市平民生活氣息。如果說這一時(shí)段第五代導(dǎo)演群體的電影創(chuàng)作還在鄉(xiāng)村與都市之間游離,那么馮小剛的市民喜劇則是都市電影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自然生成,是市民生活興起以及市民文學(xué)、電影的繁榮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甲方乙方》(1996)、《不見不散》(1999)等電影以調(diào)侃的臺(tái)詞與嬉鬧的情節(jié)表現(xiàn)都市生活,既符合電影商業(yè)的發(fā)展走向,又暗喻了現(xiàn)代都市人的情感空洞與異化等諸多問題。與此同時(shí),第六代對(duì)都市電影的創(chuàng)作認(rèn)同更為徹底與自覺,大多關(guān)注都市角落的各類生命狀態(tài)與情感體驗(yàn),底層、邊緣人群通常被放置在極具意向的都市時(shí)空下進(jìn)行藝術(shù)性的抒寫與描摹。“‘都市的一代’聚焦于陰郁灰暗的城鎮(zhèn)……呈現(xiàn)都市空間帶給個(gè)體的傷痛與迷茫。”在這些電影中,都市不再局限于被動(dòng)地成為電影的場景設(shè)置,而是作為文化背景與創(chuàng)作場域的本體意義被充分挖掘與放大,拒絕、反抗、逃離與反思都市成為其較為常見的情感特質(zhì)。如《北京雜種》中的北京、《蘇州河》中的上海以及《小武》中的汾陽等城市被充分的藝術(shù)化創(chuàng)作,在主題內(nèi)涵上體現(xiàn)為對(duì)在改革開放城市化進(jìn)程中所出現(xiàn)的某些社會(huì)問題與情感危機(jī)的個(gè)性探討,都市成為電影“悲城”。以此同時(shí),隨著社會(huì)語境的流變,這一時(shí)期的都市電影創(chuàng)作將實(shí)驗(yàn)個(gè)性、個(gè)人表達(dá)以及時(shí)代反思等多種元素混合,由此也將中國電影以區(qū)別于第五代的另一種方式推介到國際,成為中國藝術(shù)電影板塊的重要構(gòu)成。
(三)電影“幻城”——都市電影的類型構(gòu)建(2000—2018)
進(jìn)入2000年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國內(nèi)經(jīng)濟(jì)進(jìn)一步發(fā)展,北京、上海等國際大都市在改革開放的推進(jìn)中逐步成型,中國城市的國際影響力逐步增強(qiáng)。在政策方面,廣電總局于2001年后發(fā)布《關(guān)于改革電影發(fā)行放映機(jī)制的實(shí)施細(xì)則(試行)》等多條政令,實(shí)行院線改革,打破了國有企業(yè)控制電影發(fā)行權(quán)的歷史,民營電影市場被激活。由此,都市電影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新的轉(zhuǎn)向,從創(chuàng)作心理到觀影心態(tài)等多方面都發(fā)生了深刻變革,從客觀抽離反思、拒絕都市陰暗之隅走向主動(dòng)構(gòu)建參與、體驗(yàn)城市繁華之境,都市電影的類型化特征也逐步廓清。消費(fèi)風(fēng)潮、時(shí)尚生活以及城市風(fēng)貌日益成為都市電影重要的呈現(xiàn)內(nèi)容,光鮮夢幻的都市形象逐步被電影作品建構(gòu)成為影像景觀,同時(shí)創(chuàng)作類型日益豐富,愛情、職場、青春等題材均有涉及,并且部分作品生成出創(chuàng)作系列。自此,我國的都市電影也從“悲城”時(shí)代逐步走進(jìn)“幻城”時(shí)代。
此階段的都市電影類型構(gòu)建可分為探索與成型兩個(gè)階段,以2010年為轉(zhuǎn)折點(diǎn)。在2000年至2010年間,較為突出的都市電影作品有《開往春天的地鐵》(2002,張一白導(dǎo)演)、《手機(jī)》(2003,馮小剛導(dǎo)演)、《周漁的火車》(2004,孫周導(dǎo)演)、《孔雀》(2005,顧長衛(wèi)導(dǎo)演)、《瘋狂的石頭》(2006,寧浩導(dǎo)演)、《三峽好人》(2006,賈樟柯導(dǎo)演),《愛情呼叫轉(zhuǎn)移》(2007,張建亞導(dǎo)演)、《李米的猜想》(2008,曹保平導(dǎo)演)、《非誠勿擾》(2008,馮小剛導(dǎo)演)等作品。這一時(shí)期的電影立足于都市,多聚焦于現(xiàn)代都市人的情感困境與現(xiàn)實(shí)生活,電影關(guān)注與描摹的對(duì)象也開始由邊緣向主流人群轉(zhuǎn)移,并且電影創(chuàng)作較為注重藝術(shù)性探索,導(dǎo)演的個(gè)人風(fēng)格較為突出,在這其中可以窺見都市電影的類型特征正在逐步顯現(xiàn)。
通過前十年的類型化探索,中國都市電影開始進(jìn)入新的類型化時(shí)期。2010年被普遍認(rèn)為是我國“新都市電影”的發(fā)力之年,除了《唐山大地震》(2010,馮小剛導(dǎo)演)等都市災(zāi)難題材的創(chuàng)作,《杜拉拉升職記》(2010,徐靜蕾導(dǎo)演)等作品將都市進(jìn)一步“幻城”化,電影內(nèi)容多為現(xiàn)代都市人的生活狀態(tài)、職業(yè)生態(tài)與情感糾葛,致力于渲染出都市生活的光鮮靚麗與現(xiàn)代時(shí)尚,都市成為一個(gè)奮斗之地、歡樂之場與逐夢之地,逐步拋離90年代較為“傷城”式的陰暗邊緣描述,電影“幻城” 被逐步建構(gòu):高聳林立的高樓大廈、緊張高效的辦公空間、時(shí)尚現(xiàn)代的消費(fèi)空間等都是這類電影常見的景觀式呈現(xiàn)。在故事上較之于第六代的底層邊緣敘事視角發(fā)生了較大的轉(zhuǎn)變,多展現(xiàn)都市中主流人群的職場故事以及情感境地,符號(hào)化、標(biāo)簽化、公式化的都市形象以及偶像式、電視式、網(wǎng)絡(luò)式的影像內(nèi)容成為這一時(shí)期都市電影的重要特征。隨后,《失戀33天》(2011,騰華濤導(dǎo)演)、《人在囧途之泰囧》(2012,徐崢導(dǎo)演)、《北京遇上西雅圖》(2013,薛曉璐導(dǎo)演)、《心花路放》(2014,寧浩導(dǎo)演)、《人在囧途之港囧》(2015,徐崢導(dǎo)演)、《唐人街探案》(2015,陳思誠導(dǎo)演)、《喜歡你》(2017,許宏宇導(dǎo)演)等電影都從各種角度對(duì)都市進(jìn)行了“幻城”式的表達(dá)建構(gòu)。2015年,郭敬明導(dǎo)演的《小時(shí)代》因以標(biāo)簽化與概念化的表現(xiàn)手段極度鋪陳都市的浮華與夢幻遭到諸多質(zhì)疑,“夢幻之城”成為“幻想之城”與“空洞之城”。同時(shí),伴隨著國內(nèi)電影市場的繁榮,都市電影在顯現(xiàn)出類型化特征的同時(shí)發(fā)育出新的分支,青春片、探案片等類型逐步成熟并大力發(fā)展,如在都市題材與懷舊情懷的雙料結(jié)合下,一大批都市青春題材的開始出現(xiàn),《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2013,趙薇導(dǎo)演)、《中國合伙人》(2013,陳可辛導(dǎo)演)、《匆匆那年》(2014,張一白導(dǎo)演)、《同桌的你》(2014,郭帆導(dǎo)演)等作品爭相上映。《小時(shí)代》系列也可以被納入都市青春片的研究范疇,與其有關(guān)的爭議側(cè)面也反映出了都市電影在類型建構(gòu)時(shí)期所遭遇的來自創(chuàng)作與市場等多方面的問題。
二、現(xiàn)狀評(píng)析
2017年,我國電影年度票房已然突破500億元大關(guān),成為僅次于北美地區(qū)的第二大電影市場。在國內(nèi)電影市場持續(xù)發(fā)展的背景下,都市電影日益成為中國電影重要的組成板塊。總體來講,在經(jīng)歷了改革開放40年來的重建與探索,我國的都市電影在創(chuàng)作數(shù)量與藝術(shù)構(gòu)建上都發(fā)生諸多嬗變,面臨的成就與問題并存。
(一)藝術(shù)自覺
近年來,都市電影的實(shí)踐探索在商業(yè)化浪潮中逐步推進(jìn),藝術(shù)自覺自改革開放初期的復(fù)蘇重現(xiàn),到90年代的個(gè)性探索,再到2000年后類型書寫的發(fā)展脈絡(luò)并沒有斷裂。2011年以后,即使在類型化的發(fā)展浪潮下,都市電影的藝術(shù)表現(xiàn)依然較為突出,如《觀音山》(2011,李玉導(dǎo)演)、《搜索》(2011,陳凱歌導(dǎo)演)、《推拿》(2014,婁燁導(dǎo)演)、《山河故人》(2015,賈樟柯導(dǎo)演)、《闖入者》(2015,王小帥導(dǎo)演)、《烈日灼心》(2015,曹保平導(dǎo)演)、《暴裂無聲》(2018,忻鈺坤導(dǎo)演)等,這些都市作品都表現(xiàn)出了強(qiáng)烈的藝術(shù)風(fēng)格,特別是在2018年上映的電影《我不是藥神》(關(guān)牧野導(dǎo)演)引發(fā)了觀影狂潮,成為當(dāng)下都市電影的代表之作。《我不是藥神》本身所蘊(yùn)含的都市電影特質(zhì)值得思考:首先,在故事主體方面,影片將平凡個(gè)體與邊緣底層人群整合一體共同書寫,具有一定的綜合性質(zhì);其次,在主題方面觸及到了當(dāng)下國內(nèi)百姓普遍關(guān)注的現(xiàn)實(shí)問題,從而引發(fā)觀影共鳴;再次,影片從多重角度反映了都市真實(shí)空間,醫(yī)院、街道、餐館、碼頭等各個(gè)場景基于現(xiàn)實(shí)呈現(xiàn),一反過分渲染城市“悲情”或者“夢幻”的表達(dá)失衡,同時(shí)《我不是藥神》也反映出了國內(nèi)都市電影在題材選擇、風(fēng)格營造以及主題表達(dá)等創(chuàng)作方面的藝術(shù)自覺,能夠以影像的力量直面社會(huì)發(fā)展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各類問題,并且回歸都市電影的藝術(shù)本性。總之,《我不是藥神》折射出了當(dāng)下我國都市電影的發(fā)展現(xiàn)狀,側(cè)面反映出了都市電影藝術(shù)自覺的流變歷程。
(二)文化自信
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的都市電影發(fā)展歷程,在藝術(shù)自覺的同時(shí)文化認(rèn)知也逐步走向自信,影片不再局限于對(duì)個(gè)體情感的感懷抒發(fā),而是以一種新的藝術(shù)視野與格局呈現(xiàn)都市情感與生活,創(chuàng)作視角從自我審視走向?qū)ν鈧鞑ィ瑒?chuàng)作場域從國內(nèi)城市轉(zhuǎn)向跨國空間,創(chuàng)作心態(tài)從反思拒絕走向認(rèn)可自信。電影《人在囧途之泰囧》對(duì)于泰國各類文化標(biāo)簽化的戲仿、《唐人街探案2》中對(duì)美國街頭文化的調(diào)侃、《我不是藥神》對(duì)印度城市現(xiàn)狀的直白展露等,都反映出了當(dāng)下中國都市電影創(chuàng)作心態(tài)與觀影心理的變化。通過對(duì)比不同時(shí)期的都市電影不難發(fā)現(xiàn),在當(dāng)下的都市電影中,國人不再是外來文化盲目的追隨者與簇?fù)碚撸且砸环N中心的姿態(tài)去游戲調(diào)侃或者審視批判。如在電影《唐人街探案2》中,角色“唐仁”穿著浮夸的服飾大鬧紐約街頭,而來自日本、美國等各國角色皆被設(shè)定成符號(hào)化的配角,這與改革開放初期國人對(duì)外國文化的影像想象與表達(dá)大相徑庭,這些在實(shí)質(zhì)上反映出了我國都市電影從對(duì)外來文化接收到對(duì)本國文化自信的深層次轉(zhuǎn)變,這源于改革開放40年來國內(nèi)城市突飛猛進(jìn)的發(fā)展、電影市場的激活、觀眾群體的改變等諸多因素的合力。同時(shí),我國都市電影所折射出的文化自信不僅局限于跨國電影文本的生成,也暗含于各種題材的創(chuàng)作之中,如《白日焰火》(2014,刁亦男導(dǎo)演)對(duì)都市情感的探索抒寫、《火鍋英雄》(2015,楊慶導(dǎo)演)對(duì)地方方言的自由使用、《八月》(2015,張大磊導(dǎo)演)對(duì)國家改革發(fā)展的個(gè)性側(cè)記、《老炮兒》(2015,管虎導(dǎo)演)對(duì)于昔日頑主的現(xiàn)實(shí)緬懷、《我不是藥神》對(duì)社會(huì)問題的直露表達(dá)等,都反映出了都市電影在文化創(chuàng)作方面的自信心態(tài)。在好萊塢大片的浪潮卷席下,華語電影的興起以及亞洲電影的發(fā)力,都為我國都市電影的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的創(chuàng)作背景。當(dāng)然,對(duì)于自我文化的非理性認(rèn)知也會(huì)產(chǎn)生新的問題與弊病,這也存在于當(dāng)下的一些電影創(chuàng)作中。
結(jié)語
回顧改革開放40年,中國都市電影歷經(jīng)從“傷城”到“悲城”、再到“幻城”的時(shí)代流變,既反映出了我國都市電影的發(fā)展脈絡(luò),也折射出了我國整體電影創(chuàng)作的時(shí)代特質(zhì)與美學(xué)演變。在中國電影市場整體繁榮的背景下,都市題材所面臨的創(chuàng)作生態(tài)更為復(fù)雜。從橫向而言,較之于改革開放初期,當(dāng)下國內(nèi)電影創(chuàng)作明顯偏向于都市類型,鄉(xiāng)土題材一時(shí)處于失語的困頓狀態(tài);而從縱向而言,特別是較之于20世紀(jì)90年代,當(dāng)下都市題材電影的文藝片創(chuàng)作也面臨著來自商業(yè)電影的擠占危機(jī)。在追求淺層敘事、娛樂至上的消費(fèi)主義的席卷下,我國的都市電影面臨著諸多問題,隨著城市文化的演變、觀眾群體的更迭、創(chuàng)作主體的多元、傳播方式變革以及影視技術(shù)的更替,都市電影的發(fā)展勢必受到諸多方面影響。如何堅(jiān)持藝術(shù)自覺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以及文化自信的時(shí)代格局,是都市電影創(chuàng)作者時(shí)刻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