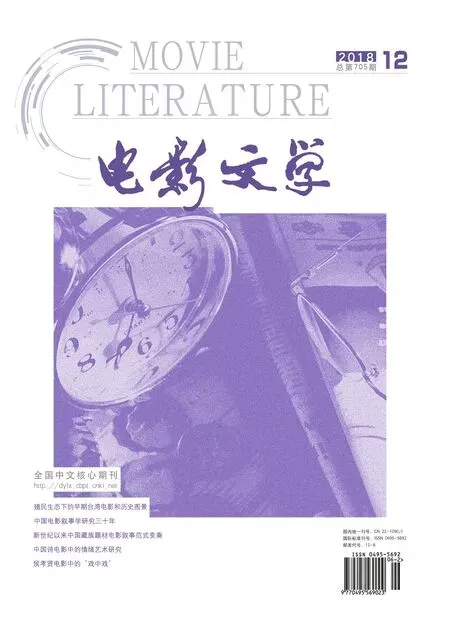“矛盾存在”呈現的可能性
——菲利普·K.迪克小說電影改編的啟示
王 平
(浙江財經大學 人文與傳播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科幻小說在當今西方文化語境中,已擺脫了亞文類的邊緣地位。伴隨著加速度的世界更新,對全球的文化想象產生著一波盛于一波的沖擊。許多當代的文化考察都意識到科幻元素已經與其密切相關。除了傳統的歷史、類型等研究理路之外,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等研究也加入批評領域。不言而喻,電影,可謂視覺傳媒時代最為重要的科幻文化載體。
菲利普·K.迪克(Philip K.Dick),科幻文學重要獎項“菲利普·K.迪克獎”便以其名字來命名。同時,他也是迄今為止,科幻小說作家中,創作的小說被改編成電影最多,銀幕受眾的影響最廣泛的一個。不久,隨著他更多的小說被搬上銀幕,如《銀翼殺手2049》(2017)、《尤比克》(時間未定)、《流吧,我的眼淚》(時間未定),其影響力必將進一步擴大。
追索其生前寂寥,死后卻得到極高贊譽的緣由,那便是他的小說特質,呈現了對存在本質的矛盾性的思考。這種思考,遠遠超前于他的時代,卻在現下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理解與共鳴。這便是美國文學批評理論家詹姆遜對他的評價:“科幻小說中的莎士比亞”的真意。這種“to be”“not to be”的思考,無關乎科學技術,而是哲學本質的。文學和電影在這終極意義的求索中達成一致。因而考量一部根據他的小說改編的電影成功與否,這就成為重要的批判基準。然而這種存在并非不言自明的,在電影改編中需要去呈現,需要引導他人去辨識考量、去加深認知、去深刻反思。
一、設定:對立性的考量
很多電影,包括鐘愛原創劇本的好萊塢科幻片制作,往往選用迪克的短篇小說進行改編,首先是因為其設定的別致。在迪克的創作時期,時空穿越、星際旅行之類的科幻設定早已不新鮮。但是他擁有不同于常人的思維與創想,總是能在舊設定中玩出新花樣,新點子也層出不窮。比如其獲得雨果獎,并被改編成電視劇的長篇小說《高堡奇人》,拉開了一幕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戰敗國為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諸國為背景的故事,開創了“錯列歷史”(alternative history)的新規則。被譽為“鬼才”的迪克甚至常常將一個令人驚艷的設定奢侈地用在一篇寥寥數語的短篇小說中。
迪克的小說中的設定,本身其實都埋藏著關于存在本身的深刻對立。當電影改編決定使用該設定的同時,是否決定沿用并深入挖掘這一對立沖突,便顯示了主創人員的定位與思路。拿短篇小說來改編,故事篇幅并不足夠應對一部電影的正常時長。留白賦予主創人員的發揮余地增大了,是可以顯示風格和水平的契機。然而問題在于,主創在敷衍故事的同時,往往將原著小說中的對立性消解彌合,取消了原作的深刻性。
《命運規劃局》(2011)保留了原著短篇小說的基本設定:在上位世界中,存在著一個能夠看到平行世界中無數個未來,并按自己的意愿為人類選擇一個未來的機構。這個未來,并非人類按自己日常生活能夠自然達到的。故而,這個機構的執行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就是強行扭轉人類的日常現實。原著小說設定本身的對立沖突,在于上帝視角決定人類的統一性。雖然這個目的本身的指向是善的,但這種行為本身無視個體的自由意志,并且隨意抹殺個體的記憶和存在的價值。整部小說使用旁觀視角,冷峻寫實地記錄小人物的命運。改編電影則明顯削弱了這一對立。首先將主人公戴維描述為天之驕子,一個被選中要成為影響人類命運格局的美國總統的最優人選。他追逐愛情、反抗命運,甚至連機構中上至“上帝”,下至“天使”都予以援手。從表面上看,似乎還隱約帶有原設定中個體自由意志需要得到尊重和極權無視個體選擇這一沖突,但仔細辨析,已然被偷換成了個人英雄主義、人定勝天的主旋律。
原設定中的對立蘊含著對人類生存矛盾的深層次思考,對這種深層次的對立不加以刻畫表現,電影根本的立意便流于浮表淺俗。《預見未來》(Next
,2007)無視這一規則,導致包括商業票房在內的改編失敗。原著小說設定人類為保證自己種族的延續,消滅因為核戰發生出現的變異人。最為棘手的是一個金色的變異人。這個變異人不會說話,不與人溝通交流,但是卻能躲避追捕與攻擊。迪克設定:金色變異人所經歷的時間線和人類不同,是逆向的。對于普通人類而言,過去是確定的,未來是不確定的。對他而言,我們所謂的未來,是他的過去。除此之外,便是他對異性有著無法言明的吸引力,如同原初的動物本能。由此可以揭示出原設定的深層對立沖突:作為進化的產物,面向未來前進的人類,卻面臨著要被保持原始本能的,沿著過去逆向而行的變異種替代的深刻危機。人類文明、情感完敗于原始叢林法則。然而電影改編則抽離了設定的這一原初對立。主人公克里斯只是一個擁有預知未來能力的人類,而不是變異的特殊存在,影片中也不再有人類滅種的危機。也取消了主人公外形如金色希臘神祇的設定。與之前的《命運規劃局》一樣,改編影片亦添加了愛情線,克里斯為了營救心愛的人殫精竭慮地使用預知未來的能力。和原著小說變異人對異性僅僅是工具性的利用截然相反。
電影改編時添加滿足迎合觀眾的商業化內容并非不可行,然而大幅度地消解原著設定的對立深度則不可取。輕而易舉地彌合和消解原著設定中的對立,如何與大量復制雷同的快餐電影相區分?太過于貼近現實人物的處境,產生和一般商業片沒有區別的情感代入,即便是假定目標觀眾也不一定會買賬。因為即便是“從此以后永遠幸福地生活著”的商業類型片制作,“也暗示趨向于偽裝或者掩蓋與每個角色的妥協相聯系的不可避免的失落”。電影和小說一樣,真正深刻的對立沖突存在的意義,是呈現出來給人觀照并反思的。而不是僅僅放諸在淺表,予以泛泛的想象性的彌合。要在“接近差異的地方把握差異,而不是夢想它的同一性、它的純粹性”。
二、敘事反轉:認知性的推進
在小說和電影中,反轉這一敘事策略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形式手段。電影中的反轉,一波三折,為起承轉合這一模式平添更多引人入勝的波折。在短篇小說中,制造反轉幾乎是一個靈魂性的操作。迪克的特別之處在于即便是創作短篇小說,也不僅只有結尾處的反轉,他會制造兩個、三個,甚至更多。反轉使得小說的敘事結構不再呈現為簡單的直線形的平鋪直敘,而是之字形的層層遞進。電影中的反轉能在一定程度上營造懸疑效果和緊張氣氛,吸引觀眾注意。如果只是為反轉而反轉,為了制造單純的獵奇效果,而沒有將故事內容和內涵意義予以推進提升的話,那本質就是故弄玄虛,耗費掉觀眾的專注、期待和興趣。
迪克原著中的反轉,跟科幻題材本身不可避免的非經驗性有關。這種可能世界中的不可能經歷的性質,非常適合用大屏幕來進行呈現。對于日常生活經驗的背離,不僅僅奪人眼球,能制造娛樂性、趣味性效果,且能激發人創造性的想象與思考,提供了一種認知性的路徑。
我們來考察《異形終結》(1995)中的幾個反轉。該片設定為:人類互相廝殺時研發的機械殺戮武器自行產生了進化,無差別地攻擊人類。其中反轉一:荒野里抱著泰迪熊的小男孩是殺戮武器的一種進化類型。反轉二:欲進入堡壘避難的斷腿傷兵亦被擊斃,同樣是針對人類的移情演化的一種殺戮機器型號。反轉三:由于不知道還有多少進化型號,留在堡壘內的人們開始互相猜忌,甚至互相殺戮。反轉四、五:因為神神道道遭受懷疑被殺死的人卻只是人類,而殺人者本身就是殺戮機器的一種進化型號。反轉六:最后,與司令官相愛并相約逃出不毛之地的女性原來是一直未知,已進化出內在的血肉和情感的一種殺戮型號。
反轉效果的營造,對于認知的推進,首先需要獲得觀眾的理解。這一前提,使科幻電影在自然科學層面的認知性受限。因為在此層面上的認知,取決于社會平均教育水平。然而,在人本哲學的認知層面,受這樣的限制卻較少。《異形終結》中,反轉建立在人類共情共識的層面。比如反轉一、二對于兒童、弱勢的同情,反轉三、四中負向的人與人的彼此懷疑、猜忌、殺戮,反轉五、六關于人造物進化的究極狀態。反轉推動了觀眾對這些共情共識的反思,挑戰了我們既定的常識和規約。人性中的同情是否有錯?被利用的話應該摒棄嗎?為了自保而猜忌懷疑錯了嗎?即便不被利用又如何?到底以怎樣定義進化、退化、人性?人造殺戮機器本身的反弒又是誰造成的?
不同于《異形終結》中的反轉對認知范疇的分別立論,《全面回憶》(1990)的反轉則是對記憶這一特定存在的反復認知。涉及記憶的矛盾存在是迪克小說中的一個重要主題,背后隱藏著關于人的存在是什么的核心矛盾。原著小說中,道格拉斯首先因為對火星的渴望但身份又很低微而只能去記憶公司植入去過火星的虛假記憶。但這一操作激發了之前真正去過火星的記憶,揭露了他特殊的身份以及被消除記憶的真相(反轉一)。他為了自保選擇植入真實的關于火星的記憶是被植入的虛假記憶(反轉二)。
電影改編有所調整,反轉一之后,道格拉斯就開始了被追逐的火星之旅。事實上,這趟被追逐的火星之旅無論是從改編短篇小說敘事需要,還是從電影的奇觀化效果而言,都可謂經典。時至今日,特效可能看來已經略顯粗糙,但是這種光怪陸離的氣氛特質,卻頗為契合地映照了關于記憶這一存在的失之毫厘,卻能使得人的存在謬以千里的本質。在影片中,最后精彩的原創性反轉是:道格拉斯對于記憶的篡改并非為了自保,而是篡改自己記憶之前的道格拉斯本人,是一個反派人物,他需要對自己植入篡改的記憶來牟取利益。而當下的道格拉斯,即便知道了這一點,還是遵從現下自我的人格選擇,做一個好人。雖然和原著小說的具體反轉有所出入,但是毫不妨礙推進記憶這一存在并且與其相關的自我、人性的復雜與深刻。同時,還吻合全片充滿戲謔的邪典風格。
迪克小說的反轉特質,如同夢魘一般急轉,步步進逼所有習以為常卻不一定理所應當的“存在”。不反轉,你就還停留在舒適的經驗區感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就無法嘗試跳出既定的界限來看問題。改編電影如何利用好這一跳出自身所處的常態,擱置經驗性認知和價值判斷特質,無論是對形式還是內涵的推進,都頗有意義。
三、內涵:復雜性的表現
迪克對于存在的思考,充滿著復雜的糾結。不同于邏輯矛盾,在哲學層面,存在本身就是矛盾的,矛盾就是存在本身。迪克只是用自己的表述將真實與虛幻、進化與退化、人類與人造物、人類大局與個體命運等矛盾存在聚焦放大,并呈現出來。這種矛盾相悖的部分,共生在一起。優秀的科幻題材電影與文學一樣,最迷人的特質就是展現其可能與復雜性,拒絕簡化和固定。它絕對不會無原則地將自己獻祭于一種淺白與短暫存在里,而是永遠啟迪著人的好奇、想象、認知與反思。在理解基礎上如何表現,也就是如何展示菲迪克這種糾結纏繞的矛盾,怎樣引導觀眾去發現這些問題呢?事實上基于載體的不同,小說和電影的表現不可能完全一致。如何借用電影獨特的綜合性藝術的助力,就成為關鍵。
首先,矛盾不是膚淺直呈的。而《少數派報告》(2002)的電影改編就是對原著小說中矛盾呈現的粗暴簡化。將預知未來這一矛盾存在的復雜性,僅僅簡化為多數和少數的對峙。三位先知對于罪行的預測,有時候并不是一致的。這就是題名的由來。原著小說中,做出不犯罪預測的少數派先知,是預見到當事人在知道多數派報告的預測之后,決定不犯罪之后的判斷。然而又因為其他的意志,當事人最后又決定執行犯罪。這時的預測是時間線最后的那位先知所做的。因而雖然一、三位的預測一致,但是其中糾結纏繞的細節和關節點非常多。這也就對預知能力提出了一個復雜的存在命題,未來會一成不變嗎?人有了預知能力之后會如何面對被預知的未來?等等。然而遺憾的是,改編無視這一矛盾的復雜性以及對其抽絲剝繭的展示,僅僅表示少數派也可能是正確的。
矛盾展示同樣不是非此即彼的。《雙面魔神》(2006)就展現了善惡、自我、真實的一系列存在的復雜性:警察弗雷德被上司派去監控毒販鮑伯,而鮑伯正是臥底打入毒販內部卻因吸食毒品已人格分裂的弗雷德。善惡集于一體;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自我;幻象、預知、幻覺、超視力和真實所見的區別在哪里?
《銀翼殺手》(1982)作為公認的迪克小說中翻拍最成功的作品,同時也是科幻題材電影中毋庸置疑的經典作品。作品在表現矛盾存在的復雜性層面超越了原著小說的高度。僅僅察其視覺元素,便同時呈現了未來與過去、東方與西方、特權階級與螻蟻草民、高科技與低生活等矛盾的糾結。它們不是潦草地堆積在那里,也不是劍拔弩張地對立并置在兩側,而是如同萬花筒一般,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展示出一種瑰奇卻自然的末世圖景。而其影像基調抑郁沉悶,雨、夜、煙霧貫穿全片,其籠罩的未來就是看不清楚的秘境,有著無數解不開的矛盾存在。在其之后,幾乎任何一部近地題材的科幻電影中都能或隱或顯地看到它的視覺元素和影像風格的影響。
而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矛盾呈現,便是貫穿影片的,糅合了科幻、文學、哲學的“問題”與回答。這種終極性的關于人的存在的本質探討的提出,是迪克被稱為賽博朋克(cyberpunk)先驅的原因。耐人尋味的是,前半部的問題是人提問人造人的,以影片開端,辨別人造人的“移情測試”始;后半部則是人造人拷問人類的,最后以提問人造人的“人”的自我反詰終。什么才是人的存在?如果說那些人造人具備的人性成分比人類還要充沛的話,那么他們是否能稱之為人?如果我們確信形成我們自我存在的關鍵記憶只是被植入的時候,那么我們到底又是什么?影片不斷地拷問卻一再延宕回答,將其復雜矛盾演繹得淋漓盡致。“我思,故我在。”迪克的移情問題設置在這里“以一種極具破壞性的、現代的方式重新激活了笛卡兒式的問題”;也“重新喚醒了笛卡兒式的懷疑”。電影改編用仿生人羅伊坐化前那首自證的詩:“I’ve seen things you people wouldn’t believe/Attack ships on fire off the shoulder of Orion/I watched c-beams glitter in the dark near the Tanhauser Gate/All those moments will be lost...in time/Like tears...in the rain” 呈現了前者“我思,故我是仿生人”,同時還借此呈現了人造人的生與死、其存在的短暫與永恒的價值判斷。也以疑似人造人的人造人殺手的夢中的獨角獸來表現后者,并對原著小說題名《仿生人能夢見電子羊》點題,向這種復雜的矛盾呈現致敬。
從考察迪克小說的電影改編我們得到啟示,他超前于自己的時代,源自拒絕二元對立的簡單固化。矛盾存在是一個問題域,一個故事可以把一系列的問題誘發與呈現在一個具體的語境之中。這種呈現是一種可能性的提示,而非必然性的決定。而一部對他本意發掘的電影,則需要感性地執行這個哈姆雷特式的任務,表現這個世界的復雜,兜兜轉轉地回到這個認知的本源命題,思考存在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