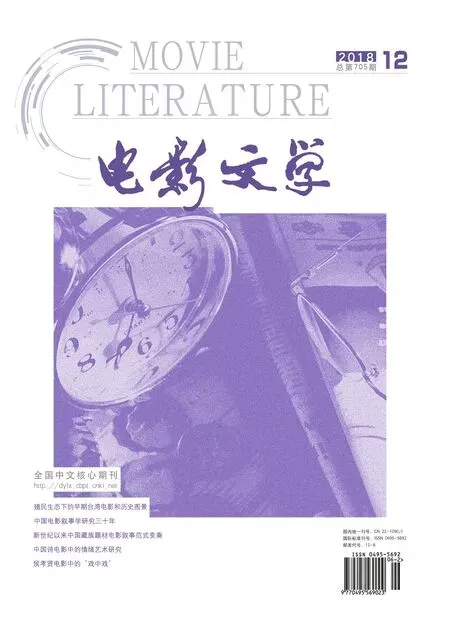電影《血戰(zhàn)鋼鋸嶺》的批判性敘事解讀
李惠然
(駐馬店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河南 駐馬店 463000)
電影是文化與意識(shí)形態(tài)整合的產(chǎn)物,而好萊塢電影則是美國(guó)社會(huì)文化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直接投射,在很多時(shí)候也起到引導(dǎo)社會(huì)大眾思潮的功能作用。美國(guó)戰(zhàn)爭(zhēng)電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流文化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的態(tài)度,絕大部分好萊塢戰(zhàn)爭(zhēng)片都有反對(duì)戰(zhàn)爭(zhēng)、評(píng)判人性的創(chuàng)作意圖,同時(shí)也深刻表現(xiàn)了個(gè)人英雄主義代表的美國(guó)文化。梅爾·吉布森執(zhí)導(dǎo)的最新戰(zhàn)爭(zhēng)大片《血戰(zhàn)鋼鋸嶺》是一部非常規(guī)意義的戰(zhàn)爭(zhēng)片,傳統(tǒng)的戰(zhàn)爭(zhēng)電影展現(xiàn)的都是戰(zhàn)士奮勇殺敵的英雄形象,而《血戰(zhàn)鋼鋸嶺》表現(xiàn)的卻是不帶槍上戰(zhàn)場(chǎng)的軍醫(yī)戴斯蒙德的形象;傳統(tǒng)的戰(zhàn)爭(zhēng)電影以國(guó)家意識(shí)為英雄誕生的最高精神準(zhǔn)則,而《血戰(zhàn)鋼鋸嶺》表現(xiàn)的則是宗教信仰對(duì)英雄的成就。雖然影片的視覺(jué)表現(xiàn)形式依然是非常主流的好萊塢大片藝術(shù)形式,但是影片在塑造戴斯蒙德英雄形象的同時(shí),也在對(duì)戰(zhàn)爭(zhēng)、人性做出批判性敘事,表述了導(dǎo)演梅爾·吉布森的個(gè)人觀點(diǎn)。
一、戰(zhàn)爭(zhēng)的批判
反戰(zhàn)是戰(zhàn)爭(zhēng)電影的恒久主題,甚至很多時(shí)候被電影人當(dāng)作是藝術(shù)職責(zé)一般看待,對(duì)戰(zhàn)爭(zhēng)場(chǎng)景的反觀與描繪反而是對(duì)和平年代的熱愛(ài)使然。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的批判不僅表現(xiàn)在視覺(jué)藝術(shù)上對(duì)于戰(zhàn)場(chǎng)的打造,子彈穿過(guò)人的身體、鮮血淋漓的殘肢、人們渴望被救贖的眼神,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批判更多的是通過(guò)敘事內(nèi)容、敘事結(jié)構(gòu)等方面集中建構(gòu)的。戰(zhàn)爭(zhēng)幾乎有著碾壓粉碎一切事物的能力,和平年代的歡聲笑語(yǔ)、和樂(lè)融融的生活、動(dòng)人的愛(ài)情、溫暖的親情等,都能夠被戰(zhàn)爭(zhēng)機(jī)器瞬間粉碎。戰(zhàn)爭(zhēng)電影中往往呈現(xiàn)的是美好生活被毀滅的過(guò)程,展現(xiàn)人們的物質(zhì)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崩塌,在極端的環(huán)境當(dāng)中揣摩人性、分解人性、解讀人性。因此,戰(zhàn)爭(zhēng)電影在塑造戰(zhàn)爭(zhēng)機(jī)器形象之前,總是會(huì)先塑造一個(gè)美好的事物,可以是美好的生活場(chǎng)景、一段美好的愛(ài)情、美麗的人物等,然后在敘事的進(jìn)程中逐漸將其徹底粉碎,最終表現(xiàn)反戰(zhàn)主題思想。
電影《血戰(zhàn)鋼鋸嶺》有著較為清晰的敘事結(jié)構(gòu),戴斯蒙德英雄角色的養(yǎng)成作為敘事主線,經(jīng)歷過(guò)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父親的戰(zhàn)后精神創(chuàng)傷行為作為時(shí)隱時(shí)現(xiàn)的副線出現(xiàn)。影片將戴斯蒙德的人生一分為二來(lái)看待,也投射在敘事結(jié)構(gòu)的劃分上,前半部分主要表現(xiàn)了戴斯蒙德的兒童到青年的成長(zhǎng)過(guò)程,后半部分則展現(xiàn)戴斯蒙德參軍及上戰(zhàn)場(chǎng)以后的故事,前后兩部分無(wú)論是在畫(huà)面視覺(jué),還是敘事內(nèi)容上都構(gòu)成了極大的反差,可以看作是構(gòu)成了一種二元對(duì)立結(jié)構(gòu)。正如傳統(tǒng)的戰(zhàn)爭(zhēng)電影敘事策略一樣,影片先是構(gòu)建了戴斯蒙德的美好生活,然后再用戰(zhàn)爭(zhēng)因素將其粉碎。戴斯蒙德的童年時(shí)光并非無(wú)憂無(wú)慮的,但是他依然形成了樂(lè)觀善良的性格。當(dāng)他看到有人受傷流血時(shí),馬上會(huì)不顧一切地送對(duì)方去醫(yī)院治療,也是由于自己善良的行為而在醫(yī)院邂逅了此生摯愛(ài)。戴斯蒙德和護(hù)士多蘿西正沉溺在愛(ài)情的甜蜜當(dāng)中時(shí),戴斯蒙德哥哥的入伍行為對(duì)他造成了精神上的沖擊,在他看來(lái)為了保護(hù)其他人,自己參軍入伍是一種愛(ài)國(guó)的義務(wù)和責(zé)任。然而,入伍參軍意味著戴斯蒙德的美好生活即將被顛覆,他需要接受部隊(duì)的訓(xùn)練和戰(zhàn)場(chǎng)的洗禮。
影片前半部分雖然對(duì)戴斯蒙德的幸福生活進(jìn)行了描繪,但即便是這樣一個(gè)遠(yuǎn)離戰(zhàn)場(chǎng)的小鎮(zhèn),依然無(wú)法阻擋戰(zhàn)爭(zhēng)產(chǎn)生的或深或淺的影響,戰(zhàn)爭(zhēng)雖然沒(méi)有對(duì)他們的身體造成創(chuàng)傷,卻影響著他們的心靈與精神。尤其是在戴斯蒙德以決不妥協(xié)的勇氣,拒絕手持武器上戰(zhàn)場(chǎng)以后,戰(zhàn)爭(zhēng)的狂暴與恐怖才真正得以呈現(xiàn)。
影片在敘述戴斯蒙德故事的同時(shí),也以一種并置處理的方式表現(xiàn)了戰(zhàn)爭(zhēng)對(duì)戴斯蒙德父親的精神碾壓。戴斯蒙德的父親湯姆·道斯曾參加過(guò)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因受傷而退伍。湯姆·道斯雖保全了身體,但精神世界卻是殘缺不全的,回到了往日生活的寧?kù)o的家鄉(xiāng),依舊宛如身在戰(zhàn)場(chǎng),不能自拔。他只能依靠酒精麻痹自己,不僅沒(méi)能緩和他的精神創(chuàng)傷,反而產(chǎn)生了暴力傾向,曾經(jīng)溫柔的湯姆如今時(shí)常在醉酒后對(duì)妻子暴力相向。影片從戴斯蒙德的父親身上反映了戰(zhàn)爭(zhēng)恐怖的毀滅力,即便是能從戰(zhàn)場(chǎng)上死里逃生,日后依舊無(wú)法擺脫戰(zhàn)爭(zhēng)的陰霾,甚至戰(zhàn)爭(zhēng)對(duì)美國(guó)大兵的心理造成的創(chuàng)傷要遠(yuǎn)遠(yuǎn)高于肉體。
二、人性的評(píng)判
戰(zhàn)爭(zhēng)電影除了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否定與批判之外,更多的還是對(duì)于人性做出了審視與評(píng)判。《血戰(zhàn)鋼鋸嶺》中的戴斯蒙德·道斯盡管童年時(shí)期做過(guò)兩次讓自己后悔終身的事——一次險(xiǎn)些讓自己的哥哥送命,另一次則是險(xiǎn)些開(kāi)槍打死自己的父親,但當(dāng)他最終確立信仰、確立了自己的做人原則之后,無(wú)論是他在平時(shí)的為人處世當(dāng)中,抑或是不帶槍上戰(zhàn)場(chǎng)拯救他人,都表現(xiàn)出戴斯蒙德·道斯人性中的閃光點(diǎn)。戴斯蒙德的哥哥義無(wú)反顧地入伍,以及他在醫(yī)院親眼看到的源源不斷地從戰(zhàn)場(chǎng)輸送過(guò)來(lái)的傷員,這些都成為戴斯蒙德想要成為一名不殺人、只救人的士兵的原因。他認(rèn)為個(gè)人的情感與生活遠(yuǎn)不及上戰(zhàn)場(chǎng)重要,這也是他能在有了美好的愛(ài)情之后,依然決定奔赴戰(zhàn)場(chǎng)的原因。
《血戰(zhàn)鋼鋸嶺》中涉及的人物并不多,片中沒(méi)有絕對(duì)的反派,即便是看起來(lái)的負(fù)面形象,到最后都會(huì)表現(xiàn)出一定的正面色彩。例如,負(fù)責(zé)新兵訓(xùn)練的霍威爾中士是一名標(biāo)準(zhǔn)的美國(guó)大兵,在他看來(lái),勇氣、體能和武器是戰(zhàn)場(chǎng)上沖鋒陷陣的必需品,他無(wú)法想象一名美國(guó)大兵來(lái)到殺人不眨眼的戰(zhàn)場(chǎng),會(huì)不拿武器去保護(hù)自己或消滅敵人。所以,霍威爾中士認(rèn)為特立獨(dú)行的戴斯蒙德是個(gè)懦夫,不配在他的手下訓(xùn)練,并利用自己的權(quán)威去欺負(fù)戴斯蒙德,甚至讓同期的士兵毆打、排擠他。但是,到了戰(zhàn)場(chǎng)上的霍威爾中士是勇敢無(wú)畏的,在這樣一種極端的環(huán)境之下,他唯一的信念是殺死更多的敵人,同時(shí)保護(hù)自己的士兵。當(dāng)霍威爾受傷窩在戰(zhàn)壕一夜以后,是戴斯蒙德不顧一切地將他從死亡邊緣拉回,平安送到了鋼鋸嶺之下。戴斯蒙德的這一行為讓霍威爾見(jiàn)證了戴斯蒙德并非一個(gè)懦夫,而是比任何士兵都要執(zhí)著、勇敢。
此外,葛洛弗上尉在部隊(duì)中處于更高的職權(quán)地位,他曾和霍威爾中士一樣認(rèn)為戴斯蒙德是個(gè)懦夫,他的存在是對(duì)于他們以往戰(zhàn)斗經(jīng)驗(yàn)和人生經(jīng)驗(yàn)的最大嘲諷,他無(wú)法想象那樣一個(gè)恐怖的戰(zhàn)場(chǎng)上,一名士兵不拿槍會(huì)有怎樣的下場(chǎng),甚至認(rèn)為如果不拿槍?zhuān)幻勘蜔o(wú)法實(shí)現(xiàn)自己的價(jià)值。但到最后,當(dāng)戴斯蒙德一夜不眠不休救下了75名士兵,深受震撼的葛洛弗上尉肯定了戴斯蒙德的勇氣和力量,并選擇尊重戴斯蒙德的個(gè)人信仰,在二次登陸鋼鋸嶺之前,他也幾乎是以懇求的姿態(tài)請(qǐng)戴斯蒙德在基督教的安息日上戰(zhàn)場(chǎng)。無(wú)論是霍威爾中士還是葛洛弗上尉,他們都從一開(kāi)始給觀眾的反面形象,轉(zhuǎn)變?yōu)檎嫘蜗螅撬麄円婚_(kāi)始對(duì)戴斯蒙德的誤解,才讓人們看到戴斯蒙德能夠堅(jiān)持自己的信仰,為信仰而戰(zhàn)是何等的難能可貴。
三、信仰的審判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美國(guó)電影繼西部片和歌舞片之后,誕生了第三類(lèi)主要的類(lèi)型電影,即戰(zhàn)爭(zhēng)電影。從一開(kāi)始,戰(zhàn)爭(zhēng)元素以其強(qiáng)大的滲透力融入幾乎所有類(lèi)型的電影當(dāng)中,直到戰(zhàn)爭(zhēng)電影最終確立為美國(guó)電影中的主要類(lèi)型之一。美國(guó)戰(zhàn)爭(zhēng)電影的敘事核心是反戰(zhàn)思想,此外美國(guó)文化中的個(gè)人英雄主義也是美國(guó)戰(zhàn)爭(zhēng)電影規(guī)劃情節(jié)、塑造人物的核心。在傳統(tǒng)的美國(guó)戰(zhàn)爭(zhēng)電影當(dāng)中,能夠擁有過(guò)人的勇氣和能力盡可能地殺死敵人被看作是一名美國(guó)大兵的合格標(biāo)準(zhǔn),消滅對(duì)方,贏得戰(zhàn)爭(zhēng)的勝利才是一名士兵應(yīng)當(dāng)做的事情。戴斯蒙德·道斯是真實(shí)存在于美國(guó)歷史上的人物,信仰基督教的他拒絕持槍上戰(zhàn)場(chǎng),堅(jiān)持自己是為了救人而上戰(zhàn)場(chǎng),徒手在沖繩戰(zhàn)役上拯救75個(gè)同伴的傳奇事跡令他載入美國(guó)歷史。于是,梅爾·吉布森將戴斯蒙德的真人真事搬上大銀幕,更傾向于用影像書(shū)寫(xiě)一場(chǎng)關(guān)于信仰的力量與奇跡。
正如導(dǎo)演梅爾·吉布森執(zhí)導(dǎo)過(guò)的其他戰(zhàn)爭(zhēng)片一樣,一個(gè)英雄,不僅要有過(guò)人的勇氣、力量與智慧,更要有堅(jiān)定的個(gè)人信仰。例如,《勇敢的心》中的威廉·華萊士在將死之時(shí)依舊信仰自由,堅(jiān)持自由的力量,那一聲響徹云霄的“Freedom”是他對(duì)信仰堅(jiān)持的極致體現(xiàn)。在《血戰(zhàn)鋼鋸嶺》里,戴斯蒙德堅(jiān)信自己前往戰(zhàn)場(chǎng)是為了拯救生命,他堅(jiān)定不移地堅(jiān)持著自己不帶武器上戰(zhàn)場(chǎng)的信念,而這一信仰的確立也源自于他的童年經(jīng)歷。戴斯蒙德出生在一個(gè)風(fēng)景秀麗、有著巍峨群山的地方,大自然賦予了戴斯蒙德勇敢無(wú)畏的性格,經(jīng)常跟著哥哥攀爬上陡峭的山崖。然而,一次與哥哥打鬧中險(xiǎn)些失手令哥哥喪命,這對(duì)戴斯蒙德日后的行為產(chǎn)生了精神刺激的根源,他對(duì)于自己能夠產(chǎn)生的暴力感到驚訝,在他看來(lái),暴力是一切傷痛的根源,暴力帶給人們?nèi)怏w和精神的雙重痛苦,暴力不僅改變了對(duì)方,同時(shí)也對(duì)施暴者的心理產(chǎn)生了影響。
《血戰(zhàn)鋼鋸嶺》并非一味地強(qiáng)調(diào)戴斯蒙德不持槍上戰(zhàn)場(chǎng)的絕對(duì)性,只是證明戴斯蒙德堅(jiān)持的信仰也是戰(zhàn)爭(zhēng)年代的一種選擇,也是進(jìn)行個(gè)人戰(zhàn)斗的一種方式,如果沒(méi)有其他戰(zhàn)友與敵人的殊死搏斗,僅僅依靠戴斯蒙德救人的信念也是無(wú)法贏得戰(zhàn)爭(zhēng)勝利的。但是,戴斯蒙德的信仰卻成為贏得鋼鋸嶺之戰(zhàn)的關(guān)鍵,鼓舞了眾多士兵的不僅是戴斯蒙德一夜不眠的救人行為,其救人行為背后的巨大勇氣更是讓人敬畏不已。在戰(zhàn)前訓(xùn)練期間,人人都是英勇無(wú)比的戰(zhàn)士,可一來(lái)到真正的戰(zhàn)場(chǎng),即便是再有勇氣的人也會(huì)被嚇得目瞪口呆,當(dāng)生死只是一瞬間的事情,任何人都不會(huì)有太多的思考,甚至只會(huì)蜷縮在戰(zhàn)壕里瑟瑟發(fā)抖。然而,信仰給了戴斯蒙德無(wú)窮的力量和勇氣,當(dāng)救人的纜繩已經(jīng)將他的雙手絞得血肉模糊,他依然祈求上帝讓他再救一個(gè)人。即便是天亮了以后,沒(méi)有了黑夜的保護(hù),戴斯蒙德依然堅(jiān)持救人,并最終找到了霍威爾中士,將他救下鋼鋸嶺。
與救人的戴斯蒙德形成鮮明對(duì)比的是葛洛弗上尉,經(jīng)歷過(guò)第一場(chǎng)戰(zhàn)役失敗的他無(wú)比苦悶,垂頭喪氣地在軍營(yíng)里自責(zé)和懊惱,他是絕對(duì)的暴力信仰者,當(dāng)暴力無(wú)法贏得戰(zhàn)爭(zhēng)時(shí),他如同被掏空了一般虛弱無(wú)力。最終,有著堅(jiān)定的基督教信仰的戴斯蒙德鼓舞了所有人,讓他們相信上帝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所有人都在戴斯蒙德信仰的光環(huán)下沖上鋼鋸嶺奮勇殺敵,即便等待他們的是死亡也在所不惜。
四、結(jié) 語(yǔ)
梅爾·吉布森執(zhí)導(dǎo)的《血戰(zhàn)鋼鋸嶺》采用辯證的批判敘事方式,還原了二戰(zhàn)英雄戴斯蒙德·道斯的傳奇經(jīng)歷,他在鋼鋸嶺之戰(zhàn)救下的75人幾乎是人們不敢想象的奇跡,當(dāng)被拯救者以為自己只能死在鋼鋸嶺之上時(shí),是戴斯蒙德給予他們新的生命,給了他們繼續(xù)生活的機(jī)會(huì)與勇氣。影片將敘事結(jié)構(gòu)一分為二,構(gòu)成了傳統(tǒng)的二元對(duì)立敘事結(jié)構(gòu),但是前期的敘事是為了后續(xù)戰(zhàn)爭(zhēng)情節(jié)做鋪墊,讓戴斯蒙德堅(jiān)持信仰的行為變得順理成章,也凸顯出他能夠在如此殘暴的戰(zhàn)場(chǎng)上依舊堅(jiān)持信仰的行為的可貴。導(dǎo)演梅爾·吉布森用這一真實(shí)歷史人物的事跡書(shū)寫(xiě)了一場(chǎng)另類(lèi)的戰(zhàn)爭(zhēng)場(chǎng)景,戴斯蒙德對(duì)信仰的堅(jiān)持也是美國(guó)文化中個(gè)人主義的一種表現(xiàn),他忠于自我、堅(jiān)持自我,即便是放棄自己的愛(ài)情、離開(kāi)自己的愛(ài)人和家人,甚至是放棄自己的生命,他依舊選擇堅(jiān)持信仰帶給他的指引,這也讓《血戰(zhàn)鋼鋸嶺》具有更加深刻的宗教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