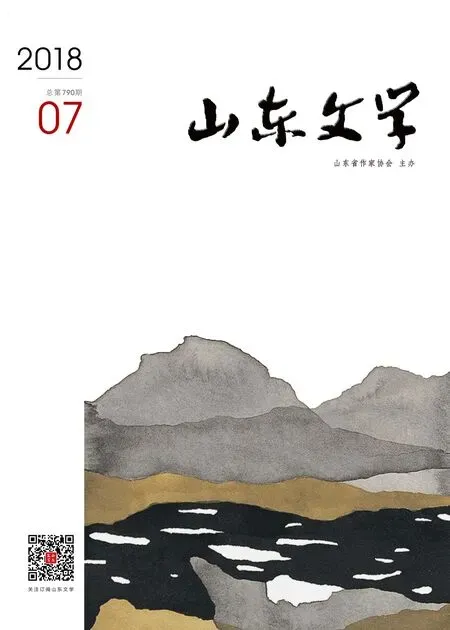友和愛的殤逝
陶 林
記得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在他的《約翰·克里斯朵夫》中曾經寫下過這樣的一段話:“人生的苦難是不能得一知己,有一些同伴,有些萍水相逢的熟人,那或許還可能。大家把朋友這個名稱隨便濫用了,其實一個人一生只能有一個朋友。而這還是很少人能夠有的福氣,這種幸福太美滿了。一朝得而復失的時候,你簡直活不下去,它無形中充實了你的生活。它消失了,生活就變得空虛,不但喪失了所愛的人,并且喪失了一切愛的意義。”
這是一段并沒有太多深意的話,當羅曼·羅蘭用一種極其平淡的口吻將它寫在自己的作品中時,或許,他自己也沒意識到,它將是藝術的另一個領域里、另一位大師命運的最真實寫照,同時,他也不會意識到,它將成為有關友愛之中人倫情感的最有力的洞析。
一直以來,作為一個為繆斯女神所俘虜的青年,我關心著人類歷史上那一個個被千萬人的景仰擦得锃亮的名字。有位文藝前輩說過:“音樂是天空的藝術,文學是大地的藝術。”是的,當我堅定地行走在大地上時,我忍不住再次要抬頭仰望我們共有的天空。這兩者其實距離并沒有我們所設想得那么遙遠,正如六十年代鮑勃·迪倫的那首歌曲所暗示我們的:人們其實并不需要抬那么多次的頭就能看見天空。我非常明確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地平線的方向上,大地和天空本是融為一體的。
于是,我不得不提起柴科夫斯基了,那位讓天鵝輕輕跳起芭蕾舞的大師,那個被全部的悲愴所擊倒的男人。我們都知道,柴科夫斯基是俄羅斯音樂的最高峰,為俄羅斯音樂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這位音樂天才,五歲時就能根據莫扎特、羅西尼歌劇中的詠嘆調主題在鋼琴上隨意變奏,很早就師從鋼琴大師魯賓斯坦,并成為他的得意門生。1866年,他還是一個26歲的青年時,柴科夫斯基就成為了俄羅斯音樂最高學府——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教授。至今,這個俄羅斯最高音樂殿堂里還矗立著他不朽的塑像。我們還知道這位天才是11部歌劇、3部芭蕾舞劇、6部交響曲還有100多首歌曲的作者。他的名字與《葉甫蓋尼·奧涅金》《黑桃皇后》《胡桃匣子》《睡美人》密不可分,代表著音樂世界的一座山形獨特的勃朗峰。當然,還有那無可替代的《天鵝湖》。無論是芭蕾舞樂的視角,還是全部音樂的視角,它代表著美的極限。
我關注較多的卻是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那個以悲愴命名的交響曲。當我在電腦中寫作這篇隨筆時,作為背景音樂的就是這支曲子。它反反復復地鳴奏著,用許多充滿魔力的音符編織出一顆悲慘的內心。我可以清楚地把握到這顆內心的愴痛,所有的哀愁、掙扎、希望、凄惻、啜泣、戰栗、迷茫、抑郁、吶喊、傾訴,交錯紛亂,清晰有序。或許,我能聽到并沒有我寫下的這么多,又或許,我寫下的根本沒有標識出我聽到的一半。但是,我完全沒有拿文字去與音符試比高的愿望。從那令人潸然淚下的主旋律,到苦悶中輕盈嬌柔的舞曲,直到最后死亡在哀訴中無可阻擋地降臨,倘若一顆心靈確實會在悲哀中崩潰的話,那么,沒有任何聲音能勝過《悲愴交響曲》對那一過程的描摹了。在文學的大地上,我唯一能看到一位同樣屬于俄羅斯的文學大師能準確無誤地做到這點,那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
借助于悲愴的尾音,我忍不住想預先寫下這樣的一個判斷:上帝給予了天才以悲愴的理由,于是,天才就給予了所有人一個比天堂還要精美的世界。當整部交響曲在我的電腦里漸漸消失的時候,我將為自己的判斷追索全部的理由。于是,一切又回到了本文開頭羅蘭的那個命題中去了:“它消失了,生活就變得空虛,不但喪失了所愛的人,并且喪失了一切愛的意義。”以我對這位與陀斯妥耶夫斯基媲美的音樂大師的崇敬,他為悲愴所吞噬的全部細節,將如月光般照射進入我的想象,支撐起我對那些獨特靈魂的判斷。
一
我們都知道,比起文學,音樂其實是門相當風光的藝術。金色大廳里萬眾矚目中的揮灑自如,紫色廣場上的引吭高歌,哪怕是一個不知名的小酒館里即興發揮,一旦音樂聲響起,釋放出音符的藝術家必定會立即成為焦點所在。從某一種角度上來說,音樂首先是一門技藝,那種必須具備清秀脫俗的面孔,然后能伸出修長的手指在鋼琴邊微笑的技藝。在這門技藝達到爐火純青之前,天賦被反復強調,艱苦的訓練被反復強調,還有就是能夠從容不迫地面對大眾展示自己的心態需要培養。最好的音樂是能讓全世界都為之歡呼并頂禮膜拜的音樂。在群星璀璨的音樂大師中,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比如說音樂的皇帝貝多芬,即使那些適應洛可可藝術風味的王公貴族們如此厭惡那咆哮、那氣勢、那力度,也非常嫉妒他所贏得經久不歇的三次鼓掌,但他們沒法否認桂冠當屬于這位失聰的天才。比起太陽的光輝,一些小蟲舉翅的遮擋顯得那么微不足道。或許有巴赫險遭湮沒的例子,但在他的遺作遭遇到門德爾松時,這位鋼琴演奏之父立即將全部的藝術生命給復活了。
然而,柴科夫斯基卻是位天生害羞的音樂家,雖然他儀表俊美,而且風度翩翩,具有著交際場上所必需的一切“硬件條件”,對異性有著很強的吸引力,但他對交際充滿了恐懼,決不愿輕易地拋頭露面,而且似乎并不怎么熱衷于與女性交往。在心理學上,這是一種典型的封閉型人格,標準的抑郁質性情。青年的柴科夫斯基曾經愛上過一位歌劇演員,并一度準備與她結婚。但可惜的是,世俗的暴力最終葬送了柴科夫斯基的初戀,因為種種的原因,那位異國的意中人最后還是離他而去。這次夭折的戀愛給了性格孤僻的柴科夫斯基以致命的打擊。在他內心深處,這一打擊的力量被保留到了1877年,到了柴科夫斯基37歲的時候,使得他一直以一種老光棍的方式生活著。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我想到了卡夫卡,同樣是一個生活在孤獨與不安之中的老光棍。我更有興趣在此將他們作一個小小的類比:一個孤僻的文學大師和一個孤僻的音樂大師,他們為兩個彼此不同的世紀所分隔,一個二十世紀,一個十九世紀,卻相似地為一種情緒所困擾。于是,兩人中一個用文學作品闡釋出了荒誕,而另一個則用音樂作品詮釋出了悲愴。這或許就是現代主義與古典主義的區別所在,但感覺中,我更相信這是人格上的分別所致。為絕望和孤獨所包圍的卡夫卡擁有著錯綜復雜的文化環境,這使得他不得不反復敲打每一種侵襲自身的情緒,好像一個考古學者在反復琢磨著古老陵墓里的利刃一樣,最終能認定的卻是那些利刃是用以自殺的。但柴科夫斯基不同,他的絕望和孤獨更多地籠罩在一個質地單純的文化背景中,而且這一背景曾經成功地醞釀出陀斯妥耶夫斯基這樣純粹的絕望者,那么,在另一個領域里醞釀出柴科夫斯基也不是什么令人驚奇的事了。
作為卓有成就的一個藝術家,柴科夫斯基的初戀以失敗而告終。可能對于常人,這一失敗并非什么左右命運的事件。我們通常認為,更好的戀人將是下一個。但藝術家注定要有的偏執摧毀了柴科夫斯基,像拖延一場災難那樣,它將他的婚姻拖延到了若干年之后,拖延到他37歲的時候。正如我們通常所認為的,這時他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光棍了,就跟卡夫卡一樣。
二
我們知道,在人類全部婚姻的歷史上,最糟糕的婚姻記錄不是花花公子、富貴人家、負心漢、負心女以及帝王將相的婚姻,雖然他們也糟糕透頂,但絕對沒有藝術家的婚姻那么糟糕得耐人尋味。有句耳熟能詳的西方諺語是:“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的時候,也同時會為你打開另一扇門。”還有一句話:“在每一個糟糕背后都藏著一個更糟糕。”這兩句話拼合起來就能代表柴科夫斯基與梅克夫人全部相遇的經歷,而這次的偶遇又將和柴科夫斯基最為糟糕的婚姻記錄捆綁在一起,并且成為造成其糟糕的最大肇因。當柴科夫斯基遭遇到梅克夫人的友愛時,對于他來說,實在是難辨其幸耶或者是不幸。
梅克夫人是個富有的寡婦,和任何一位有教養的貴婦人一樣,她有著自己一個偏執的嗜好,她相當熱愛音樂,并且她本人有著極高的音樂修養。與有些貴婦人不同的是,梅克夫人不怎么喜歡社交。這位前鐵路大亨的遺孀只讓一位客人進入她家豪華的客廳,那就是俄羅斯著名的音樂家魯賓斯坦。他是柴科夫斯基的恩師,不僅如此,他還是一個成功的音樂教育家,他還開辦了較負盛名的彼得堡音樂學院。隨便要說一下,柴科夫斯基本人也是一位相當成功的音樂教育家,他著有《實用和聲教程》《和聲簡明手冊》兩本教材,而其中的《實用和聲教程》成為世界音樂教程的典范著作之一。這位大名鼎鼎的魯賓斯坦先生經常到梅克夫人家串門,在她那金碧輝煌的客廳里為她免費演奏一些美妙的曲子。這些曲子有的是一些古典的名作,有的是時下流行的作品,還有就是魯賓斯坦本人的得意之作。我們可以設想,在壁爐旁的那架鋼琴上,美貌的少婦能聽到些什么。以她的口味,首推的還是歐洲那些已經進入經典史的名家們:亨得爾、海頓、莫扎特、伯遼茲、門德爾松。我估計,貝多芬的可能性不大,因為這位音樂皇帝的作品不怎么適合那種曖昧的場合。
1876年12月,一個相當寒冷的晚上,照例來訪的魯賓斯坦為梅克夫人帶來了一份特別的禮物——自己得意門生的得意之作。可以想象,在沒有彈奏那個曲子之前,魯賓斯坦一定諱莫如深,他一定會對梅克夫人說:“哦,夫人,今天我又給您帶來了一個音樂天才的作品。”夫人則會小俏皮一下:“所有卓有成就的音樂家都是天才,包括您自己。您該不是又譜出一部得意之作了吧。”借用一下大仲馬的幽默,我為魯賓斯坦設計的臺詞是:“哦,我的最得意之作就是發現了那個音樂天才!”當然,假如這段對話出現在小說里而不是這篇隨筆里,它會更容易讓人信服一些。不過,管它什么文體呢,人生得意能幾回。
魯賓斯坦為梅克夫人彈奏的是柴科夫斯基交響詩《暴風雨》的片段。貫穿著柴氏音樂特有的美麗與憂郁,猶如一把鋒利無比的劍,樂曲徑直刺入了梅克夫人的內心。很自然地,她向魯賓斯坦詢問起樂曲的作者來。魯賓斯坦這時才告訴她,那是自己得意門生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同時,他還向這位貴婦人詳細介紹了有關這位門生的其他一些情況。比如說,像很多年輕的藝術天才一樣,他正身陷于貧寒的困頓之中,生活常常是捉襟見肘云云。總而言之,日子很不好過。這番介紹一下子打動了梅克夫人的心,她決定資助這位毫無疑問的未來的音樂大師。
三
在歐洲,由一個貴婦人出面資助一些年輕的藝術家是很正常的事情,貴婦人們需要年輕的藝術家們充實自己的沙龍,裝點自己百無聊賴的感情生活。為了生存和出人頭地,藝術家們也樂于歸入這些貴婦的翼護之下,從而有個活路,并得以維持自己的藝術創作,或者幫助自己更好地為社會所接受,這種風氣在法國尤甚,比如說盧梭、伏爾泰、巴爾扎克,都曾經托身于那類貴婦的庇護。俄國的貴族們都是非常鐵的“法國迷”,他們處處效仿法國人,這點也不例外。所以說,梅克夫人決定出資幫助柴科夫斯基倒也不只是一時心血來潮的原因。對于她來說,或許只是其貴婦生活所必須的一個方面而已,或許,梅克夫人有著一個憐憫之心,她意識到了決不能讓這位音樂天才埋沒于貧窮之中。但對于柴科夫斯基,這筆資助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往實處里說,就是關系到人生的頭等大事,吃飯問題,或者說,能否吃飽飯問題。用一句非常市井的話來說,寫音樂是寫不飽肚子的,諸多音樂前輩大師的命運就是很好的教材。
正在貧寒、苦悶、彷徨之中越陷越深的柴科夫斯基能意外地收獲到這份資助,順帶還有一位少婦的不乏友善的仰慕,自然是無比地感激。因此,他是沒法拒絕的。梅克夫人也是個非常講究分寸的人,當她給予柴科夫斯基以資助的時候,她都說是給予他一筆基于他偉大作品的酬勞,這更令這位害羞自負又敏感的天才感激零涕。是的,他還有什么好說的呢,這是份體面的支持,情深飽滿的支持。在寫給梅克夫人的信中,他是這么說的:“如果不是有了你的友誼和同情,我一定會發了瘋而且毀滅了。你所給我的一切全是一個安全的錨,你把我將用盡的才氣又聚集起來,然后使我再度走上了音樂之路。”從柴科夫斯基這段聲情并茂的表白中可以準確無誤地看出,在他的判斷中這場友誼的出現意義很重要。當然,友誼是在不斷的資助和交往中慢慢培養起來的,但在那富有傳奇色彩的一開始,它就注定要朝一個高度唯靈化的方向發展。恰如柴本人所描述的:“一個安全的錨。”它的作用不是晾曬在陽光燦爛的甲板上,而是在深水的最底層,以難以捉摸的方式,用唯一的并且是最小的體積維系著全部的龐然大物。那龐然大物就是生活、藝術和生命本身。
在梅克夫人這只細錨的保護下,柴科夫斯基的才能閃現出最燦爛的光華,美妙絕倫的作品開始在他的筆下源源不斷地涌出,就像是一股無可遏止的急流。用藝術上的術語來說,他迎來了創作上的高峰期。然而,與我們以常規心態所設想的友誼不一樣的是,柴科夫斯基與梅克夫人奇怪地從不相見。他們之間交流思想和情感的唯一方式就是通信,并在信件中交換照片,也就是說,他們的友誼是建立在鴻雁傳書的基礎上的。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他們其實是一對筆友。即便當這種友誼漸漸發展成為愛情的時候,他們最本質的關系還是一對筆友,純而又純的柏拉圖之戀。馬克·吐溫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話,他認為友誼的書信往往是對人最有好處的。但我的理解是,在通訊還不算太發達的那些時代里,純粹依靠書信的維持的交往是令人疑竇叢生的。它一方面有其堅固性,但對人往往有壞處而沒好處。太純粹的東西總是令人生疑而且極具危害,就如毒品,越是純粹就越是可怕。請原諒我這樣草率地論斷,因為與一個純粹的音樂家相比,純粹的作家們太了解人性的種種不確定因素了。雖然有很多作家,比如蕭伯納、莫泊桑,都遭遇過類似柴的情況。甚至,包括寫下這些文字的我自己。
四
在寫給柴科夫斯基的信中,梅克夫人是這樣說的:“你愛音樂太多了,因此來不及愛女人,我知道你的生涯中有過一次愛,但我認為那樣的愛是柏拉圖式的。這是一半的愛,是一種想象中的愛,而不是心上的愛。”她指的是柴科夫斯基青年時代那場導致他性情劇變的戀情。應該說,梅克夫人的話是相當正確的,柴曾經所面對的就是一種純粹的柏拉圖之戀,一種“一半”并且“想象中的”愛。但她沒有意識到的是,她將要給柴所帶來的是一次更加“柏拉圖”的愛情,純粹的紙上之戀,純粹的想象之戀。
因為沐浴著想象中友誼溫暖的陽光,在藝術殿堂里漫游的柴科夫斯基變得非常有才氣。不久,他就為自己的朋友獻上了一曲著名的《第四交響曲》,在這首曲子的總譜上,柴科夫斯基寫道:“獻給我最好的朋友。”這部交響曲是柴科夫斯基最具喜劇性的作品。它的節奏悠揚又美好,充滿了新鮮的活力,雖然有時也流露出柴科夫斯基難以掩飾的憂郁,但歡樂是無法替代的主旋律。用所有對藝術充滿敏感的耳朵去諦聽,我們很容易就能體會到哪兒布滿了甜蜜,哪兒布滿了柔和,哪兒布滿了溫暖,就像是在聽取一位友人在傾吐內心的隱衷與歡樂。
這部充滿才華和人性之美的作品獲得了理所當然的巨大成功。1878年冬,當它在莫斯科首演時,作為承受這份禮物的梅克夫人不惜帶著病、冒著風雪去聆聽。無疑,她比任何一位聽眾都要幸福。因為,在第二天,她就給遠在意大利訪問的柴科夫斯基拍去了一份電報,祝賀他的成功。當然,這也應該被看作他們友誼的成功。世俗的鮮花和掌聲,引起不了這位音樂大師的興趣,相反,他在極力回避著它們。惟有摯友的賀詞才令他陶醉。像每一個藝術家會做的那樣,柴科夫斯基做了一個非常有藝術感的回報:他當即寄贈了六片花瓣給梅克夫人。毫無疑問,當梅克夫人收到那六片花瓣時,它們都應該枯萎了,但梅克夫人還是被那夾在信中的花朵所擊倒。在激勵性的回信中,梅克夫人寫道:“花使我陶醉,我嗅著它的香味,心里帶著一種傲然的歡喜。我愛樹,甚于愛花,因為樹比花更有力量。” 是啊,樹要比花更有力量,這位夫人陶醉得甚至有點得寸進尺了。
花朵通常用來被形容兩種東西,一種是美好的,比如美貌;一種是短暫的,比如年華。而事實上,這兩者又是一體的。當他們忘情地用花朵作為幸福的標記時,他們都注定要承擔那美好與短暫的結合體。我記得劉小楓博士曾經寫過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有關于卡夫卡的愛戀經歷的,叫《一片枯葉上的溫濕經脈》。借用這源自于卡夫卡本人經典的象形,我們可以將柴科夫斯基和梅克夫人的這段交往命名為:“六瓣枯萎花朵上冷凝的濕香”。
我們知道,老光棍柴科夫斯基在37歲時被婚姻這只強行蹦達進他生活的小球打破了原有的節奏。那是1877年左右,也就是與梅克夫人相交甚厚的時候。就像是契科夫筆下的那個套中人,這位在藝術中才華橫溢而在生活中疑慮重重的大師聽從了家人的安排,與一位叫安東尼娜·米林高娃的姑娘結識了。在那位姑娘的苦苦追求下,不久后,柴科夫斯基終于答應和她結婚了。這將是一場不恰當而且相當糟糕的婚姻。那位成了柴科夫斯娃的女性沒有將人倫的歡愛帶給柴科夫斯基,而是像潘多拉那樣釋放出無盡的痛苦卻唯一保留了希望。在寫給梅克夫人的信中,柴科夫斯基這么沒心沒肺地抱怨道:“安東尼娜并不使我害怕,她只是使我沮喪。可憐的女人,為了使我的生活愉快,她已經做到了能夠做到的一切,然而我卻以最大的憎惡去看待這一切。”是的,最大的憎惡,這位自私的音樂天才道出了內心的全部真相。這讓我不得不懷疑,是不是對于某些藝術天才來說,他們生來就被判定孤獨這種刑罰,被剝奪在日常的人倫中享受愛的權利。
因為那內心中的憎惡的驅使,在一個寒冷的冬季里,柴科夫斯基乘著夜色離開了自己的寓所。他將自己為迷亂所左右的身體交給了寒冷的莫斯科河(這又令我想到了同樣投河的伍爾芙)。然而,或許是河水太淺了,或者是還放不下自己的藝術,投河的柴科夫斯基并沒有被死神所接納,這一期限被延遲到了1893年。他只是感染了風寒,醫生認為他必須更換環境,靜心療養,而且再不能回到妻子身邊了。于是就有了他溫暖的意大利之旅。如卡夫卡悔掉婚約有異曲同工之妙,柴科夫斯基不惜用一種痛苦來擺脫另一種痛苦,以期獲得某種靈感的產生。他成功了,又恢復到一個不折不扣的老光棍生活中了。但是,痛苦究竟蔓延到哪里了呢?可憐的人啊!
五
對待柴科夫斯基的這場婚姻,他的摯友梅克夫人是如此反應的,她在回信中如是寫道:“你知道不知道,當你結婚的時候,我是多么地難受!在我心中好像有什么東西破碎了,想到你和那個女人親近,我簡直受不了……當你和她搞得不愉快的時候,我竟高興起來!我恨那個女人,為的是她不能使你快活,但如果你和她生活得非常歡快,我會百倍地恨她。我認為她把屬于我只應屬于我的東西掠奪去了,把我的權利剝奪了過去,因為這世間,我愛誰都不及愛你,我認為你的價值超過了一切。如果這幾句話使你煩惱,請原諒我這不能自制的自白吧。”
多么痛快的一段自白,簡直是歇斯底里。不需要作太多的分析,所有人都能讀出這封信里的蠻橫,那種只有情不自禁的人才會有的蠻橫。那樣露骨,那樣不近人情,全然不顧柴科夫斯基的幸福,也毫不尊重安東尼娜。在這場博弈中,她完全將自己扮演成一個霸道十足的強者,不惜犧牲柴科夫斯基的現實生活來滿足那似乎極端唯靈化了的內心,和純粹得似乎不可理喻的愛情。如果說,安東尼娜失去的只是一個丈夫的話,那么,梅克夫人獲得的就是整個柴科夫斯基。他成功地為她獻上了《第四交響曲》,還有那“六瓣枯萎花朵上冷凝的濕香”般的愛情。
那么,是否能將那么多的責難真正加在這個以柔弱為名的女人身上呢?不能,那樣也是不公平的。對于梅克夫人,在后半生的時間里,這份由友誼催化出的愛情已經成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了。她也曾嘗試過將這鴻書傳情轉化為真正的花前月下,轉化為鋼琴之畔的持手共奏。畢竟,即使是極為高雅的音樂也有其合理世俗化一面,這不同于孤燈下文學的探索。那種夫唱婦隨、實實在在的感覺的確叫人神往。可是,柴科夫斯基本人恰恰也是個有藝術癖的人,他對男女之情的淡漠可以作為一個典型的心理癥狀來分析了。縱使梅克夫人再努力,柴科夫斯基也不會讓人間的歡樂來干擾他藝術天國的痛苦的。梅克夫人知道,她是沒有成功的希望的,于是在最后,她選擇了放棄。在1890年,這個十九世紀最后十個年頭的開端,她作出了一個左右他們兩人生命的決定。
沒有比藝術家的感情和婚姻更糟糕的事了,我們可以指出柴科夫斯基,也同樣可以說是凡高、貝多芬、莫扎特、波德萊爾,可以說陀斯妥耶夫斯基,甚至是托爾斯泰。有人因為這糟糕而得福,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當他經歷了一生婚姻和命運的蹉跎而換來安娜悉心的真愛時,他變得無與倫比,在短短三年“唯一的日子”里寫下了最后最有力的輝煌;有人因為這糟糕而蒙難,比如托爾斯泰。他離開了深愛著的妻子,走向俄羅斯的荒野,死亡一下子抓住了他。但不管怎樣,和柴科夫斯基一樣,他們都是不幸的。
六
1890年9月,梅克夫人寄給了柴科夫斯基最后一筆數目可觀的錢,同時還寄去了最后一封信。在信中,她表示將停止與他的通信,并請求柴科夫斯基別忘記她。她并沒有解釋這樣做的原因。
不難想象這封信給予了柴科夫斯基多大的打擊。用崩潰還不足以表達他那張皇的程度,他接連寫了幾封信給梅克夫人,但都杳無音訊。為此,他開始無可挽回地惶惑、悲傷,甚至漸漸變得瘋狂。他忽然覺得自己這十幾年來一直是一個有錢婦人的玩物,而且一朝遭到拋棄,所有付出的真情都成了泡影。他那強大的自尊給予了他致命的一擊,他悲觀失望地寫道:“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我對人類的一切觀念,對人類至高品德的信念,都已經破滅了!”姑且不去判斷他遷怒于全人類是否說得通,從這一句話中,我們可以測量出他悲傷的程度。
對于同一件事,梅克夫人是這么表述的:“白天黑夜,柴科夫斯基都占據著我的心。這一切似乎都是清白的,但我現在知道那是一種罪惡。”梅克夫人所說的那種罪惡感是針對自己的兒子的。在1890年,梅克夫人生了一場大病,同時,她的兒子也病倒了。在養病之時,她得以靜下心來,反思自己這段感情經歷,同時認真地照看自己的兒子。這兩重的內心生活使她有了一種愧為人母的強烈自責。作為一個母親,她發現,這么多年來自己對孩子關心得太少太少了,她只是如此專注于一件事物,那就是柴科夫斯基的音樂。兒子的病痛喚回了一個母親,磨滅掉一個藝術大師的信徒。幸耶?不幸耶?真不好說。
失去了梅克夫人之后,柴科夫斯基的名聲卻越來越響亮。他的大名到處被人提起,不僅在俄羅斯,在歐洲,也在美國。越來越多的鮮花和掌聲涌向這位大師,與之同步的,他內心的創痛卻越來越深。他希望用不斷的成功來換取梅克夫人的注意,哪怕是只字片語。可惜,他只保留了失望。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成功不能補償心靈的痛苦。”這使得他很快墜入了衰老,頭發花白、脫落,并像所有高齡的老人那樣步履蹣跚。往日藝術宮殿里的驕子已經心力交瘁。得之于斯,失之于斯,柴科夫斯基只有將內心的苦楚傾注到他最后的絕唱中去了。于是現在,我就得以在電腦里傾聽這首著名的《第六交響曲》。
1893年,譜寫《第六交響曲》的柴科夫斯基一次次地失聲痛哭,淚水成了他的雙眼不可更改的裝飾。有很多次,因為悲傷過度,他不得不中止寫作。內心真摯的獨白,輕微泛起的嘆息,誠懇的請求,還有淚水和生命的終結都在五線譜上交織成一片。假如你沒有傾聽過這首曲子的話,我要祝福你,你是個快樂的人。
在《第六交響曲》上演一周后,柴科夫斯基就與世長辭了。隨后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梅克夫人也離開了人間。這一前一后的一段過程里,沒人知道發生了什么,或者,誰都知道會發生著什么。總之,人類歷史一段最奇特最真摯最不可理喻最最難得最最復雜的友和愛就此變為一段趣話,在悲愴交響曲的節奏中就此湮滅。
七
我好幾次見過柴科夫斯基的照片,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雙抑郁又充滿疑慮的眼眸。對于柴科夫斯基之死,史家歷來爭論頗多,有人說他死于霍亂,有人說他因為同性戀的緣故而被沙皇賜死。我不是職業的史學家,無從去考證他的真正原委,也不宜作出我自己草率的判斷。在《友和愛的殤逝》之名下紀念的,僅僅代表一段趣話而已。作為一個鐘情于繆斯詩藝的寫作者,現在,就讓我用普希金的詩篇結束這段趣話:
在你孤獨悲傷的日子里,
請你悄悄地念一念我的名字,
并且說有人懷念我,
在這世上我活在一個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