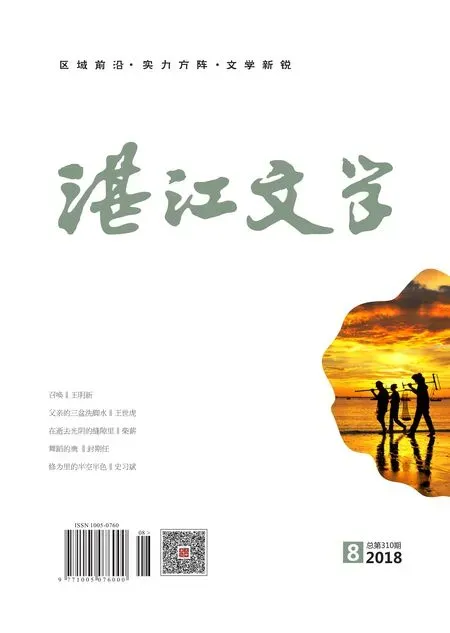在逝去光陰的縫隙里
◎ 柴薪
白鷺記
“西塞山前白鷺飛。”多年前,我曾在一個綠樹環抱的小山村看到白鷺,黃昏,一只,兩只,三只,四只,七只,八只,十幾只從遠處的天空飛來,棲息在村子茂密的樹冠上,如雪片紛紛。
白鷺飛起來或落下來的姿態,極美,風度翩翩,像古代穿白衫的翩翩公子,有一種風流倜儻之美感。
白鷺享有自身的自由,它可以飛,也可以落,還可以行走。王維寫過“漠漠水田飛白鷺 ,陰陰夏木轉黃鸝。”杜甫說“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黃鸝雖也鮮麗、漂亮,叫聲宛轉,但兩者無法比,沒有白鷺的超然脫俗之態。我一直認為,白鷺是詩性的,天然富有詩態的美感。
《五燈會元》里記載:“白鷺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真是一種生機勃勃的生命存在,飽滿的,飛揚的,活潑的,歡快的,沒有一絲頹廢和悲涼。雪隱白鷺,雪沒了,白鷺卻還在,天地一新,那無邊的白雪,都化作了一江春水。
白鷺和大多數鳥類一樣,似乎是敏感的,機警的,膽小的。岑參的“吹笛驚白鷺,垂竿跳紫鱗。”李白的“白鷺拳一足,月明秋水寒。人驚遠飛去,直向使君灘。”不要說你靠近它,連笛聲也能驚跑它。所以說,最好能遠遠觀它。
而王勃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用這種如篆之絕筆似乎寫盡了白鷺的美艷與驚艷,讓后代的文人廢筆無言兀自嘆息無以為綴了。
桂花記
這個春天,都沒怎么看花,沒想到時間過的真快,一不留神“嗖”地一下過去了,轉眼就到了秋天,轉眼桂花就盛開了。
立秋后的某一天,晚飯后,感覺有點無聊,一個人到府山公園獨自徘徊。卻不想被空氣中桂花的香氣所縈繞,無聊中突然有了興致,便順著香氣不知不覺來到一片桂花樹前。那陣陣初秋暮晚的桂花香,濃郁熱烈到讓我無奈的程度,像是某種隱隱的悸動。我不由想起郁達夫的小說《遲桂花》,在郁氏的小說中,除了《春風沉醉的晚上》,我最喜歡這一篇。郁達夫不但是天才的小說家,更是天才的詩人和散文家,是那種真正意義上的天才。或許我也是一個喜歡懷舊的人,《遲桂花》本來也就是一篇懷舊的作品。由郁氏的《遲桂花》,又想到了郁氏的不知所終?不知魂歸何處?至今也不知道他是否回到了富陽的故鄉?
桂花的芳香纏,綿,濃,淳,厚從桂花樹上陣陣襲來,又從府山公園的上空陣陣溢出。讓我覺得有點恍惚,這香味讓我覺得性感,露骨,銷魂,讓我覺得生活在這世上又是多么美好!這一瞬,讓我覺得似乎猶為年輕,青春猶在,獨自高興一回。
王維說,“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
宋之問說“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飄。”其實,桂花的芳香無意間聞到才是最美的。
秋天既然到了,用不了多久,也將會過去。大多數草木減緩或停止了生長的速度,開始自己的衰老。最后,該留下的自然會留下來,該離去的總歸要離去。桂花也開始零落,一朵一朵,一片一片,下起了桂花雨,樹冠下面的大地上一片金黃,樹梢上殘留的,最終將和天空一樣變得空無一物。
格桑花記
十月的一天,見天氣晴好,便去荊溪看格桑花,但見格桑花全開了,一片絢爛,美麗,還有的仿佛已殘了。兩年前,在江山西山下的老火車站附近,也看見一片格桑花,似乎整個老火車站附近都淹沒在一片沸沸揚揚的花海里,花海似乎也掩蓋了某些破敗與荒涼。老火車站已搬遷,改成了公園,空地植上草皮和其它中規中矩的園林樹木。一切井井有條,讓我認不出原有的模樣。不知為什么?我一直認為,人為的井然有序,反而不如大自然的雜亂無章。似乎喪失了那種(原生態的)自然的氣息。氣息,是沒法模仿的。就像人身上的東西,最無法模仿的,就是氣質。模仿的東西,乍一看,也許也很美,但就是缺少那種最真切的最回味的和最意蘊的最天然的東西,就像某些影視城中的“故宮”,而非北京的原故宮一樣,是經不起反復對比的。
格桑花開的時候,此時天氣尚溫,尚未到蕭殺的季節,但也不是桃紅梨白、群芳爭艷的高潮時季,格桑花沒有其他太多花木的映襯和烘托,需要靠數量才能形成自己的聲勢,如一株株分散的看去,倒顯得單薄與孤單。
我曾在甘南草原見過美麗的格桑花,當地人叫指甲花,漂亮的指甲花,紅的白的黃的藍的紫的五顏六色熱熱鬧鬧鋪天蓋地漫漫無際似乎一直開到天邊,似乎淹沒了大地上的一切。我沒想到如今格桑花在我們江南在我們衢州的荊溪也遍地盛開了,似乎有燎原之勢。
格桑花原是青藏高原上最普通的一種野花,當夏季來臨的時候,它們會在遼闊的牧場上滿地盛開,它的美麗和樸素,將裝點整個短暫的夏季。 格桑花是生長在海拔較高的濕地的一種植物, 是一種生長在高原上的普通花朵,桿細瓣小,看上去弱不禁 風的樣子 ,可風愈狂,它身愈挺,雨愈打,它葉愈翠,太陽愈曝曬,它開得愈燦爛。這就是寄托了藏族同胞期盼幸福吉祥等美好情感的格桑花。它 被藏族同胞視為象征著愛與吉祥的圣潔之花,它喜愛高原的陽光,也耐得住雪域的風寒。據說,格桑花隨著季節變幻,顏色也會轉變,它美麗而不嬌艷,柔弱但不失挺拔。格桑在藏語里是幸福、美好的意思,所以也叫幸福花。
而現在在荊溪,在我的眼前,格桑花一片明麗,一片燦爛,一片盛放,一片遼闊,比我在江山西山下看到的還要多,還要美,紅紅白白藍黃粉紫的花朵在風中搖曳,我的眼前是一片花的海洋,我似乎恍惚也陷身在一片幸福之中。
男男女女在這樣一片美麗的花海中游玩,似陶醉,也似恍惚,男女之間總會有一種難以言傳的微妙,眼光流盼,剎那間不經意的微微一接,似乎發生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沒發生,這是一種無法去分析的情感,似一種花朵開放般的恍惚。天空是藍藍的,飄著幾朵白云,草色遙看近卻無,但最可愛的卻正是這種未成形的潦潦草草的恰似春天般的春意。
格桑花雖然一大片一大片地盛開,色彩斑斕,卻絕不張揚,跋扈,更沒有明艷、香艷、幽艷、哀艷之情,以及于纏綿悱惻中又夾雜著感世傷生。有的是明麗,清艷,樸素,熱烈,燦爛,美好,讓人產生無限想往的感覺。
我在這一片絢爛的漫漫的花海中冥思陶醉,抬頭遠望,在這一望無際的格桑花的盡頭,就是著名的爛柯山。我想,爛柯山“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王質遇仙”的神話故事在荊溪這片漫山遍野的格桑花的簇擁下,將顯得更加異樣別致美麗更加神密神奇令人神往。
喝茶記
寒露來臨,草木蕭瑟,曰影南斜,白晝一日短似一日。寒露這天,朋友相約去“信安閣”喝茶。喝茶是一件難得的雅事,也是得一時之閑暇。
茶為南方嘉木,古人稱茶為茗,故喝茶,又謂品茗。茶生于天地之間,濯山野之泉,沐天地之露澤,雖寒而不凋,其色常綠常新,郁然如丁香瓜蘆之樹。陸羽《茶經》中說,“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葉如丁香,根如胡桃。”
有一則軼事:北宋時,有一次,蘇東坡從故鄉四川眉山至重慶經長江回京,船至西陵峽時才忽然記起宰相王安石曾有一事相托:“回程時取巫峽江水一罐以供煮茶。”于是,蘇東坡硬著頭皮連忙取了一罐西陵峽之江水權當巫峽之水(心里想,同樣是長江水王安石如何喝得出?),回京時,蘇東坡有些忐忑,親自將水送到王安石府上。王安石大喜過望,遂邀蘇東坡留下一起喝茶,水煮開后,泡上茶。王安石呷了一口,回味片刻,笑著對蘇東坡說,此非巫峽之水,乃西陵峽之水也。蘇東坡大驚失色,佩服致極,作揖賠罪,連忙說了原委。喝茶喝到王安石這份上,不只是高人而是天人了。
由此可見,喝茶需先煮水,好茶還需配好水。而用水之精者,喜山間之泉,杭州人泡龍井茶,常去取虎跑之泉。其次是江河溪流之水,再次是井窟之水,而現代人用所謂的桶裝純凈水泡茶,實因無水可煮,也只能以此代之了。
喝茶,我本是不太講究之人,好比抽煙,也無南北之分,好壞貴賤,曾與朋友戲言,能點著的即可。朋友用的是云南的普洱紅茶,雖煮時工道繁復,但喝時味純可口。
秋末之際,容易感傷,喝茶卻能寬心,坐在信安閣內,靜聽秋風過耳,遠觀樹木搖曳,更遠處高層樓宇,車馬流水,紅塵滾滾,喧喧囂囂,秋天已經被逼仄到了一些不易為人注目的角落。信安閣西面,可觀日之西薄,晚霞翩翩,橫亙在遠天,仿佛無數美妙炫爛之花。天空下遠遠的可以望見衢江,灰白一線,流向由南向北又轉東,曲折委蛇,茫茫不知所終。
時近日暮,天空蒼黃,天色為薄霾所翳,更見蒼茫,內心似乎也徒增一片蒼茫。
而眼前壺內的水聲砰然躍起,似煮水知人生,又如飲茶,初極濃郁,終淡如水,此始于水而又終于水,飲茶即品人生也。
古人有喜收集雨雪寒露之水為煮茶之用的。《紅樓夢》中的妙玉,喜歡用雪水煮茶,而且是梅枝上的雪。蘇東坡被貶海南,叫人收集芭蕉葉上的露水煮茶,此等皆妙人文人雅事爾。而鄉下鄉野農夫用野茶葉,粗瓦罐泡茶,照樣喝的痛快淋漓。唐朝的郁離子,喜歡用從天而降的露水煮茶。寒露過后,露氣將結。每天清晨,路邊草木上無數的露珠晶瑩透徹,看的人滿心歡喜?只是露水易逝,古人歌薤露以寄哀,人生如薤上之露,短暫易逝。
我想,僅為煮茶而收露水,實為暴殄天物。露水宜觀,遍地晶瑩之境,不說收之不易,收了于心何甘,實實在在糟蹋了眼前的這一番美景。
傷感記
衢江流到沙灣的時候,江面變寬變闊,江水也變慢變緩,江面如鏡,波浪不驚,著名的浮石潭就在這里。原來橫在江中的浮石若隱若現并在水位下降時浮出水面。如今,下游不遠處筑了水壩,水位上漲,浮石沉在水下不見了天日,只剩下明太祖朱元璋與浮石的傳說和這一片水域的廣闊與蒼茫。
沙灣的東面,過衢江那邊有個叫徐家塢的村子,秋天的時候,我養的一條“銀狐犬”,過馬路時被一輛轎車撞死了。傷感之余,我把它埋在這個村子后面的桔園里。我記得,我剛走到桔園時,一只大鳥從一條兩邊長滿茂盛灌木叢和雜草的小水溝里突然飛起,然后迅速隱入附近的青枝綠葉之中。我沒看清這是只什么鳥?我只看到它翅膀的羽毛是紅黑色的,背部有一大片褐黃色。我想,一定是我驚到了它,不然它不會飛走的,不知道它會不會飛回來?
埋完好“銀狐犬”后,我繞過這個小水溝,我準備穿過那片茂密的桔林回去。秋蟬在正午時分靜悄悄的,它們只有在夕陽西下時才喧囂起來。
那一瞬,我忽然發現整個桔樹林靜悄悄的,似乎整個徐家塢也是靜悄悄的。
那一瞬,我忽然發現,夏天,寂靜似乎被深深包裹在聲響之中;秋天,聲響則似乎被深深包裹在寂靜之中了。
我記得,夏天的時候我曾來過這里。有許多不知名的昆蟲在草木花叢中飛舞,很輕,很小。有蜜蜂,飛蛾,蜻蜓,蟬,還有蝴蝶,蝴蝶品種繁多,各色各樣,五顏六色,色彩斑闌,大大小小的蝴蝶在草木花叢上飛舞。其實蝴蝶也是一種昆蟲,它們有著小小的身子和大大的夢幻一般美麗的翅膀。不像蜜蜂飛動時嗡嗡作響,蝴蝶飛動時無聲無息,翩翩飛舞,姿態驚艷,曼妙,像探戈,像華爾茲。蝴蝶骨子里就是一個唯美主義者或者說是一個抒情詩人,像席勒,像雪萊,像普希金,像萊蒙托夫,像松尾芭蕉,像德富蘆花,像朱湘,像廢名,像徐志摩,唯美,柔軟,脆弱,易逝,傷感。如今這一切都不見了,秋漸漸開始滲透,滲透周圍的一切,天空遼闊,大地遙遠,只剩下草木開始枯萎,蟲聲消遁,飛鳥遠走。
一切唯美的東西似乎都很脆弱。
唯美的東西似乎柔情似水似乎生來令人傷感。
老鷹潭記
老鷹潭在衢城雙港大橋往西二公里處的孫姜大橋下面,江山港和常山港在此附近匯合后稱作衢江,兩股江水匯合后,江水陡增,江水滔滔浩浩湯湯向北流去。
老鷹潭在孫姜村西邊,過了雙港口大橋向南二公里左右往西經過一條長滿草叢野花的小路再穿過船廠宿舍沿河灘往下走就能走到它旁邊。三十年前,我剛來到這個城市,客居禮賢街,夏天酷熱,下班時,騎著自行車,穿過人聲鼎沸的禮賢街、寂寞的雙水橋、穿過車來人往喧嘩的雙港大橋,常常去老鷹潭游泳,常常模仿偉人也到江中擊水,浪遏飛舟。當時這一帶還沒有防護堤,一切是原生態的,我躺在水面上,看藍天深遂湛藍,看白云悠哉悠哉,看采沙船在我身邊來回穿梭,掀起陣陣水浪,馬達聲驚起不遠處水草叢中的水鳥,常常腦袋一片空白。
船廠宿舍四周有一大片桔樹林,樹葉有的依舊蒼翠,有的已開始變黃有的已飄零。冬日的陽光白晃晃的,藍藍的天空、光線,清涼的樹翳,桔樹椏間裸露出的桔黃色的果實油光可鑒,風中空空的寂寥的鳥巢,還有風中的落葉。在桔林中,我總感到一種莫名的觸動,心中有一點點細微的敏感,摻雜著絲絲塵埃的氣息,還有一點點揮之不去的蒼茫和蒼涼。仿佛是那種自遙遠的漢唐宋傳承來的很古老的心情,仿佛像一首古老的歌謠,在我身上深深扎下自己繁多的根須,然后茁壯成長,結出密密麻麻的種籽,繁衍出更多的花朵和果實,最后通過我,來重新感受這個此刻的世界。
老鷹潭在下午向黃昏過渡的白亮的陽光中,由于一側斜斜江岸的阻擋,一半在清爽的陰影里。潭邊的斜坡和沙灘上以及水邊長著大片大片細小的蘆葦,蘆花還沒有飛白。還有很多不知名的草叢和水草,草木早已枯萎,一只水鳥從水面上劃過,藍色的漣漪一圈一圈向四周擴展一直蔓延到潭的那邊。一只水鳥在另一邊鳴叫,半天一聲,半天一聲,間隔太長了,像一架古琴兩頭的琴樁,中間是繃得緊緊的琴弦般的寂靜。聲音瓷實、短促,又很有穿透力。每叫一聲,仿佛在我心中輕輕彈拔一下。我在老鷹潭這邊坐下來,凝神靜氣,竭力想看清這是一只什么水鳥,可我始終無法看清楚。
這個冬日,我不知道為什么會走到這個潭邊?仿佛從三十年前走來,從一個更遙遠的過去走來,從一個古老的刮著大風的世界里走來。走過一個又一個荒荒落落的年景,走過一個又一個春暖花開落葉凋零的四季更替,走過一個又一個生生死死的生命輪回。走著走著,累了。閉上眼睛,就站在這兒。夢想的腳步慢慢變成老鷹潭中一片顫動不止的江水。最后,它深深沉入潭底,沉入時間的黑洞,深深沉入自己的命運,不能自拔。
三十年時間,彈指一揮間。
我曾經去過許多很遠很遠的地方。人世間,那些開滿野花的小路,我多想多走幾次。那些即將消失的小路,在它們消失之前,我多想都走一走……
這個有陽光的冬日,陽光曬在身上暖洋洋的。天空中和大地上到處是滿滿的青枝綠葉,風吹過,風聲中充滿豐富的細節和內容,風聲聽起來便很繁復。冬天,落葉歸根,大地空闊遼遠,天空鋼藍锃亮,風聲粗棉布般在天上懸著,風聲只是風聲,風聲中什么也沒有。而現在是剛剛展開的冬天,風聲清澈干爽。我在老鷹潭邊靜靜坐著,風一陣陣刮來,把我心中的溫暖一點點刮走了。我不由想起少年時在故鄉嵩溪河里游泳,而從這里沿江山港溯游而上,理論上是可以游到故鄉的。
天空越來越暗,我也慢慢變得空曠。在夕陽消失之前,我滋生把這個老鷹潭帶回去的想法。但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我的這個小小的不切實際的想法只能在我的身體里波動一下,可它卻仿佛從我的身體深處溢了出來,茫茫無際,卻又不知所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