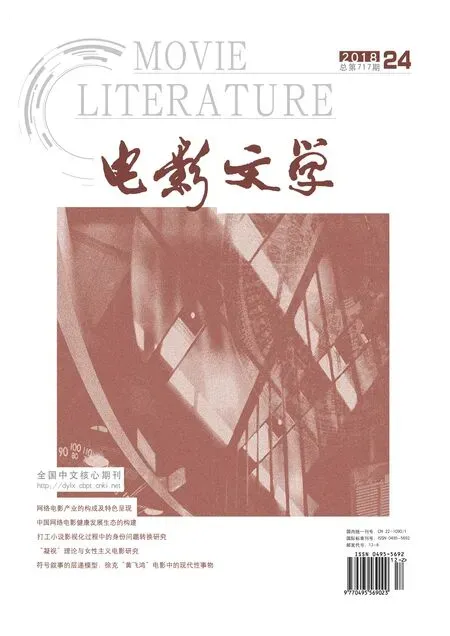《影》的對(duì)比敘事淺談
陳艷華
(呼倫貝爾學(xué)院,內(nèi)蒙古 呼倫貝爾 021008)
電影誕生于1895年,而在十四年后大衛(wèi)·格里菲斯執(zhí)導(dǎo)的,出現(xiàn)了窮人與富人對(duì)比鏡頭的《小麥的囤積》(1909)之后,電影人就開(kāi)始了在對(duì)比敘事上的實(shí)踐。可以說(shuō),這一敘事手法由于關(guān)系著人生成意義、認(rèn)知外界的思維方式,在電影藝術(shù)的發(fā)展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在張藝謀的新作《影》(2018)中,對(duì)比敘事也俯拾即是。
一、《影》對(duì)比敘事的哲思與審美基礎(chǔ)
在《影》中不難發(fā)現(xiàn),電影自始至終都在強(qiáng)調(diào)陰陽(yáng)互斥而又互補(bǔ),兩極對(duì)立而又共生的哲學(xué),而這正是中國(guó)古代文化中,人們對(duì)世界、宇宙長(zhǎng)期秉承的一種認(rèn)知態(tài)度。從當(dāng)代唯物辯證法的角度來(lái)看,無(wú)處不在、此消彼長(zhǎng)、相互制約的對(duì)比矛盾存在于客觀社會(huì)中,這也是電影藝術(shù)建立戲劇沖突,抓住觀眾興趣的關(guān)鍵。以電影中的子虞夫婦琴瑟和鳴一段為例,兩人坐在巨大的八卦的陰陽(yáng)魚(yú)魚(yú)眼上,彈奏彼此的樂(lè)器。而此時(shí),收復(fù)境州的戰(zhàn)役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kāi)。黑與白,男與女,封建夫權(quán)制下的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子虞情緒的張揚(yáng)快意與小艾情緒的壓抑怨憎,藝術(shù)交流的平和美好與戰(zhàn)爭(zhēng)的殘忍血腥等多組對(duì)比,都在畫(huà)面中表達(dá)出來(lái)。子虞與小艾是利用替身境州欺騙君王,奪權(quán)篡位的合作者,他們相互依存,小艾要一個(gè)健康的,能夠順利統(tǒng)軍的夫君維持生存和地位,子虞也需要小艾配合替身做戲。也正是小艾在武學(xué)上啟發(fā)了子虞,讓他想出了克制楊蒼刀法的以陰制陽(yáng),以柔克剛的沛?zhèn)阄渌嚕欢舜擞忠驗(yàn)榕で姆蚱揸P(guān)系而相互忌憚。對(duì)待境州,子虞陰狠無(wú)情,小艾溫柔關(guān)心,子虞割傷境州,小艾則給境州送去傷藥,這些都是鮮明的比較。矛盾最終在子虞被境州殺死,而目擊者小艾保持沉默中達(dá)到高潮和結(jié)局。可以說(shuō),電影以對(duì)比的方式將復(fù)雜的人際關(guān)系、勢(shì)力消長(zhǎng)、倫理道德等符合情理地聯(lián)系到了一起,使觀眾能夠順利地接受電影敘事。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影》的對(duì)比敘事并沒(méi)有停留在明辨是非,善惡有報(bào)等價(jià)值觀層面上。盡管各個(gè)民族在文化深層結(jié)構(gòu),藝術(shù)思維方式上存在區(qū)別,但是在情感和道德的層面上都有著懲惡揚(yáng)善,愛(ài)憎分明的是非觀念,這也是對(duì)比敘事存在的思想基礎(chǔ)之一。在《影》中,這一道德標(biāo)準(zhǔn)卻是沒(méi)有得到踐行的,電影中的人物都被置于黑白灰色調(diào)之中,然而幾乎沒(méi)有一個(gè)人稱得上徹底的黑或白,簡(jiǎn)單的二元對(duì)立原則并不能用以衡量電影中角色的言行。以田戰(zhàn)為例,田戰(zhàn)驍勇善戰(zhàn),與子虞肝膽相照,為了子虞而在朝堂上冒死直言,喊道:“沛國(guó)遲早要?dú)г谀愕氖稚希杈 弊罱K付出了刺傷身體和貶為庶人的代價(jià)。然而他又有可能是沛良陣營(yíng)的一個(gè)潛伏者,正如境州是子虞陣營(yíng)的潛伏者,他完全有可能是以做戲而成為子虞的心腹,最終以“都督何苦自囚于密室,何不取主公而代之”詐出子虞真實(shí)意圖的臥底。而在最后,田戰(zhàn)也默許了子虞與沛良雙雙被殺,自己成為都督的結(jié)局。而相對(duì)單純無(wú)辜,還愿意為了田戰(zhàn)而答應(yīng)婚事的公主青萍卻死在戰(zhàn)場(chǎng)之上。觀眾既不能簡(jiǎn)單地判定田戰(zhàn)是一個(gè)正直或陰險(xiǎn)的人,也不愿意接受背主自立的境州、田戰(zhàn)活了下來(lái),而正直美好的青萍等人死去這樣的結(jié)局。觀眾在集體無(wú)意識(shí)之中有著愛(ài)憎分明的情感道德要求,而電影恰恰不滿足這一點(diǎn),以違背觀眾的審美期待的方式,促使觀眾正視人性的陰暗與命運(yùn)的不可掌握,電影的深度和審美力量也由此體現(xiàn)出來(lái)。
二、《影》對(duì)比敘事的呈現(xiàn)
(一)具體對(duì)比
所謂具體對(duì)比,即觀眾可以從具體畫(huà)面,或前后的銜接較為緊密的一組蒙太奇之間直接感受到的對(duì)比關(guān)系,以及電影中直觀的人物、場(chǎng)景的設(shè)定等。以人物而言,在進(jìn)行人物的對(duì)比時(shí),好萊塢電影曾被認(rèn)為:“好萊塢電影有一個(gè)經(jīng)典模式,即高大威猛的主人公身邊總有一個(gè)滑稽可笑的小人物做陪襯,在面對(duì)一些具體問(wèn)題的時(shí)候,主人公總是一往無(wú)前,而小人物則嘴里絮絮叨叨,但卻膽怯得不敢上前。”這種一目了然的對(duì)比之所以能夠成為經(jīng)典,正是因?yàn)樗掀章迤铡睹耖g故事形態(tài)學(xué)》之中對(duì)敘事角色的“英雄-助手”分類,能夠增加電影的可看性。張藝謀在《影》中也借鑒了這一點(diǎn),但是卻在“替身”這一主題下對(duì)其進(jìn)行了改動(dòng)。
在電影中,“真身”和“影子”就是一組對(duì)比,“真身”子虞作為整個(gè)計(jì)劃的策劃者與他人的操縱者,理應(yīng)屬于“英雄”,而猶如玩偶般的,連正常名字也沒(méi)有的境州則為“助手”。然而,境州所用的是子虞的身份,因此觀眾可以直觀地看到,境州才是高大威猛,相貌堂堂的主人公,而子虞卻骨瘦如柴,形容枯槁,仿佛一具骷髏。在給境州割出傷口時(shí),子虞絮絮叨叨,多用氣聲,手舞足蹈,狀若瘋迷,境州則咬牙忍痛。因?yàn)殚L(zhǎng)期的傷痛以及自我囚禁早已摧毀了子虞的身體和精神,無(wú)怪乎小艾逐漸將自己對(duì)丈夫的感情轉(zhuǎn)移到境州的身上。又如在沛國(guó)與炎國(guó)的交戰(zhàn)中,電影中表示炎國(guó)屬火,楊蒼的刀法至陽(yáng)至剛,而沛國(guó)則屬水,要用陰柔之法來(lái)破解楊蒼大刀,也要用陰謀來(lái)攻下炎國(guó)把守的境州。因此,在楊蒼與境州在江面上堂堂正正對(duì)敵時(shí),沛國(guó)死囚卻趁機(jī)潛水偷襲境州城關(guān),炎國(guó)將士全副武裝,盔甲鮮明,而沛國(guó)死囚們卻身著布衣,靠在傘中扭捏身形的武藝和出人意料的暗器殺傷對(duì)方等,剛與柔,光明正大與陰謀算計(jì)形成具體的對(duì)比。
(二)抽象對(duì)比
抽象對(duì)比則是較為隱晦的,它也為主題服務(wù),但并非所有觀眾能夠讀解。如電影敘事中存在偶然與必然的對(duì)比。《影》中幾乎每個(gè)人都機(jī)關(guān)算盡,自己經(jīng)歷了也為他人制造了太多“偶然”,但也都最終落入到宿命的“必然”中,為黑暗吞沒(méi)。如擁有自我意識(shí)的青萍不愿意和親做妾,偷偷離家出走,混入死囚當(dāng)中,讓指揮官田戰(zhàn)頗為意外,并且在戰(zhàn)斗中,青萍一直極為驍勇,但最終她還是被放言要拿她做妾的楊平重傷而死。青萍的參戰(zhàn),對(duì)于田戰(zhàn)和根本不認(rèn)識(shí)青萍的楊平來(lái)說(shuō)是偶然,楊平更是萬(wàn)萬(wàn)想不到會(huì)死在自己送出的匕首之下。與甘于命運(yùn)安排,服從男性命令的小艾相比,青萍的出現(xiàn)也是偶然,但是在傳統(tǒng)的男權(quán)社會(huì)中,青萍無(wú)論美丑善惡,無(wú)論是否勇武過(guò)人,她的悲劇結(jié)局都是必然的;包括境州原本擁有的是死亡的必然,作為替身他肯定會(huì)被滅口,然而境州卻完全憑借自己的武藝和冷靜連殺楊蒼、子虞和沛良,斗爭(zhēng)出了一條生路,這是偶然,但最終他也有很大的可能被田戰(zhàn)或他人所殺。這一種對(duì)比有著特別的表意功能,比之具體的如陰陽(yáng)、善惡對(duì)比等,更為深刻、含蓄。
一方面《影》迎合觀眾的審美期待,電影中如“女子/陰柔—男子/陽(yáng)剛”,“影子/健壯—真身/衰朽”,“沛國(guó)(兵者詭道)—炎國(guó)(堂堂正正)”等對(duì)比都極為明顯,符合觀眾的審美情趣與先在經(jīng)驗(yàn),另一方面電影又讓觀眾的期待逆向受挫,制造需要觀眾克服障礙才能理解的對(duì)比,并模糊善惡忠奸誠(chéng)偽的界限。可以說(shuō),張藝謀在《影》中讓觀眾看到了對(duì)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