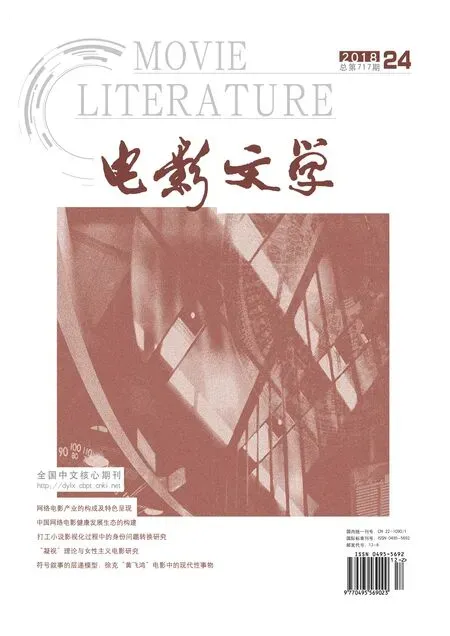《媽媽咪呀2》的敘事策略分析
張 虹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2008年,導演菲利達·勞埃德將《媽媽咪呀》從好萊塢歌舞劇舞臺搬到了電影屏幕,給影視觀眾帶來了歌舞劇特有的聲像融合體驗。故事描述了蘇菲利用自己婚禮的契機,試圖尋找生父的故事。影片通過歌舞與對白的穿插設置,完成了向ABBA樂隊的致敬和愛與自由的主題表達。時隔十年,《媽媽咪呀2》以全新的形象呈現(xiàn)在大銀幕上,導演歐·帕克一改前作風格,將敘事性作為電影的主要特征,減少了歌舞情節(jié)的權(quán)重,通過現(xiàn)實與回憶相互穿插的多線程敘事模式,完成了蘇菲對母親夢想實現(xiàn)歷程的呈現(xiàn)和對唐娜的青春往事的回顧。并通過電影敘事的空間轉(zhuǎn)向,表現(xiàn)出人物的情感認同與對影片主題的表達。
一、多線程的敘事模式
在《媽媽咪呀》中,導演菲利達·勞埃德發(fā)揮自己本為歌舞劇導演的專長,將歌舞作為電影敘事的主要承載方式,使觀眾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劇情中東西方文化與觀念的差異,而以個人情感融入劇情之中,在ABBA歌曲旋律的渲染和高飽和度影像的視覺沖擊下,感受到青春的肆意張揚與對愛與自由的追逐,完成了自己的電影處女作。影片以時間順序為線索,利用單線程的線性敘事講述了簡單的故事,形成了完整的時間閉環(huán)。但是為了充分表達向ABBA的致敬,部分情節(jié)中的歌舞插入不免刻意,使屬于電影特有的敘事性有所淡化。也可以說,《媽媽咪呀》中的敘事是為歌舞服務的,影片完全照搬著歌舞舞臺劇的模式。
在《媽媽咪呀2》中,導演試圖從敘事性上尋求突破。由于梅麗爾·斯特里普不出演任何續(xù)集的演藝原則,《媽媽咪呀2》無法延續(xù)前作的原班人馬,然而也是梅麗爾·斯特里普的缺席間接促成了今天的《媽媽咪呀2》,全新的劇情設置得以跳出舞臺劇的框架更加靠近電影注重敘事性的表現(xiàn)特征。從經(jīng)典敘事理論角度來看,影片利用非線性敘事結(jié)構(gòu),分為兩條線程平行推進劇情發(fā)展。影片剛開始,就用對卡片的特寫交代了前作主體空間——旅館的重新開業(yè)線索,引出后續(xù)蘇菲借旅館實現(xiàn)唐娜夢想的敘事線程,兩分鐘后又通過對唐娜的追憶和一句“我媽媽去哪里都會遲到”的對白引出年青唐娜在畢業(yè)典禮中的青春熱情與自由向往,從而開啟唐娜追逐夢想之旅的敘事線程。自此開始,兩個線程的敘事形成各自的時間閉環(huán)向前推進,并在情節(jié)發(fā)展中不時穿插閃現(xiàn)。影片開始十分鐘后,通過蘇菲與斯凱的電話通話交代了唐娜的離世,使整部影片籠罩在淡淡的悲傷之中,也將觀眾的視線聚焦于蘇菲為完成母親夢想的執(zhí)著行為,并獲得情感上的認同。然而導演并未在唐娜離世的悲傷話題上多著筆墨,依然在蘇菲努力重開母親的旅店和唐娜的愛情故事與開旅店經(jīng)過的雙線程敘事中有序推進。暴風雨的來臨將情節(jié)推向高潮,蘇菲面對的暴風雨是她追逐著母親的腳步追求自由過程中的沖突矛盾。年青唐娜經(jīng)歷的暴風雨讓她結(jié)識了山姆——第一個真正讓她打開心扉面對的愛人,也是在山姆身上,體現(xiàn)了唐娜對于夢想的執(zhí)著和對愛的態(tài)度。隨著劇情的不斷發(fā)展,鏡頭在雙線程敘事中的轉(zhuǎn)換越來越頻繁,導演嫻熟運用影視藝術(shù)特有的蒙太奇手段在不同時空的敘事線程中不斷轉(zhuǎn)換,卻并沒有讓觀眾有突兀生澀之感。與歌舞的運用一樣,蒙太奇的剪輯方法與歌舞音樂的運用都是在為電影的敘事性服務,讓觀眾獲得良好的沉浸式觀影體驗。
二、電影敘事的空間轉(zhuǎn)向與情感融合
后經(jīng)典敘事學的研究賦予了空間新的敘事地位,將敘事中空間與時間定義為合作的關(guān)系,共同構(gòu)成敘事力量。《媽媽咪呀2》中,導演歐·帕克在時間上的雙線程敘事模式之外,充分運用空間的轉(zhuǎn)向來對不同時空的劇情發(fā)展進行銜接,并表達出雙時空敘事線程中人物的情感溝通。
影片中曾多次出現(xiàn)利用相同空間進行不同時空轉(zhuǎn)換的無縫銜接鏡頭。在回憶唐娜的敘事線程,唐娜選擇獨自旅行,鏡頭對皮箱的特寫巧妙完成了機場與巴黎街頭的空間轉(zhuǎn)換,也通過這一簡單的空間轉(zhuǎn)向,表達出唐娜的青春無畏與對夢想的探索。緊接著,通過對天空的特寫完成時空線程的轉(zhuǎn)換,代入感極強。更為巧妙的是,影片在對蘇菲與斯凱通話后的情感矛盾中,多次運用物體實現(xiàn)空間轉(zhuǎn)換,放在枕頭上的照片,衣柜里的襯衫,房間中的墻壁、鏡子等,都成為人物之間感情溝通的媒介與紐帶,在不停的時空轉(zhuǎn)換中,完成對人物情感矛盾的交代和劇情的鋪陳。出現(xiàn)時間與空間轉(zhuǎn)向最多的場景是島上的旅館,旅館內(nèi)部的樓梯、窗戶、門、露臺、床等都引領(lǐng)了平行時空的敘事銜接。最典型是母女二人在旅館小屋中對I
have
a
dream
的合作演唱,旅館是母女二代女性夢想的承載與外在表現(xiàn)形式,對旅館內(nèi)的各種構(gòu)造在不同時代的特寫進行雙線程的敘事轉(zhuǎn)換,除了營造視覺上的和諧和敘事上的連貫性之外,更表達了母女兩代女性在思想上交流溝通和對愛與自由的共同向往與追逐。影片最后的十分鐘,是頗具魔幻色彩的純粹舞臺劇表演。空間定格為歌舞劇舞臺。這是導演歐·帕克對于《媽媽咪呀》舞臺劇的真誠致敬,更是影片主題的升華。在歌舞表演中,祖母、母親與女兒同臺演繹,雙線程敘事不同時空中的同一角色不同時期的演員同時出現(xiàn),在視覺上直觀表達出祖孫三代女性對愛與自由的執(zhí)著追求與不同時期人物的特征與成長。在視覺與聽覺的雙重刺激下充分調(diào)動觀眾對影片敘事情節(jié)的回味體驗與思索,為影片畫上完滿的句號。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影片最后的十分鐘舞臺表演,影片中還有兩次不同空間人物的同框畫面。一次為蘇菲與斯凱通話不歡而散后,在不停的場景變幻中,通過鏡子的影像傳達形式將二者在同一畫面中表現(xiàn)出來。另一次是蘇菲生子后的洗禮儀式,母女二人在旅館屋頂?shù)男〗烫谩爸胤辍保ㄟ^母女二人生子的共同經(jīng)歷加深了二者之間的情感紐帶,并升華了女性形象中母性光輝的主題。兩次具有魔幻色彩的時空重疊,都實現(xiàn)了影片與觀眾的情感交流,最后梅麗爾·斯特里普的回歸,更加點燃了觀眾的激情,引領(lǐng)起前作的狂歡氣氛。
在空間與時間的合作關(guān)系之外,《媽媽咪呀2》相對于前作也更加豐富了空間的選擇與表現(xiàn),加強了空間在敘事線程中的帶動作用。除了旅館、船和島上街道的空間選擇,影片更加入了禮堂、校園、巴黎街景、工業(yè)化城市、機場等場景的描繪畫面,豐富了敘事的可讀性和觀眾的觀影體驗,也更加從歌舞電影向傳統(tǒng)意義的敘事電影靠近。
三、結(jié) 語
歐·帕克的《媽媽咪呀2》,更加飽滿地展現(xiàn)了歌舞劇電影的表現(xiàn)力和渲染力,影片對故事的書寫和主題元素的整合更加和諧工整,具有電影意識和電影感。影片在雙時間線程和空間轉(zhuǎn)向與重疊的敘事策略中推進劇情,完整敘述了親情的緊密聯(lián)結(jié)和超越時空的精神力量,在輕松幽默之余,呈現(xiàn)出慢生活基調(diào)和從未冷場的熱情狂歡。導演歐·帕克雖是男性,但始終沒有拋棄對原作中女性關(guān)懷的堅持,絲毫沒有偏離前作女性主義的色彩,在細節(jié)與情節(jié)的打造中堅持凸顯女性的主體地位,圍繞女性對愛與自由的追逐進行表達,并書寫著愛超越血緣與時空的奇跡。《媽媽咪呀2》成功地實現(xiàn)了對前作的超越,是一部成功的歌舞劇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