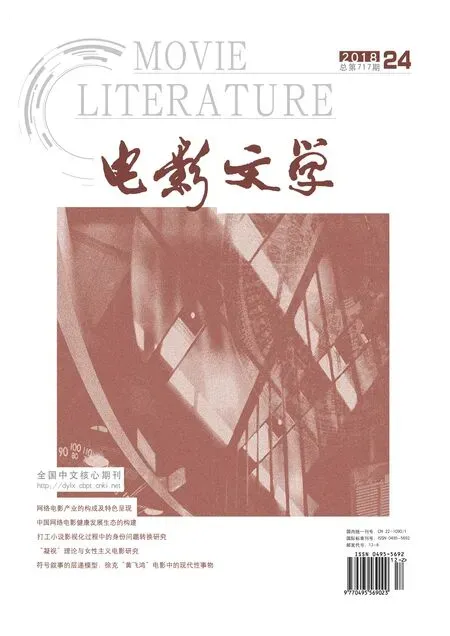《媽媽咪呀2》的人物創(chuàng)作解讀
邱金鳳
(鄭州工業(yè)應(yīng)用技術(shù)學(xué)院,河南 鄭州 451100)
在電影文本的敘事中,通常情況下敘事的完成都是依托于人物的行為活動和自我完成來實(shí)現(xiàn)的。也正是因?yàn)檫@樣,在電影文本的敘事過程中,都會通過多種手段對人物的進(jìn)行描寫,力圖將人物的情感經(jīng)歷、性格形成、命運(yùn)進(jìn)程作為電影的敘事核心,并且由此出發(fā),解決在電影敘事中人物的人生困惑,從而到達(dá)人物與他人和自我的和解。在音樂電影中,這種規(guī)律同樣適用,但是作為一種相對特殊的電影類型,雖然人物對于敘事的重要地位是相同的,在表達(dá)方式上,音樂電影在塑造人物上采用了一種不同于一般電影的手段,在這種近似于狂歡化的電影場景中,人物之間的情感關(guān)系與自我認(rèn)識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完成。這個電影場景也就是音樂電影文本中的歌舞場景。
歌舞場景在音樂電影中的構(gòu)建的特點(diǎn),接近于狂歡化,但是其中癲狂的成分相對較小,甚至接近于無,而其中歡樂的氣氛相比之下更加濃重。這是因?yàn)樵诟栉鑸鼍爸腥宋锏那楦嘘P(guān)系沒有因?yàn)楦栉鑸鼍暗某霈F(xiàn)而中斷,而且是進(jìn)一步在歌舞場景中被強(qiáng)調(diào)和延續(xù)。也就是說音樂電影中的歌舞場景是依托于人物關(guān)系的形成才出現(xiàn)的,是在一定的情感邏輯發(fā)展到高潮之后,通過這種歌舞手段暗示人物的心理狀態(tài),并且在這種外化的心理狀態(tài)的展示過程中,締結(jié)新的人物情感關(guān)系。在具體的歌舞場景中,又因?yàn)橐魳凤L(fēng)格、演唱的人物之間的和聲關(guān)系、對唱的復(fù)調(diào)關(guān)系形成了不同的人物形象。然而上述的這些多樣態(tài)的情感關(guān)系的締結(jié),都是在人物的自我認(rèn)證發(fā)展的過程中或是發(fā)展的結(jié)果,但是不論如何,歌舞場景的表現(xiàn)最終的走向都是指認(rèn)人物的自我和解和自我確認(rèn)。也就是說在音樂電影的敘事中,歌舞場景的參與者往往是電影敘事最終想要展現(xiàn)的對象,或者說,在歌舞場景當(dāng)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都在電影文本的敘事中充當(dāng)著敘事的重要對象。
一、歌舞場景的人物塑造
在《媽媽咪呀2》電影文本敘事當(dāng)中,由于是兩條時間線索并行前進(jìn),因此出場的人物相對較多,人物之間的情感關(guān)系也相對復(fù)雜。為了勾連起兩個時空環(huán)境下的人物關(guān)系,在電影的敘事中勢必要通過某種情感主線作為貫穿整個電影文本的中心環(huán)節(jié),而人物的關(guān)系則是這種情感關(guān)系的一種直觀體現(xiàn)。也就是說當(dāng)電影文本當(dāng)中試圖建立起一種情感關(guān)系時,必然要通過多樣態(tài)的人物關(guān)系來體現(xiàn)出這種敘事邏輯。在音樂電影的塑造中,多樣態(tài)的人物關(guān)系建立或者發(fā)現(xiàn)都是集中在歌舞場景中來表現(xiàn)。在獨(dú)立個體的人物塑造層面,歌舞場景首先表現(xiàn)的是人物的個體性格。例如在《媽媽咪呀2》影片剛開始的時候,蘇菲清唱,在這個歌舞場景中,舞蹈的元素相對較少,但是音樂整體風(fēng)格相對輕快,歌曲所唱的也無關(guān)于整體的敘事內(nèi)容,而是對音樂本身的贊嘆和肯定,在這個歌舞場景中蘇菲這一角色展現(xiàn)出了柔弱但是堅(jiān)強(qiáng)、對生活始終保持樂觀和積極的心態(tài)的最基礎(chǔ)的人物性格。
這個性格基礎(chǔ)的構(gòu)建是整個電影文本敘事過程中的風(fēng)格基礎(chǔ),也是核心人物之間交流的最大前提,這就是整個電影的敘事風(fēng)格和人物之間的情感聯(lián)系,都是相對輕松的。也就是說在電影的一開場,就確定了一種人物性格的基調(diào),就是人物的性格都比較單一而逐漸趨于單純和和善,彼此之間不存在著重大分歧和絕對難以調(diào)和的矛盾,而是通過相對平凡的生活問題和情感問題來凸顯出敘事層面的矛盾,從而達(dá)到敘事情節(jié)的展現(xiàn),試圖通過敘事的建構(gòu)解決人物的自我認(rèn)識問題。
比如在比爾、哈利和山姆向唐娜求愛時的三個不同歌舞場景,第一場是以比爾的獨(dú)唱為主,這場歌舞大量使用了整齊的舞蹈鏡頭,規(guī)模較大,氣氛也是在三個場景中最為熱烈和有感染力的。但是在這個場景中,女聲部分的合唱相對較少,雖然在舞蹈場景中有所出現(xiàn),但是不屬于共舞。也就是說,在這個歌舞場景中所暗示出來的人物關(guān)系,女性的情感表達(dá)處于相對被動的狀態(tài),不能主動呼應(yīng)來自男聲的呼喚,可以看到這段情感關(guān)系難以在兩人的關(guān)系中產(chǎn)生共鳴。在第二場哈利船上求愛的歌舞場景中,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女聲部分在對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歌舞屬于雙人舞,彼此的呼應(yīng)和交流更加豐富,很明顯地讓兩人的情感關(guān)系更加緊密,也更加可能產(chǎn)生更好的結(jié)局。在第三場的歌舞場景中,舞蹈的成分大大減少了,歌唱形式,也由對唱變成了女聲獨(dú)唱,不難發(fā)現(xiàn)女聲部分在這段感情中占據(jù)了更加主動的地位。相較于前面兩段歌舞場景,這段歌舞場景展現(xiàn)出來的情感關(guān)系更加明確,也更加符合唐娜的情感取向,也就是會選擇在小島這個空間內(nèi),支持唐娜決定的角色。在相對獨(dú)立的人物個體的個性前提下,這種情感關(guān)系的締結(jié)更加明確了文本在于敘事上的重點(diǎn)選擇上,也就是說,歌舞場景實(shí)際上是人物情感關(guān)系相對直觀和藝術(shù)化的表達(dá)。
二、歌舞場景于人物的自我發(fā)現(xiàn)
從上文的討論來看,在人物關(guān)系建構(gòu)層面,由這種單純的人物性格的建構(gòu)出來的人物之間的情感關(guān)系也是相對單純而且美好的,甚至在這種唯美主義傾向的道德世界建構(gòu)都會顯示出一種對于人物個體的美的表達(dá),這些人物的關(guān)系最重都會向同一種意識形態(tài)觀點(diǎn)趨于統(tǒng)一。這里提到的意識形態(tài)并不是指政治術(shù)語和哲學(xué)話語體系當(dāng)中的概念,而是向更加生活化、平凡化的概念滑動的一種生活訴求。在《媽媽咪呀2》這部電影當(dāng)中,最主要的意識形態(tài),或者說是人生選擇,都是來自唐娜,而女兒蘇菲對于旅館的堅(jiān)守,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來自對唐娜內(nèi)心精神的繼承和變體。而在電影文本的整體敘事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支持或者最終支持這個精神世界的選擇,而走向了主人公的周圍,這種對單一意識形態(tài)的認(rèn)同一定會迎來大團(tuán)圓的結(jié)局。這實(shí)際上是人物在敘事結(jié)構(gòu)中凸顯出來的敘事指向問題,每一個人物的最終指向都是向一個固定空間回歸,也就是都是由唐娜和蘇菲為代表的意識形態(tài)所建構(gòu)起來的。這種最終向單一方向妥協(xié)的人物情感關(guān)系最終迎來的就不再是對他人的接納和重新認(rèn)識,而是著重朝向?qū)ψ晕业睦斫獍l(fā)展的。因?yàn)橐磺型庠谝蛩囟紩詣颖幌猓娪拔谋揪蜁⑹陆裹c(diǎn)轉(zhuǎn)向?qū)?nèi)在自我的分析。這也就是歌舞場景在建構(gòu)人物個體時,最終產(chǎn)生的對于包括廣泛的人物情感關(guān)系在內(nèi)的自我確認(rèn)的人物刻畫核心。
在《媽媽咪呀2》的敘事中,兩位主人公唐娜和蘇菲都曾經(jīng)表達(dá)過自己的母親總是缺席于自己的成長過程中,而在兩人最終成為母親之后又都對自己的心理缺失產(chǎn)生最終的和解,當(dāng)然這種和解是在這兩個人物獲得母親這一社會身份之后。但是在電影文本的敘事中并沒有在人物成為母親之后直接敘述了人物心理的變化,而是通過外化人物心理的狀態(tài),形成了對人物自我發(fā)現(xiàn)與自我和解的最終目的。在電影敘事中的最后一場有關(guān)敘事的歌舞場景中,借由音樂蒙太奇的鏡頭手法,剛剛成為母親的唐娜在生下蘇菲所在的時空與蘇菲成為母親并且為了孩子受洗時的時空形成了連接,在同一首歌曲中由唐娜的獨(dú)唱開始,展示出了一位曾經(jīng)不受到母親照顧的女孩成為母親之后,對于母親這一社會身份責(zé)任的認(rèn)識,實(shí)際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原諒了自己的母親。而蘇菲對于唐娜的懷念也是她對自我身份的重新發(fā)現(xiàn)的障礙,而同樣在這個打破了時空關(guān)系的歌舞場景之中,蘇菲重新與母親在這種場景中達(dá)到了心靈的共振,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了蘇菲對自我獨(dú)立身份的認(rèn)知,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來自母親的情感束縛。在這個場景中達(dá)成了敘事對于主要人物的刻畫。實(shí)際上是影片通過歌舞場景完成文本敘事的一種表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