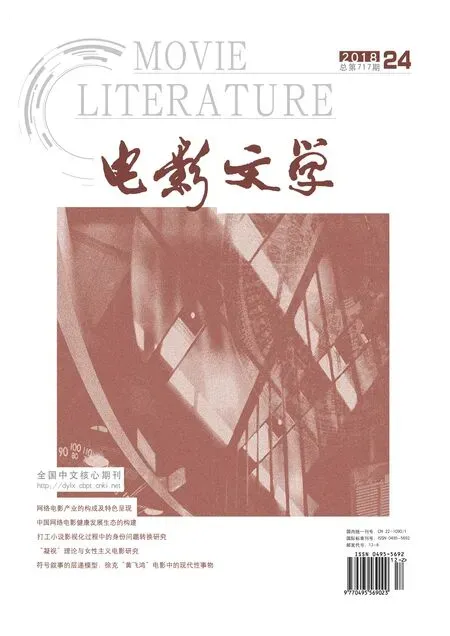電影《血觀音》中的女性身體觀照
戴小晴
(重慶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媒學院,重慶 401331)
電影《血觀音》片名英譯為The
Bold
,the
Corrupt
,and
the
Beautiful
(勇敢的、腐敗的和美麗的),十分契合電影主題。“觀音”是善念慈悲的,“血”則是肅殺兇殘的,兩者善惡相左。作為電影中的核心意象,“血觀音”象征著“披著優雅至善的外衣卻大行魔道的魔鬼”。電影以絕對女性視角展開,盡可能排斥男性角色的登場,展示著男權世界里的女性身體形態,可謂一部純粹的女性電影。身體理論自尼采以來,實現了“意識主體”向“身體主體”的轉變過渡。女權主義將其與社會地位與歷史語境結合,福柯則將其納入社會規訓的范疇,德勒茲吸收尼采的權力意志,創造性地提出無器官身體。而女性身體因為夾雜了欲念、性別、話語、歷史、權力等多向度元素,呈現出更為復雜的形態。
一、女性史詩——歷史語境中的女體神話
(一)女體神話
女性身體作為“他者”,被放置于歷史語境中。電影《血觀音》以女體神話般的視角,回應了男權世界的桎梏與脆弱。電影一方面強化了家族與權勢對身體的深層次壓抑和摧殘;另一方面展示了女性身體在家族與權勢斗爭中反抗他者形態,完成了女性主義和女性身體的覺醒。棠氏家族三位女性以不同的身體形態參與家族歷史,締造女體神話。
棠夫人以依附男權的方法,獲得了超越男權世界的可能。棠家明面上是做古董生意,實際卻是官商往來的掮客。彌陀計劃涉及主席選舉、農會融資、房產開發等系列事件,棠夫人在其中往來穿梭,幾乎將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間。棠夫人就是“血”與“觀音”的結合體,她苦心孤詣地經營著自己的慈悲形象,修性念佛;然而家族與權勢的爭奪又使她巧言令色,心如蛇蝎。棠夫人呈現出的冷靜果斷和殺氣,使得她身體和精神男性化,她的身上兼具了女性、母性與男性多重屬性:在女兒面前,她是女性和母性的化身;在政敵面前,她的身體傾向于男性化。當幕后推手馮秘書長出場,她的女性身份得以強化。然而此時電影出現了很值得玩味的一幕:馮秘書長用手壓住棠夫人的手,她掙脫手來反而壓住馮秘書長的手。她不甘心被男權控制,使得她仍舊要以壓制性別為斗爭點。
棠寧以縱欲與叛離家庭,獲得了超越性與家庭關系的可能。棠寧是一個悲劇性的角色,她渴望得到母親的認可,更渴望得到女兒棠真的愛。母親視她為工具,她用身體迎來送往;女兒背叛了她,在她準備逃離之時將她告發,也間接造成她的死亡。棠寧是覺醒的女性身體,她在生命的最后關頭,企圖恢復自己的母親身份,回歸被壓抑和埋沒的母性。“女人的悲劇,就是這兩者之間的沖突:總是作為本質確立自我的主體的基本要求與將她構成非本質的處境的要求。”主體意識與處境的沖突反映在棠寧身上,就是母性被壓抑,淪為家族棄子,被母親和女兒雙重拋棄。她縱欲、酗酒、吸食鴉片、歇斯底里,種種表現,從本質來說都是身體對于身份沖突的間接反映。
棠真以無愛無欲抗拒一切,獲得了超越情感與血緣的可能性。棠真看似純真無邪,實則卻是電影里最為復雜的女性形象,她的成長跨度最大。電影里她常被當成窺視者來推進故事,也借此塑造她性情的轉變:她窺視棠寧與家奴的性愛場面,體驗性啟蒙;窺視好友林翩翩與男友的偷情,萌發戀情。促使她性情陡變的情節包括:棠寧坦白她們是母女關系;好友林翩翩在她面前死去;一心暗戀的馬仔Marco強奸了她;等等。劇烈變故使她對家庭關系和愛情失去了信賴,淪為無愛的一具軀殼。她的義肢就是她的身體的象征,精美華麗然而毫無感情。
棠氏家族從政商“掮客”搖身一變成為富甲一方的豪商。棠家從事實上完成了家族事業的壯大,不用躲在權貴階層后面做“聽話人”,棠家獲得了權力。諷刺的是,棠家事業的輝煌卻是以棠家三代肉身的毀滅與沉淪為條件的,身體與權力出現了置換關系。在棠氏家族日益壯大的歷史語境中,她們的身體宣告了現實處境:棠夫人的身體毀壞枯萎,盛顏不再;棠真的身體,走向了殘疾與冷漠。
(二)男性缺席與男權在場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寫道,當女人開始參與規劃世界時,這個世界仍然是屬于男人的世界。“拒絕成為他者,拒絕與男人合謀,對女人來說,就等于放棄與高等階層聯合給她們帶來的一切好處。”電影中女性上演的“廝殺”與情仇,歸根結底都只是高層政治人物在政治斗爭中的犧牲品,仿佛暴風雨中的飛蛾。棠夫人與王院長夫人虛與委蛇、林夫人討好縣長夫人等情節,看似只是女性之間來往,其實是男性權力世界的一個變體。棠夫人提醒林議員把握機會親近王院長夫人,只是因為王院長是大選的熱門。棠夫人明面上與王院長等人同流合污,暗地里卻與另一位候選人結為同盟。
電影將女性投身于男權世界弱肉強食的規則之中,女性身體的羸弱與“殘缺”,更指向女性深層次的社會屬性,無論是欲望發泄還是成家立業,男權世界仍然籠罩著她們。棠家的發跡史,源自“老將軍”的根基。棠家墻壁上的老將軍照片,即為一個男性身體的缺席和權力的在場。在電影里,女人都是男性權力的附著物,女人無法拒絕成為他者,甚至她們必須牢牢依附于男權,來穩固自己的利益。棠夫人也不例外,與男性合謀才能為自己和棠氏家族攫取最大的利益。
二、權力機制——規訓與反抗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解析權力與身體關系圖譜,他指出權力對肉身的懲罰(酷刑)逐漸向權力對于身體的規訓(監視)過渡。規訓意味著人體正在進入一種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編排它的權力機制。規訓“要建立一種關系,要通過這種機制本身來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或者因更順從變得更有用”。
在《血觀音》里,權力與身體的對峙,既表現為對于肉身的刑罰,也表現為對于身體的控制與規訓。林議員一家五口被殺人滅門,手段極為殘忍,林翩翩則是“給人捆綁斷手腳”;棠家的御用殺手還有營建署小官被拋尸荒野;棠寧逃離出海,船只爆炸;等等。棠家以及其他權勢家族都依靠著對肉身的毀滅來確定其權力,恢復對于失控事件的主宰。這種顯在的懲罰機制,加重了本片血腥黑暗的影像風格。
相比起肉身的懲罰,《血觀音》里更多呈現的是對于身體的規訓。身體不再遭受殘忍的刑罰,卻依然難以擺脫控制。家庭比起工廠、學校、監獄等監視設施,具有更為隱秘的控制機制。血緣關系和家族利益驅使家庭成員遵從符合家族利益的行為規范。棠夫人操控棠寧放縱性欲,將她與男人的關系徹底異化成交易——棠寧與棠家殺手的性愛、與廖隊長調情等,都是出于對家族利益的維護。棠夫人甚至剝奪了她做母親的機會,在她身上呈現著身份糾纏與身體符號錯位。棠夫人說她“公主命,丫鬟身”。電影前半段里,棠寧的身體是半失控的狀態,她縱欲、酗酒、嗑藥,甚至她在棠夫人面前乞求、撒潑,依舊得不到真正的關懷。電影后半段,在她母性復歸的時刻,得不到女兒的承認,她選擇放她自由。
棠真則是一個雙重規訓的身體存在,她既是被規訓者同時也是規訓者:一方面她處于棠夫人的關愛和規訓之中,另一方面她以保護Marco的名義囚禁著他,想將他據為己有。棠夫人教會她迎客之道,教她學會察言觀色,其實是一種漸進的身體規訓,意在將她的身體納入家族利益關系網中。棠夫人教她作畫時,鬼魅的音樂襯托了這一場景,作畫其本質是棠夫人在教她“殺人”——權謀之術的最高境界,即是殺人于無形之中。而看似幼稚的棠真,在醫院照顧林翩翩,眼睜睜看著好友慢慢死去,她冷靜異常。電影用了紅蘋果作為罪惡的意象,將棠真急劇變化的內心標志出來,觀眾見證她的罪惡的誕生,她的身體淪為家族利益的無意識的傀儡。
在福柯看來,身體與靈魂一樣都是社會建構起來,社會家庭徹底改變了肉體,甚至塑造它的“生理功能”。然而福柯也認為,哪里有權力,哪里就有阻力。“我所謂的反抗不是一種實體。它與權力是共生的,同時存在的……”只要存在著權力關系,就會存在反抗的可能性。棠寧與棠夫人的決裂就是權力關系崩塌的結果,一開始棠寧通過酗酒、縱欲等形式來反抗棠夫人對她的異化,但并沒有成功。她明白母親將她出賣后,她選擇“叛離”家庭,以肉體毀滅瓦解了家庭施加在她身上的權力枷鎖。相較而言,棠真的反抗顯得隱忍克制,不動聲色。她在獲得對棠夫人的生殺大權之時,執意讓她承受病痛的折磨,讓她活在無愛的未來里。無論棠寧的縱欲,還是棠真的權力取代,都沒有獲取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棠寧的放縱只會加劇身體的異化,棠真雖然重新書寫了權力關系,依然逃不出權力的規訓機制。
三、欲望機器與無器官身體
(一)欲望機器:驅動力
《血觀音》是一部涌動著欲望的電影。欲望存在于身體與身體的相互貫連中,在德勒茲看來,身體是去機體化的,涌動著多樣化的景色的,身體是一臺反俄狄浦斯的欲望機器,無時無刻不處在生成的運動狀態中。
在本能驅使之下,電影《血觀音》里面的人物幾乎都是扭曲的,如同棠寧完成的那幅家族肖像畫——詭異之間帶著一絲邪氣。《血觀音》的空間具有兩重屬性,首先它是一個物欲橫流、利欲熏心的名利場,在這個特定空間中,權貴階層躲在繁文縟節和文明外衣里,遵循著原始的沖動本能追逐聲色名利;其次它也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家庭場域,棠家三位女性,遵循著個體欲望之流,詮釋著不同的身體形態。棠夫人同時身處兩個空間場域之中,在名利場里,她的身上既有原始的征服欲念,也有爭取家族利益的外在驅動力;而在家庭場域里,她的母性的本能欲望與家族利益產生沖突。棠夫人壓抑自己的母性本能,追隨了原始的征服的欲望,實現家族利益的最大化。
棠寧則臣服于母親至高權力之下,被剝奪了自我,她的欲望源于母親的肯定和自身母性的復歸。一方面她作為欲望機器的身體,取之不盡地為棠家生產和創造著價值。母親的認可即棠寧作為欲望機器的內驅力,驅使她游移在與其他欲望軀體的連接之間。另一方面,她的母性的內在渴望,使得她本能地破壞棠夫人為她設置的身份角色,進而引發家庭關系的土崩瓦解。
(二)無器官身體:兩種形態
在德勒茲看來,“無器官身體”并不是一個“沒有器官的身體”, 而是“一個擺脫了它的社會關連、它的受規誡的、符號化的以及主體化的狀態,從而成為與社會不關聯的、解離開的、解轄域化了的軀體”。無器官身體意指剝離具體的身體實質,身體被抽象成某個意義上的生產性力量和欲望。無器官身體大體細化為兩種形態:充實的與空虛的。
電影中運籌帷幄、步步為營的棠夫人以及“涅槃”過后的棠真,展現的則是充實的無器官身體。在她們那里所生產的相互作用的各種力量、欲望,充裕了她們的物質與權力世界,構成了她們所在的名利場,也成為顯在的社會精神的投射。空虛的無器官身體,如癮君子、受虐狂等。從這個維度來說,對酒精、毒品、藥物依賴的棠寧,常表現出癮君子般譫妄的迷狂狀態,可謂空虛的無器官身體的一種表象。棠寧對身體的毀滅式的否定,用極端的病態的身體使用方式,展示著空虛的無器官身體的內在可能性。
四、結 語
電影《血觀音》借由女性視角來構建故事,影像色彩艷麗濃烈,運用說書人結構,營造詭譎奇異的氛圍等,可謂近年華語電影難得的佳作。女性身體只是電影展示的一個顯性的維度,但無疑是其最具話題的一個維度。電影將女性身體與女性地位、權力機制等話題并置,沒有刻意消費肉體和追求感官刺激,明智地回避了女性電影的肉欲怪圈。電影與社會現實精神的內在融洽,尤其是女性身體在男權世界的扭曲呈現,也正說明了類似的故事遠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