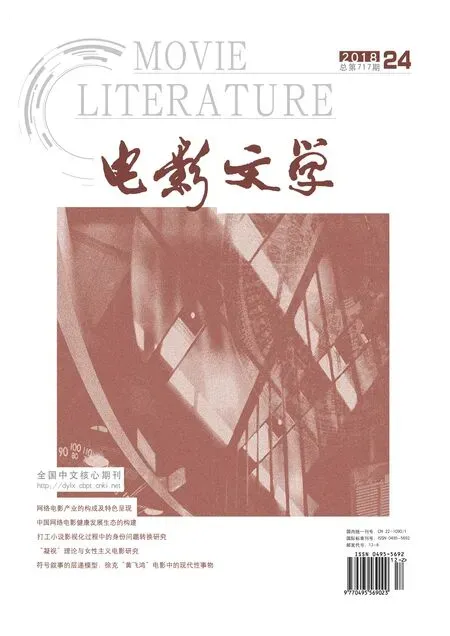現(xiàn)實(shí)主義視域下的《江湖兒女》
王 麗
(河西學(xué)院 信息技術(shù)與傳媒學(xué)院,甘肅 張掖 734000)
談起“江湖”對(duì)今天的中國(guó)電影觀眾而言,最熟悉的莫過(guò)于武俠片或者香港黑幫片。作為我國(guó)最成熟的類型電影,武俠電影所呈現(xiàn)出來(lái)的江湖故事與現(xiàn)實(shí)生活之遠(yuǎn)不言而喻。香港黑幫片雖然是現(xiàn)代社會(huì)背景下發(fā)生的江湖故事,但傳奇性是其基本的色彩。賈樟柯卻在現(xiàn)實(shí)主義視域下給觀眾呈現(xiàn)了一個(gè)“陌生化”的江湖故事,不同于《臥虎藏龍》,亦不同于《喋血雙雄》。20世紀(jì)70年代出生的賈樟柯將自己成長(zhǎng)過(guò)程中的生命體驗(yàn)深刻地融入作品之中,用自己的方式呈現(xiàn)了一個(gè)更貼近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江湖”故事,它超出了電影觀眾對(duì)“江湖故事”的觀影經(jīng)驗(yàn),卻難能可貴地挑起了他們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照和個(gè)體命運(yùn)與時(shí)代變革的關(guān)系的思考。
一、“真實(shí)”江湖映襯大時(shí)代變遷
在談到對(duì)江湖的理解時(shí),賈樟柯說(shuō)“江湖應(yīng)該有激蕩變動(dòng)的社會(huì)背景,比如胡金銓和張徹導(dǎo)演的電影,比如吳宇森電影里20世紀(jì)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江湖故事總是把時(shí)間設(shè)置在激烈變革的動(dòng)蕩時(shí)代。另一方面,江湖也意味著危機(jī)四伏的生存環(huán)境以及復(fù)雜的人際關(guān)系。除了以上這些,如今大多數(shù)人離開(kāi)家鄉(xiāng)去外地闖江湖,尋找一個(gè)適合自己生存的地方,這種四海為家的漂泊感受,是在每個(gè)人心里的”。比起熱血的街頭江湖故事,導(dǎo)演更想呈現(xiàn)的是時(shí)代變革浪潮之下的世俗生活和更真實(shí)、更日常的“江湖”。
影片開(kāi)場(chǎng)于2001年,而背景則可以推到20世紀(jì)最后十年國(guó)有企業(yè)改革的大形勢(shì),這正是導(dǎo)演所說(shuō)的“激蕩變革”的時(shí)代:中國(guó)改革處于攻堅(jiān)克難的轉(zhuǎn)型階段,宏安礦的改革也在艱難進(jìn)行:形勢(shì)不好、開(kāi)工不足、礦務(wù)局謠傳要搬走,礦長(zhǎng)劉金明還把礦區(qū)食堂承包給自己的小舅子,民怨沸騰卻又無(wú)可奈何。故事主人公斌哥和巧巧就是這宏安礦的職工。基于現(xiàn)實(shí)的無(wú)路可走,斌哥成為有黑幫色彩的街頭組織的頭目,他講義氣、有原則,拿人錢(qián)財(cái)幫人鏟事。傳統(tǒng)能源行業(yè)的衰落無(wú)可挽回,而代表改革潮流的地產(chǎn)正野蠻生長(zhǎng),所以開(kāi)發(fā)別墅的二勇被人捅死在停車場(chǎng)卻始終找不到兇手,時(shí)代劇烈變革下的利益角逐就這樣被導(dǎo)演用一個(gè)舉重若輕細(xì)節(jié)充分表達(dá)了出來(lái)。這個(gè)結(jié)果也同時(shí)昭示了斌哥的江湖在即將到來(lái)的新時(shí)期里無(wú)路可循。斌哥也曾計(jì)劃積極地參與到新時(shí)代變革中,在同巧巧去郊外火山附近時(shí)說(shuō)要在即將到來(lái)的大同市的拆遷改造運(yùn)動(dòng)中大顯身手。可他們的命運(yùn),卻在那聲槍響之后徹底翻轉(zhuǎn)。出獄后的斌哥出走奉節(jié),以期東山再起。巧巧千里尋人,恰遇三峽工程的移民將啟程前往遙遠(yuǎn)的廣東,對(duì)故土的眷戀與不舍寫(xiě)在每個(gè)移民的臉上,他們卻是靜靜地等待最后時(shí)刻的到來(lái)。導(dǎo)演敏銳地發(fā)現(xiàn)時(shí)代的變革風(fēng)起云涌,人們身處其中卻不自知。
17年時(shí)間流逝,未能東山再起的斌哥落魄回歸,迷失于日漸繁華的大同市,幸得巧巧收留才有棲身之所。曾經(jīng)的江湖早已崩塌,唯有時(shí)間一直向前,唯有時(shí)代不斷變化。
二、復(fù)雜人性的多維度呈現(xiàn)
通常賈樟柯電影作品中較少使用科班出身的演員,除去現(xiàn)實(shí)主義風(fēng)格的追求之外,更是因?yàn)殡娪敖巧粚?dǎo)演定位為為其敘事意圖進(jìn)行表達(dá)的符號(hào),對(duì)演員塑造人物的要求不高非專業(yè)演員身上特殊的鏡頭感正是他追求的。但這一情況在《江湖兒女》有所改變:女主角巧巧是一個(gè)除去表達(dá)導(dǎo)演意圖之外也能留給演員巨大表演空間的角色,扮演者仍然是賈樟柯御用女主角趙濤,男主角斌哥則起用了影帝廖凡這個(gè)演技極高的專業(yè)演員。廖凡的確不負(fù)眾望,將斌哥這一形象塑造得入木三分。導(dǎo)演對(duì)這一對(duì)江湖男女各自寄予了不同的情感期望。
(一)巧巧:尋找與堅(jiān)守的情義女性
賈樟柯說(shuō):《江湖兒女》就是寫(xiě)給中國(guó)女性的情書(shū)。巧巧這個(gè)角色的確是一個(gè)了不起的女性。
影片的英文名Ash
is
Purest
White
可以譯為灰塵是最純凈的白色,亦如巧巧在影片中所言:灰是最干凈的。巧巧就是這個(gè)影片中最干凈、最純粹的女性。這個(gè)角色在情節(jié)演進(jìn)中不斷成長(zhǎng),17年時(shí)間里三個(gè)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上的角色趙濤非常有層次感地表現(xiàn)了出來(lái):開(kāi)場(chǎng)她以“斌哥的女人”的身份在《男兒當(dāng)自強(qiáng)》的音樂(lè)中入畫(huà),這一身份標(biāo)簽使她可以得到斌哥的馬仔或者出租車司機(jī)的尊重與巴結(jié),敢打麻將館里那些跟她開(kāi)玩笑的男人。“黑社會(huì)大哥”的女人的身份并沒(méi)有令她迷失自我,更不曾得意忘形,她想要的不過(guò)是江湖之外安穩(wěn)的生活,她是一個(gè)傳統(tǒng)的青春女孩。在斌哥生死攸關(guān)的時(shí)刻,她義無(wú)反顧地扣響了手中的槍,并擔(dān)下了所有罪名。獄中,她隱忍堅(jiān)強(qiáng),坦然接受了法律的懲罰。出獄后千里尋情,她執(zhí)著勇敢,不卑不亢。遭遇了拒絕與背叛,她決絕離去,卻也沒(méi)有隨波追流。徐崢扮演的克拉瑪依小賣部店主對(duì)巧巧這個(gè)角色的塑造至關(guān)重要。了卻與斌哥的情緣之后,巧巧一度迷茫,也不知道自己該去向何方,火車上偶遇新疆小販被說(shuō)動(dòng),一同前往克拉瑪依。火車狹窄空間里的曖昧擁抱被不合時(shí)宜響起的電話鈴聲打斷,當(dāng)然,打斷他們的不只是電話鈴聲,更是巧巧自我堅(jiān)守的力量。所以她選擇了中途下車,并在深夜的陌生的車站看見(jiàn)了UFO。賈樟柯說(shuō)“巧巧下了火車之后,這是全片電影主人公唯一不處在人際關(guān)系中的時(shí)刻,也是她最孤獨(dú)、最絕望的時(shí)刻。寫(xiě)到這兒的時(shí)候,我覺(jué)得或許應(yīng)該讓她看到一個(gè)生命的奇跡,一個(gè)我們常人看不到的一個(gè)奇跡,就突然寫(xiě)出了看到UFO這一幕”。這暗喻她會(huì)擁有可期的未來(lái)。時(shí)間直接來(lái)到2018年元旦,巧巧在大同擁有了自己的麻將館,其間艱辛毋庸多言,可她活出了自己,無(wú)須依附于誰(shuí),也不依附于誰(shuí)。巧巧是一個(gè)對(duì)時(shí)代變革敏感的人,順應(yīng)了社會(huì)改革的新趨勢(shì)。她也同樣堅(jiān)守著自己認(rèn)可的人情世道,所以她會(huì)收留已經(jīng)沒(méi)有愛(ài)恨之情的斌哥。所以,她才是影片中最有江湖情義的人。
(二)斌哥:拋棄與背叛的世俗男性
郭斌這個(gè)角色,導(dǎo)演選擇廖凡來(lái)演可以說(shuō)是極其成功的。開(kāi)場(chǎng)宏安礦機(jī)車廠職工出身的他在變革的時(shí)代洪流中成長(zhǎng)為黑社會(huì)大哥,談笑間了卻江湖事,可謂意氣風(fēng)發(fā)。斌哥試圖在規(guī)則之外建立秩序,也一度成功。這個(gè)脆弱的秩序在街頭械斗中巧巧救人的槍聲里轟然瓦解、灰飛煙滅。出獄后的斌哥,無(wú)法接受曾經(jīng)的小弟一個(gè)個(gè)搖身一變成為成功人士,而他自己在大同卻無(wú)立足之地,無(wú)奈出走奉節(jié)去投靠他曾經(jīng)幫助過(guò)的“大學(xué)生”林家棟,這場(chǎng)出走更像出逃。他拋棄了上一個(gè)時(shí)代里曾經(jīng)信仰的江湖義氣,背叛了和巧巧曾經(jīng)的愛(ài)情。在奉節(jié),他被迫與巧巧重逢在破舊的小旅館里,連說(shuō)分手的勇氣都沒(méi)有,說(shuō)自己“已經(jīng)不是江湖上的人了”。期望東山再起的他,數(shù)年后歸來(lái)并未功成名就,而是腦出血癱瘓了,暫居在巧巧的麻將館里,被昔日的小弟羞辱,這個(gè)曾經(jīng)的江湖大哥如今徹底被時(shí)代拋棄了。斌哥的人生從開(kāi)場(chǎng)就在不斷下行,他的悲劇在于對(duì)自己曾經(jīng)高高在上的江湖大哥的身份定位與出獄后遭受冷遇的巨大反差。屬于他的時(shí)代漸行漸遠(yuǎn),癱瘓實(shí)際在暗喻他被囚禁的靈魂不被認(rèn)同,也無(wú)法自我認(rèn)同。倒是最后的離去,讓人心生幾分敬意。
三、隱喻豐富的視聽(tīng)意象
賈樟柯導(dǎo)演電影的視聽(tīng)語(yǔ)言獨(dú)具特色:現(xiàn)實(shí)色彩濃厚。《江湖兒女》秉承了他一貫的風(fēng)格。看似無(wú)須精心設(shè)計(jì)的鏡頭畫(huà)面恰是真實(shí)的生活面貌,它活生生地存在于那個(gè)時(shí)代。變革中的礦區(qū)蕭條衰敗、滿目瘡痍,暗喻了那個(gè)時(shí)代經(jīng)歷改革陣痛普通人的真實(shí)狀態(tài),“江湖之地”KTV霓虹繽紛、電子閃爍感造就的現(xiàn)代性亦無(wú)法遮蔽。影片總體視像風(fēng)格呈現(xiàn)出灰暗的底色,壓抑、內(nèi)斂,包含著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觀照與思考。
(一)視像呈現(xiàn)價(jià)值觀沖突
“好的故事來(lái)源于深刻的價(jià)值觀沖突,如果電影創(chuàng)作者不能正確地理解這一基本元素,那么他所有的電影創(chuàng)作嘗試就只能成為一系列毫無(wú)感染力的聲畫(huà)排列。”影片中沖突強(qiáng)烈的段落有幾個(gè):第一個(gè)是KTV里和葬禮上跳國(guó)標(biāo)舞的段落。KTV里氣氛癲狂躁動(dòng)顯然與國(guó)標(biāo)舞格格不入;而二勇葬禮上跳國(guó)標(biāo)舞更是不符合傳統(tǒng)的吊喪習(xí)俗。用這種不符合傳統(tǒng)習(xí)俗但卻尊重了死者喜好的方式進(jìn)行吊唁自然是導(dǎo)演有意為之,那是對(duì)劇烈的社會(huì)變革中無(wú)所不在的價(jià)值觀沖突的呈現(xiàn)。
導(dǎo)演毫不避諱作為“江湖中人”的斌哥和兄弟們對(duì)香港黑幫片的意淫與模仿,大家高喊“五湖四海皆兄弟,肝膽相照”,荒誕嚴(yán)肅的氛圍中集體收看《喋血雙雄》,似要學(xué)習(xí)港片中義薄云天的江湖情義,背景墻上卻是隱蔽了“兄弟齊心”只剩“其利斷金”的大字。這昭示了導(dǎo)演無(wú)意復(fù)制港片中的江湖情義,所以才會(huì)有斌哥入獄后兄弟們各自趨利而去,這個(gè)“江湖”市井、煙火氣,更有底層烙印。
影片中第三個(gè)能呈現(xiàn)價(jià)值觀沖突的畫(huà)面是二勇家刑警隊(duì)萬(wàn)隊(duì)長(zhǎng)和斌哥同坐在沙發(fā)上討論案件。萬(wàn)隊(duì)長(zhǎng)代表的是主流的秩序社會(huì),而斌哥則代表了主流之外的“江湖”秩序,他們的并坐隱喻了兩種原本強(qiáng)烈沖突的秩序在那個(gè)時(shí)代的并存。
(二)敘事空間多重轉(zhuǎn)換
羅蘭·巴特認(rèn)為“空間敘事”所涉及的空間主要有三類,即故事空間、形式空間和心理空間。故事空間是電影故事發(fā)生的場(chǎng)所或地點(diǎn);形式空間是為了實(shí)現(xiàn)作品整體的結(jié)構(gòu)空間(與繪圖中的構(gòu)圖類似);心理空間是在創(chuàng)作一部敘事作品時(shí),其心理活動(dòng)(如記憶、想想等)所呈現(xiàn)出來(lái)的空間。大同市里霓虹閃爍的KTV、奉節(jié)縣里狹促的小旅館以及數(shù)年后巧姐經(jīng)營(yíng)的小小麻將館都是電影情節(jié)進(jìn)展中可見(jiàn)的故事空間。這每一個(gè)故事空間的選擇都極具代表性,而導(dǎo)演尤其重視影片結(jié)構(gòu)空間的敘事功能。巧巧入畫(huà)是在一個(gè)從外部進(jìn)入小劇場(chǎng)的跟拍鏡頭,劇場(chǎng)舞臺(tái)上屬于底層人的娛樂(lè)項(xiàng)目口叼自行車正在上演,然后巧巧繼續(xù)走入麻將室,繞過(guò)一桌一桌打著麻將的男人最終坐到斌哥旁邊。這個(gè)煙霧繚繞的空間與后來(lái)巧巧自己經(jīng)營(yíng)的麻將館形成照應(yīng),展現(xiàn)了時(shí)代洪流中的“變”與“不變”。影片采用了回到過(guò)去的視角,利用這些現(xiàn)實(shí)中常見(jiàn)的生活空間,將一個(gè)戲劇性很強(qiáng)的故事保持了本真的色彩,也保證了觀眾更多的自我投射,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影片的心理空間。
(三)作為江湖與反江湖符號(hào)的“槍”
講江湖故事自然是離不開(kāi)槍的,熟悉香港黑幫片的觀眾必然會(huì)對(duì)其中的槍?xiě)?zhàn)情節(jié)印象深刻。但《江湖兒女》中這把槍并不似一般黑幫片中單純作為道具出現(xiàn),它更是一種符號(hào)和象征。槍第一次出現(xiàn)是故事開(kāi)篇,麻將館里老賈要賴掉向老孫借的債,掏出搶來(lái)讓老孫打死自己。而斌哥讓跟班李宣請(qǐng)關(guān)老爺出來(lái),老賈乖乖承認(rèn)了債務(wù)。槍沒(méi)了江湖事,在巧巧看來(lái)它更像是個(gè)麻煩,會(huì)讓壞人找上斌哥,斌哥則覺(jué)得有槍更像江湖上的人。街頭械斗的重場(chǎng)戲,混混們使用的武器大都是鋼管和鐵鍬。反倒是自認(rèn)為不是江湖上的人的巧巧鳴槍救人,這聲槍響瓦解了斌哥的江湖秩序,也改寫(xiě)了主人公們的命運(yùn)。“槍”在此刻成為赤裸裸反諷江湖的符號(hào),而這種反諷恰恰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照進(jìn)。影片的后半段巧巧出獄千里尋人被拒,數(shù)年后斌哥癱瘓回歸,巧巧憑一個(gè)“義”字收留他,這段無(wú)槍的故事才是導(dǎo)演要重點(diǎn)表現(xiàn)的時(shí)間長(zhǎng)河里和復(fù)雜人際關(guān)系中的江湖。這是一個(gè)有槍的江湖故事,卻也是一個(gè)無(wú)槍的江湖故事。
“想用電影去關(guān)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作為一部現(xiàn)實(shí)主義風(fēng)格的電影,卻不帶有慣常的批判眼光,導(dǎo)演用深情、悲憫的情懷呈現(xiàn)著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興衰變遷,展示著我們這個(gè)國(guó)家被忽視的人群和被遮蔽的現(xiàn)實(shí)。也許這群人和這個(gè)現(xiàn)實(shí)都不完美,卻不應(yīng)該被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