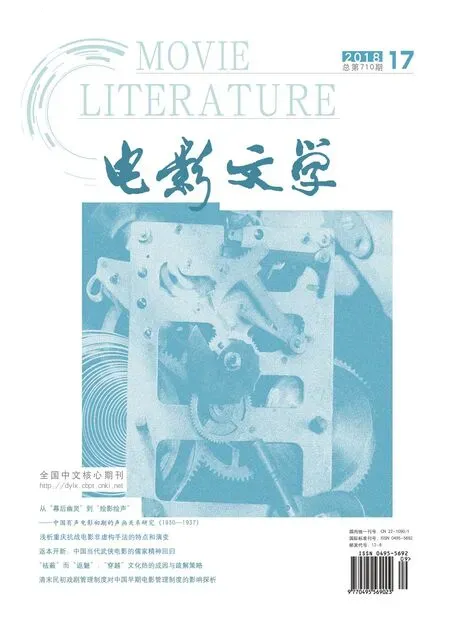淺析重慶抗戰電影非虛構手法的特點和演變
鄔建中 林澤夫
(四川外國語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重慶 400000)
一、導 論
現實主義美學是貫穿中國電影從始至終的一條主心骨,早在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運動之前,中國電影就迎來了第一個輝煌時期——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現實主義創作,蔡楚生、費穆等第二代導演使電影藝術真正深入人心,開創非虛構手法,并融入自覺的文化批判意識。這一奠基使得之后的“十七年”電影和第五代導演的集體創作都與非虛構主義美學手法緊密相連,而重慶地域電影起步較晚,非虛構手法可以說已經成為了重慶地域電影發展的限制框架,在此大框架中,重慶地域電影依靠地域特色,形成了獨具美學風格的非虛構手法。中國部分現實主義電影呈現出兩極分化的趨向:一部分導演堅持現實主義理想,但其中一些導演雖然力求冷靜讓攝像機說話,可還是流露出些許作家電影的傾向,附帶有精英、小眾文化的情緒。而早期的重慶抗戰故事片導演卻兼二者有之,催生了奇妙的現實主義下的家國情懷。
二、概念界定
(一)重慶抗戰電影
重慶抗戰電影是指1938年中國電影制片廠、中央電影攝制廠等電影文化機構隨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后,任用何非光、史東山、田漢等編導在重慶本土攝制的一批抗戰影片,目的在于樹立大后方抗日文化戰線,宣揚抗日民族思想。截至1945年日本軍國主義正式投降,完成拍攝的重慶抗戰電影共計200余部,其中抗戰新聞紀錄片占據絕大部分,故事片達到17部,代表作有《東亞之光》《保家鄉》《血濺櫻花》和《勝利進行曲》等影片。無論是在新聞紀錄片方向還是在故事片方向,重慶抗戰電影都呈現出一致的非虛構手法,以反映社會現狀為出發點、以描繪實景為原則、以激發國人熱血為己任,運用超前而又樸實的視聽語言完整地為大后方平民百姓展現了戰場之冷酷、日寇之兇殘以及英雄之偉岸。
(二)非虛構手法
非虛構手法英文名為documentary style,即“一種紀錄片的風格”,最早起源于美國電影藝術家弗拉哈迪在1922年拍攝的《北方的納努克》,弗拉哈迪以一種扮演的方式重現了原始文化的種種情境,被克拉考爾稱為“簡略的敘事”。而這種“簡略的敘事”經過蘇聯“電影眼睛派”維爾托夫一系列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正式形成一種專門應用于紀錄片拍攝的美學手法和原則。在當今的電影研究中,非虛構手法更多的是對故事片中紀錄性手法的一種統稱,20世紀40年代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運動將故事片中的非虛構手法推向頂峰和流行。因此,非虛構手法可以初步用巴贊對新現實主義總結的六個特點來表述:一個規定的社會文本;體現歷史的真實和轉瞬即逝性;政治、社會的發展變化;實景拍攝;對好萊塢表演方式的拒絕,盡可能地啟用非專業演員;非虛構性攝影。
(三)現實主義戰爭題材
現實主義戰爭題材專指不同國家、不同政治立場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爭事件進行現實主義創作的電影題材分類。在時間上,現實主義戰爭題材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戰爭進行時拍攝的,充滿政治當局傾向性,例如本文所研究的重慶抗戰電影;第二類是戰爭結束后甚至現代進行拍攝的,弱化政治性而突出反戰的母題,例如新好萊塢時期興起的《全金屬外殼》《現代啟示錄》等反戰影片。在主題上,現實主義戰爭題材影片的主題永遠以反思性和嚴肅性為大綱,而其視聽追求永遠以非虛構性和還原度為目標,通過對戰爭殘酷性的逼真描繪,來反對戰爭、反對侵略者。因此,非虛構手法便成為現實主義戰爭題材不得不采用的創作手法,從故事情節、人物塑造、美術設計、攝影技巧等各方面都展現出濃厚的非虛構美學。
三、文獻綜述
截至2018年5月1日,筆者在中國知網(CNKI)搜索到關于研究重慶抗戰電影的學術論文總計18篇,其中碩博士論文3篇,期刊論文15篇;關于研究電影非虛構手法或風格的學術論文總計14篇,其中碩博士論文2篇,期刊論文12篇;關于研究現實主義戰爭題材的學術論文總計18篇,其中碩博士論文5篇,期刊論文13篇。而在研究主題方面,與本文一樣以重慶抗戰電影的非虛構手法為研究側重點的論文有7篇,這些文獻在重慶抗戰電影的起源和發展、重慶抗戰電影的非虛構手法等方面有兩類不同的看法。首先對于重慶抗戰電影的起源,第一類觀點認為國民黨南遷、中國電影制片廠和中央電影攝制廠的支持以及反戰情緒的高漲是重慶抗戰電影發展過程中不可忽略的背景條件,例如南開大學羅顯勇副教授發表的《論重慶抗戰電影“紀實主義美學”的成因和特點》一文中,明確提出:“中國電影制片廠和中央電影攝制場吸收了大量在上海的電影從業人員,把他們轉移到陪都重慶,從而在重慶形成新的電影基地。”第二類觀點認為,國共的兩次全方位合作和抗日戰爭所導致的受眾變化是重慶抗戰電影萌發和發展的土壤,例如貴州大學汪太偉老師發表的《重慶抗戰時期的電影藝術》一文中,明確提出:“抗戰時期重慶電影業的從業人員已經認識到受眾所發生的變化,即由都市的知識分子、市民轉變為鄉鎮的農民以及各戰區的士兵。”其次,在對于重慶抗戰電影紀實手法的研究方面,第一類觀點認為重慶抗戰電影的紀實手法是以前期新聞紀錄片的非虛構手法為基礎的,經過開拓性的演變應用在故事片中,偏向于紀錄片的紀實片風格,例如重慶師范大學周晶老師發表的《消解與重建——重慶抗戰電影的影像精神》一文中,明確指出:“在中國電影發展歷史中,重慶抗戰電影非崇高、重意象的鏡像風格的呈現,是抗戰時期大后方電影創作的一大特征。”第二類觀點認為重慶抗戰電影的非虛構手法是相對脫離于新聞紀錄片而存在的,是一種更偏向于故事片銀幕夢幻的故事片風格,例如重慶師范大學李悅所發表的《抗戰時期重慶電影文學敘事研究》碩士論文中,明確指出:“此時期電影文學多以場景作為基本敘述單元并加以蒙太奇式的敘述連接,從而使得劇作結構呈現出電影化的影像特征。”在這兩方面問題的分歧上,本文對第一類觀點表示認同,對第二類觀點持保留意見。
縱觀關于研究重慶抗戰電影的18篇文獻,更多的是研究論述重慶抗戰電影的歷史背景、發展狀況以及非虛構手法的分析,而將紀實手法的演變與之后重慶地域電影的發展結合為一個整體進行系統研究的論文只有2篇。但是在之后的80年間,中國和中國電影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重慶也歷經解放和直轄,重慶地域電影也在曲折中緩慢發展,而起初重慶抗戰電影中的非虛構手法成為重慶地域電影永恒的美學根基,也產生了許多演變或者遺失,在當今大好的市場環境下,此問題是急需探討和研究的。因此,重慶抗戰電影非虛構手法的特點和演變對于近當代重慶地域發展的影響,是此大類研究問題中的研究空白,這也是本文進行研究的一個重點和現實意義所在。
四、重慶抗戰電影非虛構手法的萌發
(一)抗戰紀錄電影開疆擴土
在1937年之前,重慶的地域電影幾乎處于空白期,整個電影行業為數不多的電影人才、資源等都聚集在上海,但是在日軍侵華期間,隨著上海局勢越發緊張,尤其是1937年的“八一三”戰事爆發,上海的電影業遭受重創和威脅,田漢、夏衍等愛國藝術家奮起反抗,帶隊支援大后方的抗戰電影拍攝。而另外,中國電影制片廠和中央電影攝制場(以下簡稱中電廠和央電場)帶著大量的電影拍攝物資、經驗轉移到陪都重慶,如此,重慶抗戰電影的勃興條件充分。
重慶抗戰電影的揚帆啟航離不開抗戰新聞紀錄電影的過渡和實踐準備,重慶抗戰新聞紀錄片的制作在一定程度上受20年代蘇聯“電影眼睛派”的新聞紀錄片創作熱潮的影響,剛進入1938年,中電廠便開始制作了一大批抗戰新聞片和紀錄片,其中包括《東戰場》《克復臺兒莊》《抗戰第九月》《蘇聯大使呈遞國書》《敵機暴行及我空軍東征》《劉甫澄上將移靈》等新聞片和《中原風光》《抗戰建國一周年》等紀錄片;這一批新聞片和紀錄片憑借著低成本、時效性、真實性等突出優點,在社會上贏得了一致好評,時局政治任務圓滿完成。因此,在此后的8年間,重慶抗戰新聞紀錄電影雖然發展不及抗戰故事電影,但創作從未間斷。更重要的是,新聞紀錄電影的真實性也奠定了之后重慶抗戰電影的非虛構手法。
(二)抗戰故事電影統領大后方文化藝術
故事片較之于新聞紀錄片,雖然制作成本較為高昂,但是優點也極為明顯,即更容易被大眾所接受,故事片能夠憑借其情節走向、人物成長、環境渲染等給予觀眾更強的代入感和情感煽動,這是新聞紀錄片的直接性與真實性無法達成的。因此,在新聞紀錄電影獲得成功之后,中電廠和央電場開始著手抗戰故事片的拍攝,并將紀錄電影的非虛構手法大膽運用于這一大批故事片之中。其中何非光導演的作品這種運用最為顯著,他從演員轉行為編劇、導演,編導了《保家鄉》《東亞之光》《新生命》《氣壯山河》《血濺櫻花》,是抗戰電影史中導演作品最多的人,質量也最為上乘。何非光導演的作品囊括了當時重慶抗戰故事電影的所有特點,統領了大后方的文化藝術板塊,在當時成為廣大人民群眾藝術生活的首要選擇和電影談資,同時也喚起了中國人民對日本侵略者的清醒認識和團結一致抗日的理念。
五、重慶抗戰電影的非虛構手法特征
(一)以展現社會現實主義戰爭題材為內容原則
重慶抗戰電影作為歷史潮流和時局政治的產物,其主題內容自然是受到嚴格限制的,一方面當時電影制作的人才、資金、資源等都來源于國營制片廠體制內;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社會和大眾面臨國家滅亡所必需的藝術良藥。重慶的抗戰電影也體現出了中國戰區的獨特之處,即正面戰爭與敵后周旋所并存,這兩種內容選擇在情節架構、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側重點。
1.正面戰爭
何非光導演的“抗戰四部曲”分別為《東亞之光》(1940)、《保家鄉》(1939)、《氣壯山河》(1944)、《血濺櫻花》(1944),是重慶抗戰電影最具代表性的四部作品。這一類影片情感表達細膩,但戰爭場面最為浩大,也更多地通過樹立典型去表現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正面沖突。影片《保家鄉》便是通過中日民族兩方的群像塑造——燒殺搶掠的日軍隊伍和英勇抗爭的農民群眾,通過這一短暫的抗爭故事來映射中日正面戰場上的境況和兩個國家之間的血海深仇。《氣壯山河》也不例外,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何非光將正面抗日的背景搬到了緬甸,展現了中國遠征軍對抗侵緬日軍的悲壯歷史。而《東亞之光》和《血濺櫻花》則展現正面更為別具一格,影片放棄了正面畫卷式的描繪,立足于抗戰即將勝利的發展趨勢,側面突入,不忘總結式和史詩式的批判目光,展現了正面戰爭大背景下個體人物的精神狀態。
總而言之,無論是正面抗爭的展現,還是運用典型的側面突破,都屬于正面抗爭的家國層面的表達,它們更多采取長時間跨度、時空交錯的蒙太奇敘事方式,更多地注重抗戰中敵我雙方的群像塑造或者大環境壓迫下的人性掙扎。《血濺櫻花》中的山田桃太郎便是這一典型代表,這一人物形象經歷天真善良——人性泯滅——幡然悔悟這一變化過程,心靈飽受折磨,最終在內外壓迫和掙扎中完成自我的救贖。此外,何非光導演作為重慶抗戰電影創作的數量和質量擔當,從他的“抗戰四部曲”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展現正面戰爭的影片是占大多數的。
2.敵后周旋
反法西斯戰爭在中國戰區呈現了敵后抗爭和底層人民占據極重要地位的特點,敵后周旋不僅僅停留于騷擾日軍,更是起到了重創日軍、凝聚人民的重要作用。因此,敵后周旋的題材內容是重慶抗戰電影所不可能忽視的,相對于正面戰爭,更能展現普通老百姓面對辱國者的精神狀態和民族危機感,而史東山導演自1932年擔任中國電影制片廠編導委員會委員后,編導制作了大量的抗戰影片,年幼之時便在社會上摸爬滾打的他在創作上呈現了一定的作者性,在其主要影片《勝利進行曲》(1939)、《好丈夫》(1941)、《還我故鄉》(1945)中都更多地呈現出底層關懷,聚焦于抗戰背景下底層人物的聰明才智與犧牲精神。
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史東山導演、田漢編劇的《勝利進行曲》后半部分,那三段展現底層老百姓精神面貌的敵后抗爭故事是依據湖南長沙鄉村中的真實事件而改編的。一是農婦何大嫂誓死反抗日寇侮辱,抱著日寇一起滾入池塘;二是慧海和尚為營救他人破了殺戒,擊斃敵人,自己也壯烈犧牲;三是三個12歲的小學生,在敵軍官面前對著汪精衛的照片大罵“漢奸領袖”而被殘忍殺害。出現在史東山電影中這些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性別但是同屬于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真實描繪,感人肺腑的同時也展現了中國人民的剛烈和不屈。
(二)以運用非虛構性的拍攝手法為美學準繩
從拍攝手法上而言,以新聞片、紀錄片起步的重慶抗戰電影呈現出嚴格的非虛構性美學追求,通過自然主義的攝影手法、燈光技巧盡量使所呈現的畫面充滿真實性和代入感,并且在演員運用調度方面甚至比1945年開始聲名鵲起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更勝一籌。
1.場面調度及長鏡頭
第一節中提到,何非光導演的系列影片都主要展現大場面的正面抗戰,因此場面調度及長鏡頭的畫面展現就顯得理所應當,信息量巨大的大場面和多義性的場面調度相得益彰。《保家鄉》作為何非光第一部重慶抗戰電影,創作沖動來源于他偶然瀏覽一本關于南京大屠殺慘案的畫冊,于悲憤交加之下創作并拍攝了這一全村村民團結奮起抵抗日軍的故事,但是在分鏡頭和攝影方面卻與這一激情相反,最大限度地追求客觀性和真實性。《保家鄉》中有大量的長鏡頭,注重場面調度和排演,盡可能少地切割鏡頭。這一手法的選擇對于《保家鄉》這一環境情節較為緊湊的故事無疑是相得益彰的,長鏡頭和場面調度保證了時空的完整性和統一性,但同時又保證了故事情節、人物動作的多義性。例如在影片中日軍虐殺嬰兒、集體侮辱婦女、用火鉗燙烙抵抗者等幾場觸目驚心的戲份,何非光沒有選擇快節奏分鏡剪切,而是以客觀冷靜的長鏡頭來展現暴行,不僅帶來了身臨其境的真實性,也顧及了觀眾在觀看中的自主選擇能力和冷峻深刻的思考空間。《保家鄉》先后在盟國多個國家進行巡回公映,上座率、口碑都創下中國抗戰電影之最,更一度成為英、美等國官兵的精神食糧,這一傲人成績與該片的運鏡方式是緊密相關的。如果說《保家鄉》在早期奠定了重慶抗戰電影的場面調度及長鏡頭偏好,那么《氣壯山河》則是將場面調度理念深入到了重慶抗戰電影乃至重慶地域電影的骨髓,何非光在該片中精心設計了很多精彩的長鏡頭,例如中方士兵行軍的場面,影片取消了一如既往的特寫鏡頭、空鏡頭的拼接,代之以一個展示隊伍全貌和真實氣勢的運動長鏡頭;還有在多個戰爭段落中,使用復雜的場面調度來配合早期的搖晃鏡頭,完美替代了快節奏剪輯所帶來的緊張感,并更多地體現了真實感和情景感。
2.實景拍攝及自然光
實景拍攝及自然光的使用,是重慶抗戰電影的前身——抗戰新聞紀錄片在非虛構手法上最為注重的一點,而過渡到故事影片之后,實景拍攝及自然光的使用更是成為一種美學追求。這種延續與一位攝影師是分不開的,吳蔚云在其一生的創作中都保持著現實主義傾向,在重慶抗戰電影時期的不同階段,他在參與攝制的新聞片《抗戰實錄》,故事片《保衛我們的土地》《熱血忠魂》《火的洗禮》《孤島天堂》《日本間諜》中都大力推崇實景拍攝和自然光的運用。
實景拍攝及自然光照明的手法選擇在展現正面戰爭的影片中是近乎百分之百的。而之所以將吳蔚云掌機的系列電影作為典型分析,是因為相對于其他影片而言,這些影片將故事焦點放置于個體人物,總體場景格局更小,按照電影工業流程而言應該更多地選擇棚景拍攝。《保衛我們的土地》是重慶抗戰電影第一部全部采用實景拍攝和自然光照明占比過半的影片,青年劉山帶著一家老小到處逃難的過程中,滿目瘡痍的荒涼實景和自然真實的自然光,將影片的戲劇性降到了最低程度,感人肺腑,與《偷自行車的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自該部影片之后,實景拍攝和自然光運用便成了其他影片紛紛效仿的手法特征。經初步估算,《熱血忠魂》和《日本間諜》的實景拍攝占比在95%以上,其他影片在90%以上。在攝影燈光方面吳蔚云更是堅持以自然光照明為主,不得已輔之以簡單的人為照明。
(三)創新性的敘事結構
如果沒有敘事、時空上的革新反叛,那么重慶抗戰電影的非虛構手法就只是沿循新聞紀錄片的政治產物,值得剖析的藝術潮流永遠伴隨著藝術突破。重慶抗戰電影在敘事結構上開創了地圖式的背景敘事,這種手法甚至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好萊塢類型電影中風靡一時(好萊塢是否參考了重慶地域電影這一手法暫時無從考證);在影片時空跨度的處理上,不僅延續30年代社會寫實主義的戲曲式跨越時空,而且更為大膽和碎裂。
1.開創地圖式的敘事背景
相對于早期的重慶抗戰新聞紀錄片,地圖式的敘事模式是開創性、突破性的,在當時的敘事系統中是極為新穎和超前的。這一特征是由我國著名戲曲作家、電影編劇田漢帶到重慶抗戰電影中的。田漢執筆的抗戰影片數量不多,只有兩部:《青年進行曲》和《勝利進行曲》,但都是采用相對分隔、間離化的敘事結構,大膽突破當時線性因果結構的禁錮。田漢在談到《勝利進行曲》的劇本創作時,認為自己是用相對獨立的“故事”來表現抗戰題材,這一手法類似于當代西班牙影片《蠻荒故事》這種同一母題下的短片集。之所以將這種敘事結構稱為地圖式的敘事背景,顧名思義,就是片中的故事沒有時間上的橫向聯系和因果上的縱向聯系,而是處于地理位置上的包容聯系,即片中的故事發生的地點雖然不同,但都同屬于被慘遭侵略的中國大地。這種并行的故事組接方式表面上雜亂無章,實則聯系緊密并且同屬于同一母題之下。此外,地圖式的并列結構使得正面戰爭與敵后抗戰信息相互補充,影片的敘事空間變得更加宏大,影片主題得以廣義升華。
2.打破統一性的時空連續
由牽引力公式可知,牽引力大小是由氣流特性和紗線特性決定的,氣流特性由氣流密度ρ和氣流速度V組成,紗線特性由紗線直徑和紗線阻力系數CD組成。由于輔助管道中氣流參數相對比較穩定,可知突出物通過改變紗線直徑和紗線阻力系數CD來影響牽引力的大小。
由鄭君里和蔡楚生聯合創作的《一江春水向東流》代表了40年代中國電影工業的巔峰水平,其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江春水向東流》非連續時空的壓縮和拼接,十分成熟地凸顯電影的時空假定性。而在此之前即1944年的《氣壯山河》中,何非光導演便超前、系統地凸顯了時空假定性,影片中中國遠征軍入緬甸作戰的情節占了大部分,要在短短1個小時內展現遠征軍數年的作戰情境,那么時空連續性是必然需要打破的,也是重慶抗戰電影尤其是正面抗戰題材所常用的。例如何非光“抗戰四部曲”和其他影片,雖然時空壓縮和拼接相對而言不明顯,但都盡量把影片時間壓注在有情感表達的故事段落上,例如《東亞之光》中高橋三郎出征前和被俘后在俘虜營的雙線敘事,有重點有側面,兩條線相互鋪墊相互渲染;再例如《血濺櫻花》中戰爭爆發前后,高云航、表妹立群、日籍同學春子、空軍少尉山田桃太郎四個人的愛恨情仇與不同背景下的關系。由此可看出,何非光不僅僅鐘愛宏大的敘事結構和時間跨度,并且在影視時空與現實時空的處理上是恰到好處的。
綜上所述,相較于早期的新聞紀錄電影和30年代現實主義創作,重慶抗戰電影的非虛構手法特征的形成,有延續,但更重要的是延續中的革新以及立足于現代電影文化語境上回望歷史的偉大開創。在這短短的十年光景,何非光導演以及他最具代表性的“抗戰四部曲”奠定了重慶抗戰電影的非虛構手法特征,筑成了當時重慶電影大廈的根基和主梁。而注重底層關懷的導演史東山、強調自然主義的攝影師吳蔚云、執著于獨立敘事的編劇田漢等藝術大家在中國電影制片廠、中央電影攝制場的支持下不斷為重慶抗戰電影大廈的非虛構手法特征添磚加瓦,做出了進一步的鞏固。
六、重慶抗戰電影非虛構手法的演變
重慶抗戰電影作為二戰戰火培育下的藝術曇花,在完成它的時代政治任務后,慢慢淡出了中國電影舞臺,但其研究價值遠遠尚未終結,重慶抗戰電影引領了重慶地域電影的第一次輝煌,其最大的美學特點——非虛構手法給之后的重慶地域電影的發展在各方面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一)“山城”印象
重慶憑借著獨特的山地地形特征,以及穿插于山城間的萬千河流,在重慶抗戰電影中留下了極具辨識性的畫面元素。在非虛構手法中,展現故事發生的地理環境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早期重慶抗戰電影中所堅持的實景拍攝,重慶凹凸不平的地形、近在眼前的山包、梯坎交錯的小巷經常得到有意或無意的表現。而在接下來的重慶地域電影中,由“山城”這一地形所形成的城市地理面貌,成為電影畫面中獨特意象的重點表達。在2006年寧浩導演的影片《瘋狂的石頭》中,重慶的斜坡、防空洞、爬梯上坎的小巷不僅都得到了大規模的實景展現,而且這些獨特的視覺體驗更服務于劇情發展、人物形象塑造等影片內核。在2016年張一白導演的影片《從你的全世界路過》中,“山城”印象更加現代化和風景化,但重慶的獨特之處還是包含其中,例如兩段愛情故事在老十八梯、鵝公巖大橋上的開展,都為故事加分不少。總而言之,無論重慶地域電影如何發展,重慶地理形態特征永遠是影片所青睞的符號表達和非虛構性元素。
(二)移民與遷徙的精神漂泊
抗戰期間由于陪都的建立,大量人口內遷至重慶地區,高達100萬人。隨著戰事的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多的難民進入重慶,加上重慶市區面積、規模的擴大,自1942年起,日軍減少對重慶的空襲,市區相對“安全”,先前被疏散的市民大批回遷。幾年間的人口內遷、逗留、外遷造就了當時重慶人大量的精神漂流、情感糾葛以及外來文化的沖擊碰撞。1940年蘇怡執導的抗戰片《青年中國》中便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重慶移民的沖突和融合,來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宣傳隊進到村莊宣傳抗日、幫助農民,這些青年為了同樣的目標、理想而奮斗,但是導演也有意識展現了他們之間細微的沖突和不適,如此卻更加貼合全國各地、各民族、各階層聯合抗日的母題。而直轄后的三峽大移民更是形成了“故土難離,他鄉月更明”的社會普遍情感,對此表現得最為直觀的是2008年上映的影片《秉愛》。導演馮艷帶著觀眾走進了一個居住在三峽庫區的普通農婦張秉愛的困境。大壩截流,這位肩負全家生活重擔的農婦,守著釘子屋,因沒有分得該有的土地,誓不遷走。
七、新時期重慶地域電影的新探索——非虛構手法復興
(一)重拾社會關懷與歷史回望
重慶抗戰電影作為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有力文化戰線,也是撫愈戰爭創傷的藝術良藥,承擔了電影藝術在特殊時期的社會關懷和責任。而在電影高度工業化和商業化的今天,重慶地域電影愈來愈向大眾的娛樂旨趣發展,鮮有如《三峽好人》一類社會關懷的影片,更沒有如《建國大業》一類歷史回望的影片。重慶在戰爭時期可謂多難之邦,歷經持續6年多的“重慶大轟炸”、因躲避轟炸窒息死亡7000余市民的“大隧道慘案”等事件體現了重慶人民在國難當頭時的堅韌不屈,這些富有歷史厚重感的事件都值得在銀幕上再現;另外,重慶普通大眾的生活狀態、社會矛盾都值得去探討和展示,相信重拾社會關懷和歷史回望的影片會得到較好的商業回報和市場口碑,而并非只局限于商業類型片在重慶地域的發掘,如此重慶地域電影只會淹沒在眾多商業類型片的大流中。
(二)追求自然主義攝制手法與影片內核的巧妙融合
重慶抗戰電影中的自然主義攝制手法自然無法完全在當今后現代文化語境下遺傳下來,但是自然主義攝制原則所帶來的客觀性、真實性、多義性等等是能為影片服務的。一方面,當時的重慶地域電影可以思考和采用的自然主義攝制手法包括非職業演員的發掘和采用、自然光與人造燈光的融合、重慶實景的展現、客觀冷靜的運鏡方式等手法;另一方面,攝制手法選擇的前提是要貼合影片氛圍,并且為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塑造服務,也就是與影片內核進行巧妙融合,例如由楊超導演的影片《長江圖》中,巫山區的蜿蜒江流、氤氳水汽與李屏賓鏡頭中的大氣沉穩渾然一體,相得益彰,客觀理性地展現了長江秀美的同時,又融天地萬物于山水的宏偉壯麗中。總而言之,非虛構手法不是單純指自然主義攝制手法的采用,而是指從影片的人物、情節、主題等內核出發,才能從日常人物中提煉出藝術典型,從藝術情境中提煉出藝術意蘊。
(三)重慶地域電影的時代性、國際化目標
注釋:
① 張智華:《我國當代現實主義電影思潮的變化與發展》,《上海大學學報》,2008年第15期。
② 朱珠:《巴贊與克拉考爾非虛構主義電影理論之比較》,《電影理論史家》,2008年第1期。
③ 鄭雪萊:《世界電影鑒賞辭典》,福建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頁。
④ 羅顯勇:《論重慶抗戰電影“非虛構主義美學”的成因和特點》,《當代電影》,2013年第1期。
⑤ 王太偉:《重慶抗戰時期的電影藝術》,《重慶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
⑥ 周晶:《消解與重建——重慶抗戰電影的影像精神》,《電影評介》,2011年第22期。
⑦ 李悅:《抗戰時期重慶電影文學敘事研究》,《重慶師范大學》,2011年第4期。
⑧ 陳墨:《“東亞之光”:何非光人生影事初探》,《當代電影》,2009年第2期。
⑨ 朱丹彤:《抗戰時期重慶的人口變動及影響》,《重慶交通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
⑩ 陳希:《直轄后的重慶電影及電影中的重慶》,《學苑論壇》,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