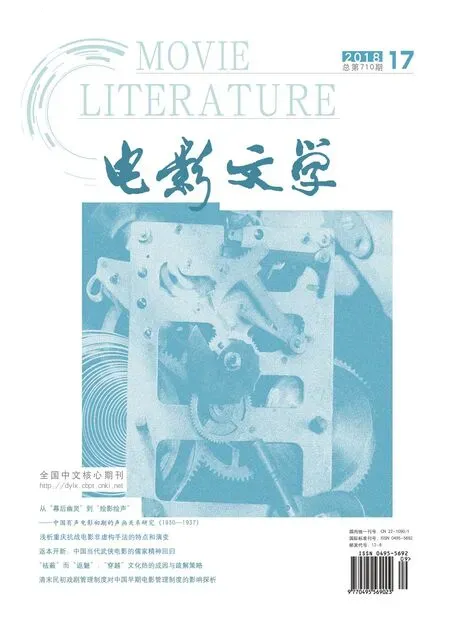從作者論看喬治·盧卡斯的電影
雷 超
(周口師范學(xué)院 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河南 周口 466001)
美國(guó)導(dǎo)演喬治·盧卡斯的影響力在電影界是不可否認(rèn)的。他建立了龐大的“盧卡斯電影帝國(guó)”,所制作的《星球大戰(zhàn)》系列共六部,前后歷時(shí)20多年,是電影史上迄今最為成功的科幻電影。盧卡斯電影吸引了廣泛的關(guān)注和追隨效仿。詹姆斯·卡梅隆,彼得·杰克遜等導(dǎo)演或是在其《星球大戰(zhàn):新希望》(1977)的影響下立志踏入影壇,或是曾在執(zhí)導(dǎo)筒之前將《星球大戰(zhàn)》反復(fù)觀看十多遍,并在自己的代表作中向《星球大戰(zhàn)》致敬。在世界市場(chǎng)中,盧卡斯的電影更是一部接一部地上演票房奇跡,在近半個(gè)世紀(jì)中影響了數(shù)代觀眾。迄今為止,當(dāng)人們提及建立起一個(gè)“帝國(guó)”的導(dǎo)演時(shí),首先想到的往往便是在創(chuàng)作數(shù)量上并稱不上高產(chǎn)的盧卡斯。而透過(guò)盧卡斯名字的光芒,當(dāng)我們對(duì)其作品進(jìn)行整體上的把握時(shí)就不難發(fā)現(xiàn),在盧卡斯電影中復(fù)沓出現(xiàn)的電影主題、主題旨?xì)w以及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味的視聽語(yǔ)言,都賦予了盧卡斯的電影“作者”資格。
一、體制背景
在談及盧卡斯電影“作者”資格時(shí),首先必須關(guān)注的正是其在制片權(quán)掌控方面,與好萊塢體制背景之間的特殊關(guān)系。
作者論作為一種電影批評(píng)方法,誕生于20世紀(jì)50年代。法國(guó)的電影理論家阿斯特呂克在《新先鋒派的誕生:攝影機(jī)自來(lái)水筆論》中,提出了電影作者依靠攝影機(jī)來(lái)寫作的觀點(diǎn)。阿斯特呂克認(rèn)為,導(dǎo)演有必要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有著絕對(duì)控制權(quán),而非僅僅是一個(gè)文案(小說(shuō)或劇本)的機(jī)械搬演者。這被視為是作者論之濫觴。在此之后,特呂弗、巴贊等人發(fā)展了阿斯特呂克的理論,主張導(dǎo)演集中地、持續(xù)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現(xiàn)個(gè)性化元素,提高導(dǎo)演的地位。對(duì)于希區(qū)柯克、約翰·福特等個(gè)性鮮明,作品序列風(fēng)格明顯的美國(guó)導(dǎo)演,巴贊主編的《電影手冊(cè)》的一干批評(píng)者給予了高度評(píng)價(jià)。在作者論進(jìn)入了學(xué)界的視野之后,導(dǎo)演們有了更充足的進(jìn)行自我表達(dá)的理由,而批評(píng)者也開辟了導(dǎo)演研究分支,電影研究進(jìn)一步學(xué)院化。
而希區(qū)柯克、福特等人的最大共同點(diǎn),正是能夠在美國(guó)的制片廠體制下依然踐行“導(dǎo)演中心制”,在電影的生產(chǎn)流程中,擔(dān)負(fù)起從策劃到剪輯的一系列任務(wù),同時(shí)也承擔(dān)由于自身的創(chuàng)新而有可能招致觀眾不滿的風(fēng)險(xiǎn)。在電視開始挑戰(zhàn)電影的20世紀(jì)60年代,這類具有自我意識(shí)的電影人無(wú)疑帶來(lái)了一股挽救電影的新鮮空氣。好萊塢順勢(shì)進(jìn)行了一個(gè)體制內(nèi)的微調(diào),賦予了導(dǎo)演以稍大的權(quán)力,但旨在將導(dǎo)演打造為與明星演員一樣的能招徠觀眾的“品牌”,而非任由導(dǎo)演如歐洲電影導(dǎo)演一樣,成為能肆無(wú)忌憚進(jìn)行主觀表達(dá)的個(gè)體。在這樣的背景下,盧卡斯橫空出世,成為一個(gè)從試圖顛覆體制,到最終和體制互相妥協(xié),實(shí)現(xiàn)共生的典型電影人。
不難發(fā)現(xiàn),在當(dāng)代美國(guó)電影導(dǎo)演中,喬治·盧卡斯是頗為特殊的。一方面,盧卡斯與他的“星戰(zhàn)”帝國(guó)被緊密地捆綁,而《星球大戰(zhàn)》更是成為好萊塢電影生產(chǎn)機(jī)制的里程碑式作品。自此之后,好萊塢電影出現(xiàn)了兩個(gè)明顯的趨勢(shì):一是仰賴特效技術(shù)的進(jìn)步,對(duì)視覺奇觀開始了狂熱追求;二則是電影的類型化,電影制作的程式化,也都進(jìn)入到成熟、高效的階段,在這兩方面《星球大戰(zhàn)》是當(dāng)之無(wú)愧的肇始之作。但另一方面,盧卡斯又始終堅(jiān)持自己是一名反傳統(tǒng)、反體制的獨(dú)立電影人。他保持著與好萊塢的距離,時(shí)常對(duì)好萊塢電影惡言相向,并對(duì)摯友科波拉為好萊塢所控制而有著玩笑式的嘲諷。可以說(shuō),盧卡斯是一個(gè)另類,他以對(duì)抗體制成規(guī)的姿態(tài)進(jìn)入電影工業(yè),卻得到了大批追隨者,引領(lǐng)了一種新的成規(guī)。他以反抗類型化的創(chuàng)作為使命,但是卻取得令人矚目的商業(yè)成功,在后來(lái)者的蕭規(guī)曹隨中實(shí)際上促進(jìn)了電影的類型化。這是由主客觀多方面因素造就的。
從主觀上來(lái)說(shuō),盧卡斯追求藝術(shù)自由的理念從未變過(guò)。早在其處女作,有著極強(qiáng)的實(shí)驗(yàn)性質(zhì)《五百年后》(1971)和帶有自傳意味的《美國(guó)風(fēng)情畫》(1973)中就可見端倪。兩部電影全由盧卡斯自編自導(dǎo),并且進(jìn)行了徹頭徹尾的自我表達(dá):一是滲透自己對(duì)人類未來(lái)生活于極權(quán)和冰冷科技中,人性淪喪的擔(dān)憂;一是紀(jì)錄自己的青春歲月。而《美國(guó)風(fēng)情畫》問(wèn)世后便引起轟動(dòng),讓盧卡斯被好萊塢相中,并成為一個(gè)“品牌”。但這之后的盧卡斯并無(wú)意延續(xù)《美國(guó)風(fēng)情畫》樸實(shí)、感人的風(fēng)格,而是我行我素地又回到了《五百年后》怪誕的、指涉政治的科幻路線。結(jié)果在科幻電影并不景氣的70年代,盧卡斯以令人驚艷的想象和酣暢淋漓的敘事贏得了觀眾山呼海嘯的歡迎和奧斯卡六項(xiàng)大獎(jiǎng)的加冕,從此越發(fā)得到了自由創(chuàng)作的權(quán)利。而在客觀上,如前所述,好萊塢在體制上進(jìn)行了微調(diào),讓獨(dú)立制片廠中和了獨(dú)立電影人和大制片廠制度之間的矛盾。盧卡斯和科波拉、斯皮爾伯格等導(dǎo)演都選擇了獨(dú)立制片廠這種被體制“招安”的模式,心照不宣地迎合“觀眾原則”,復(fù)制著自己的成功,也使得他人能復(fù)制自己的成功。盧卡斯后來(lái)一心一意地繼續(xù)“星戰(zhàn)”主題,并且保守地維持自己的特色,即奇觀式的視覺語(yǔ)言,加上簡(jiǎn)單、“膚淺”而又令觀眾備感刺激痛快的劇情設(shè)置,以及一成不變的美式的傳統(tǒng)核心價(jià)值觀,就是明證。
在這種和體制的共生中,成立了盧卡斯制片公司以及工業(yè)光魔的盧卡斯成為電影當(dāng)仁不讓的掌控者。正如盧卡斯在談到自己在《星球大戰(zhàn)》的前三部特別版中起到作用時(shí)所說(shuō)的:“我是執(zhí)行制片人,負(fù)責(zé)選演員,寫劇本,決定影片的基調(diào)等問(wèn)題。……每天都到,一切都要經(jīng)我同意……這是合作的結(jié)晶。”可以說(shuō),盧卡斯就是整個(gè)“星戰(zhàn)”系列的靈魂。
二、主題指歸
成就盧卡斯“作者”身份的,無(wú)疑是他傾盡心血完成的,既有“一意孤行”色彩,又有迎合觀眾之嫌的“星戰(zhàn)”系列,這也是盧卡斯最吻合雷諾阿所說(shuō)的,一個(gè)導(dǎo)演“終其一生只拍一部電影”論斷的代表作。猶如結(jié)撰一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在“星戰(zhàn)”系列中,盧卡斯表現(xiàn)出了具有穩(wěn)定性的故事講述方式,并使其對(duì)好萊塢在新時(shí)代的創(chuàng)作方向提供了啟發(fā)。
(一)世界觀與情節(jié)鋪排
整個(gè)“星戰(zhàn)”故事,以及其龐大的世界觀完全是盧卡斯的自出機(jī)杼。在“星戰(zhàn)”中,人類的生存和活動(dòng)范圍,包括沖突都到達(dá)星際層面。數(shù)千個(gè)星系組成了銀河系共和國(guó),而其中的加盟星系在杜庫(kù)伯爵的策動(dòng)下決定脫離共和國(guó),戰(zhàn)爭(zhēng)一觸即發(fā)。絕地武士歐比旺曾在《星球大戰(zhàn)前傳1:幽靈的威脅》(1999)中收聰明俊秀的少年安納金·天行者為徒,二人肩負(fù)起徹查沖突,維護(hù)和平,保衛(wèi)女王阿米達(dá)拉的重任。然而戰(zhàn)爭(zhēng)依然爆發(fā)了,絕地武士遭到陷害,安納金也倒向了黑暗,成為邪惡的達(dá)斯·維達(dá)。安納金的妻子則在生下了莉婭和盧克后死去。兩個(gè)孩子被尤達(dá)大師分開撫養(yǎng),盧克在長(zhǎng)大后繼續(xù)與邪惡銀河帝國(guó)對(duì)抗,在漢·索羅等人幫助下先后解救了妹妹,認(rèn)識(shí)了父親。最終,安納金贖罪死去,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反抗軍取得了勝利。“星戰(zhàn)”中人物眾多,有著令人嘆為觀止的龐大世界和炫目科技,然而其敘事主線卻是簡(jiǎn)單的正邪輪回,黑暗力量與光明力量此消彼長(zhǎng),最終以正義一方勝利而告終。天行者父子的經(jīng)歷險(xiǎn)象環(huán)生,陰謀密布,盧克與身邊人的關(guān)系更是柳暗花明。一言以蔽之,盧卡斯賦予了“星戰(zhàn)”系列引人入勝,出乎觀眾的意料,但是又不難讓觀眾理解的情節(jié)。人們?nèi)缧蕾p連環(huán)畫一般,癡迷于盧卡斯不拘一格的奇妙世界,代入到盧克和莉婭等人的艱難困厄之中,“愿原力與你同在”等話語(yǔ)深入人心。
(二)敘事技法
在敘事技法上,盧卡斯深諳通俗文學(xué)之道,不斷用幽默和悲情來(lái)調(diào)整敘事節(jié)奏,帶動(dòng)觀眾的情緒,這一點(diǎn)也成為后續(xù)諸多好萊塢大片中的法寶,甚至形成了精細(xì)到分鐘的敘事程式。如愛耍貧嘴的漢·索羅和楚巴卡,以及兩個(gè)機(jī)器人R2和3PO始終是給觀眾帶來(lái)歡笑的角色。3PO是個(gè)話嘮,總是沒(méi)完沒(méi)了地說(shuō)話,即使是在自己四分五裂時(shí),也依然口齒伶俐,活躍著氣氛,在《星球大戰(zhàn)3:絕地歸來(lái)》(1983)中,3PO又被單純的、浣熊一般的伊沃克人奉為神,展開了一段逗樂(lè)的劇情,3PO也成為眾多觀眾追捧的對(duì)象。而天行者父子則代表了凝重、恩怨,一直為命運(yùn)和欲望所糾纏。出身平平的安納金失去了母親,背叛了師門,盧克也失去了親人。電影中不乏觸發(fā)觀眾哀情的互文。如盧克駕駛飛車飛過(guò)黃土茫茫的塔圖,而多年之前,父親安納金也是在這里贏得飛行比賽的冠軍,他們各自走向自己的或正或邪的“遠(yuǎn)大前程”,這種互文無(wú)疑是令人唏噓的。
(三)古典美學(xué)趣味
從美學(xué)趣味上來(lái)看,盧卡斯深厚的古典情結(jié)滲透在電影的故事原型中。盡管科幻電影往往指向的是未來(lái),然而盧卡斯卻一再在電影中強(qiáng)調(diào)過(guò)去。如片頭字幕總是“很久以前,在遙遠(yuǎn)的銀河系”。盧卡斯實(shí)際上是將保守主義的價(jià)值觀移植到了一個(gè)超現(xiàn)實(shí)土壤中,以科幻、前衛(wèi)的包裝上演古典戲劇。電影中盧克對(duì)抗邪惡父輩,天行者父子的少年成長(zhǎng),安納金所受到的魔鬼誘惑,絕地武士的挽歌等,都可以在《哈姆雷特》《大衛(wèi)·科波菲爾》《浮士德》《堂吉訶德》等古典名著中找到影子。而電影所傳達(dá)的熱愛家庭與親人,邪不勝正,個(gè)人英雄主義等價(jià)值觀更是為好萊塢電影屢試不爽。
三、視聽語(yǔ)言
盧卡斯的天才創(chuàng)造,以及對(duì)電影的精益求精,也體現(xiàn)在了諸多奇觀上。早在正傳三部曲中,電影的視聽語(yǔ)言,從美術(shù)設(shè)計(jì)、道具布景、視覺特效到音響效果,就都已令觀眾贊嘆不已。電影中的各種怪異生物,構(gòu)思精巧的如“死星”等設(shè)備,都已值得大書特書。及至前傳三部曲以及《星球大戰(zhàn)7:原力覺醒》(2015)中,數(shù)字技術(shù)更是一再滿足了觀眾對(duì)于異域文明的想象。銀河系中不同星球或遍布沙漠,或森林環(huán)繞的場(chǎng)景,人類活動(dòng)的極具未來(lái)感的飛船或原始蠻荒之地,戰(zhàn)斗機(jī)駕駛員高速穿越狹窄的甬道等,更是給予了觀眾視覺上的盛宴。正如盧卡斯曾經(jīng)表示的:“在《星球大戰(zhàn)》中,我要時(shí)時(shí)收住我的想象力,深受技術(shù)所能達(dá)到的敘事范圍的限制。而在《星球大戰(zhàn)前傳1》中我可以讓環(huán)境足夠大,大到超越我的故事還綽綽有余。數(shù)字技術(shù)電影制作具有無(wú)限的可實(shí)現(xiàn)性,能將人們種種奇異美麗的想象搬上銀幕,并促使人們做出更加絢麗的幻想。”
《星球大戰(zhàn)》系列對(duì)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的開拓與探索,使得盧卡斯贏得了“數(shù)字電影之父”的美稱,也使得在有著“大師情結(jié)”,講究“藝術(shù)精神”的中國(guó)電影批評(píng)界,人們對(duì)盧卡斯有著一種偏向貶抑的評(píng)價(jià),認(rèn)為其不過(guò)是一個(gè)玩弄特技,作品浮華花哨的匠人而非藝術(shù)家。事實(shí)上,盡管對(duì)數(shù)字技術(shù)的濫用,對(duì)奇觀的盲目尊崇,成為美國(guó)電影的一個(gè)負(fù)面特征,似乎也使得運(yùn)用數(shù)字化處理技術(shù),給觀眾制造令人目眩神馳的畫面已經(jīng)不足以成為盧卡斯的藝術(shù)個(gè)性。然而不可否認(rèn)的是,盧卡斯在這條路上具有得風(fēng)氣之先的開路者地位,并且他用力之深,已使得其影片中留下了有可識(shí)別性的影像符號(hào),這是與當(dāng)代“為奇觀而奇觀者”截然不同的。能與盧卡斯比肩者,只有斯皮爾伯格、卡梅隆、杰克遜等寥寥數(shù)人而已。在探討盧卡斯作為電影作者的美學(xué)觀念以及創(chuàng)作傾向時(shí),盧卡斯傾力打造的幻光魅影是不可回避的。
從游走到體制之外,到自己成為新體制,新范式的奠基人,喬治·盧卡斯憑借著“星戰(zhàn)”等電影釋放了自己的個(gè)性和豐沛才華。在成就自我的同時(shí),也為后人提供一座值得挖掘的IP富礦,這是盧卡斯作為一名“作者”完成自己藝術(shù)使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