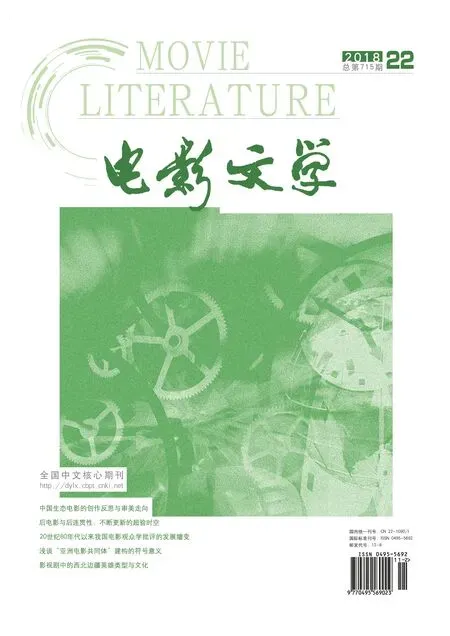經典影視劇的淪陷:彈幕狂歡下的審美嬗變及倫理反思
熊曉慶 高 尚
(1.河海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0;2.滁州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安徽 滁州 239000)
一、彈幕視頻中的經典影視劇:工具化與附庸化
兼備了青年亞文化與網絡亞文化混合特性的彈幕視頻對于時下個性化突出的亞文化青年而言似乎有著難以抗拒的魔力。彈幕愛好者在主動分享、創造以及傳播彈幕內容的同時也得以盡情游戲、互動,創造出一幅幅娛樂狂歡的群像,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彈幕迷群的自我歸屬與文化認同。在傳播內容上,彈幕視頻主要依托于動畫、動漫、游戲以及小說類文化的作品,如動畫原作、二次創作、同人作品、惡搞等次文化色彩濃厚的作品。經典影視劇在彈幕視頻傳播中往往屬于二次作品或者惡搞作品,由于彈幕視頻兼具了松散性與開放性的特征加之傳播的門檻又低,理論上任何視頻內容都可以成為它的傳播素材與傳播內容。因此,經典影視劇中的任何人物、情節、臺詞甚至背景配樂都有可能成為彈幕傳播的素材;從傳播方式上分析,經典影視劇在彈幕視頻中往往以兩種方式出現,一種是以完整體的形式,而另一種則是以片段剪輯的方式,前者是以整部劇加流動彈幕的形式進行傳播,而后者則是經過編輯的影視片段對特定內容加以傳播。就經典影視劇本身而言,這兩種呈現方式所產生的效應結果本質上并沒有不同。經典影視劇在彈幕傳播的過程中其本身并不能構成觀影的主體,流動彈幕的游戲性以及游戲過程的歡愉性要比具體傳播內容重要,其結果是經典影像凸顯為彈幕視頻的附庸物。彈幕視頻傳播中常見的經典影視劇如《三國演義》《亮劍》《四渡赤水出奇兵》等,無論是劇中人物抑或臺詞、情節,它們的出現都是為了游戲,對于經典的“肢解”也變成一種極為普通的現象。流動性彈幕的游戲性以及道德嚴肅感的喪失,使得人們在觀看經典影視劇的同時很難思考深刻的問題也很難形成相對獨立的批判思維。
二、彈幕狂歡下的經典影像:娛樂、戲謔與顛覆
(一)故事情節娛樂化
西方哲學與文學批判中的解構主義認為“文本不能只是被解讀成單一作者在傳達一個明顯的訊息,而應該被解讀為在某個文化或世界觀中各種沖突的體現”。換言之,一個被解構的文本會顯示出許多同時存在的各種觀點,而這些觀點通常會彼此沖突。如果將解構閱讀與傳統閱讀進行對立比較的話,也會顯示出文本中的許多觀點是被壓抑與忽視的。相比原有文本意義存在,彈幕族解構式觀看卻將經典影視文本的存在意義發揮到極致。在1994年版的《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對罵王朗的橋段以及《帝國的毀滅》中元首的憤怒這些影視片段被反復且廣泛地使用于各類彈幕視頻中,彈幕字符對傳統戲劇情節的意義再構建則完全突破了公共審美的邊界。影片本身的嚴肅背景以及意義傳遞已不再重要,此時觀賞的重心不再是戲劇情節本身,而是變成一種精神上的消遣娛樂。這些經典橋段在彈幕字符的作用下或變成吐槽的對象、或成為惡搞的工具。可以說經典影視劇的公共意義被顛覆或被曲解,從而形成彈幕娛樂的主要方式。彈幕族在觀看視頻內容的同時,有意識地主動對視頻內容不斷解構,同時也在利用彈幕符號意圖實現對彈幕文化補充和完善,彈幕在這場解構盛宴中則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從而創造出一幅幅娛樂狂歡的景別。
(二)影視臺詞戲謔化
彈幕能夠扮演解構工具的角色,因其能夠達到、完成或促進解構目標的實現。對于彈幕字符如何成為解構工具的理解,則須對彈幕本身加以考察。視頻解構的過程同樣也是內容意義打碎、重構與再組合的過程,彈幕字符為這一過程的開展提供必要的條件。由于彈幕視頻本質上屬于一種開放性文本,受眾利用形形色色的彈幕字符對這種開放性文本盡可能多地展開意義重構。最為常見的彈幕如“我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出自《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對罵王朗的臺詞),“二營長,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出自《亮劍》),它們的出現與視頻內容本身二者相結合時,文本意義或發生反轉,或產生對視頻內容的吐槽、或贊賞、或將與之有關與無關的內容相聯系從而產生一種戲謔的效果。此彈幕符號儼然已經變成一種催化劑,劇中臺詞也被反復挪用、轉接至別的場景成為其他場景中的彈幕傳播內容,它使得視頻內容得以進一步拓展,從而產生出不一樣的作品。依照符號學的觀點,如果將經典影視劇中的臺詞符號視為一級符號,那么變成彈幕的臺詞文本則構成了一種二級符號。所謂的“打碎、重構與再組合”已經變成了一種神話過程,這種神話過程也將原有的公共審美與理解加以“扭曲”,即經過彈幕加工過的臺詞文本其意符與意指均發生變化。雖然彈幕字符中的大部分能為人們所辨識,但是它們本身就存有意義上的規定性,如果沒有相關的背景了解,這些普通的字符很難被圈外人所理解。也正是這種神話過程與曲解運動使彈幕族與圈子外的人相隔離,他們用一種更為自我的方式來“抵抗”公共審美與理性道德,這種“抵抗”也進一步鞏固了他們對彈幕文化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從而營造出一種“與眾不同”“抱團取樂”的審美錯覺。
(三)人物形象顛覆化
解構主義認為任何文本并非封閉性的,解構主義學者雅克·德里達指出“一篇‘文本’不再是一個已經完成的寫作集合,不是一本書所包含的或書頁空白之間存在的內容,它是一種差異作用下的網狀結構,是由各種蹤跡編成的織物,這織物不停地指向其邊界之外的東西”。如果將以上表述用于對彈幕視頻傳播中的內容解構則最為貼切不過了,既然文本是開放式,基于彈幕族自身條件差異,那么任何彈幕視頻在被觀看的同時,觀眾對視頻內容所產生的認知也會各有不同。同“一千個讀者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格言相似,在這“一千個哈姆雷特”當中,未必沒有一位是莎士比亞所認同的。當一切內容都可能變成素材提供給彈幕使用者,這些二次元創作的視頻大多以原有視頻作為敘事框架,但其中主題風格卻并不固定,通過技術剪輯與聲話處理,以及說唱元素的融入、二次元鬼畜情節的涵蓋等技術手段的加入,彈幕作品本身就是對原有戲劇人物形象進行重置。經典影視劇中的諸葛亮既不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文臣,也非“多智而近妖”的智者,他可能是罵街能手、饒舌達人、廣告狂人等;在《帝國的毀滅》中,元首也不再以納粹形象示人,他可能是一位游戲失敗者、沒有完成假期作業的學生、考試掛科的人等。這些彈幕作品無所謂善惡界限,缺乏嚴肅的道德立場,仿佛一切都是為了戲耍而存在。這種個體匿名與理性思考的缺位直接導致任何事物都可以被拿來當作消遣的元素,經典影視劇中人物形象自然也就難逃被顛覆的命運。
三、彈幕狂歡的背后:另類的規訓化與同質化
人掌握技術還是技術控制了人,這是反烏托邦小說中古老而又永恒的話題。不得不承認彈幕視頻源自網絡技術的發展,在彈幕族沉醉于自我狂歡的盛宴時這背后不乏視頻傳播技術所提供的便利。但過分依賴彈幕技術所提供的工具從而沒有任何節制與邊界地宣泄自我情緒以滿足自我的快感,這本身就是一種陷阱。對于深受御宅文化影響的網絡彈幕迷群而言,利用相關的網絡技術,進行反傳統、反權威的同時也在規訓書寫著自己的權威,生產著屬于自己的權力。“實際上,權力能夠生產。它生產現實,生產對象的領域和真理的儀式。個人及從權力身上獲得的知識都屬于這種生產。”彈幕傳播的過程即為權力生產的過程,彈幕參與者無形中成了權力規訓的實體對象。彈幕語言的使用、彈幕符號的散布以及對彈幕文化的認同最終形成彈幕一族的權力規訓技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彈幕族在視頻觀看時存在多種路徑解構傳統戲劇影像,但是這些技術手段的最終指向還是落入了反權威化、反傳統化與去中心化的范疇。無論是二次作品對原有作品進行何種重新拼貼與組合,再造出無數新的文本,但最終還是會指向娛樂與惡搞。這反映出,彈幕御宅族在反傳統性的過程中卻樹立起了另類的同質化傳統,即娛樂與惡搞。伴隨對經典影視劇“肢解”的是彈幕族沉浸于自我世界的消遣行為,在縱情狂歡的過程中樹立起屬于自己的權威,即無惡搞不歡樂。彈幕族不分青紅皂白地滌蕩一切的后果就是沒有信仰、沒有崇高、沒有神圣,在對傳統影視劇的“改編”過程中這類現象也最為普遍,也正是這樣的“沒有信仰、沒有崇高、沒有神圣”最終變成了彈幕族的權威。這不禁讓人想起約翰·彼得斯所言“看不見的東西,渴望愈加迫切;我們渴望交流,這說明,我們痛感社會關系的缺失”。彈幕視頻這種發生在虛擬空間的傳播方式并不能替代現實中的人際交往,尤其是在彈幕視頻對公共審美以及倫理提出挑戰的當下社會,如何合理地利用與發展彈幕視頻則成為值得深思的問題。
四、結 語
有人說彈幕視頻的出現與發展是對網絡公民的有力賦權,是有利于文明的進步的,但彈幕視頻在傳播過程中同樣產生了相應的副作用。它在反傳統、反穩定僵化的同時也將反傳統、反穩定僵化形塑成了自己的權威與穩定。換言之,這種反傳統性在擊碎傳統權威的同時又落向另一個權威,造成網絡虛無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泛濫。正如業內人士所述“對爛片而言彈幕場是遮羞布,彈幕是小屏幕上的集體狂歡,放到大銀幕上就是耍流氓”。彈幕視頻依靠二次元文化的維持,一旦脫離這樣的社會亞文化氛圍,它能發展成什么樣態,結果不可預知。此外,對于彈幕中的“臟”話以及攻擊性、辱罵性字符如何才能有效地規避,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詩人紀德曾說“用美好的情感,卻創造了糟糕的文字”,現如今,制造出的卻是糟糕的彈幕,更遑論情感是否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