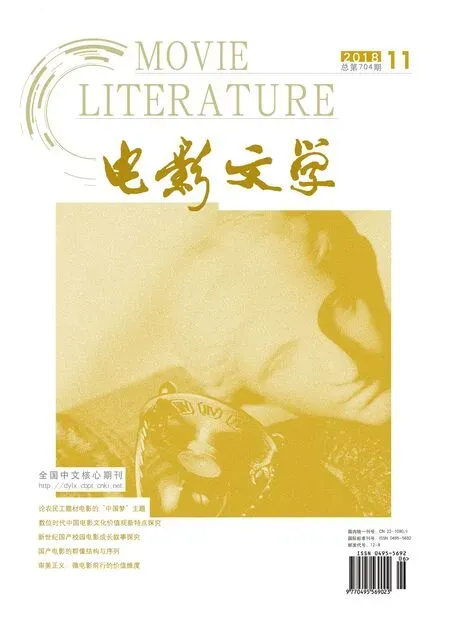跨文化視域下中美史詩電影比較
崔秀芬
(商丘師范學院 外語學院,河南 商丘 476100)
早在20世紀中期,美國就已經拍攝了由維克多·弗萊明根據話劇改編而成的《圣女貞德》(1948)這樣具有史詩風格的電影。到新世紀,史詩電影更是好萊塢大片的重要組成部分,如2004年就被稱為美國的“史詩電影年”。而在中國電影中,也有這樣觸摸歷史神經的氣勢宏闊之作。電影人或是通過電影來有意建構歷史意識,或是在作品中無意中流露了自己的使命感和歷史觀。中美史詩電影既有類似之處,又不乏區別。當前,影像傳播在跨文化交流時代日益發揮著獨特作用,我們有必要從跨文化的角度對兩國史詩電影進行觀照。
一、跨文化與史詩電影創作
文化本身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復雜性。羅杰·基辛指出:“文化,可被認為是在廣泛的共識和深度的規范上被共享的,也受個體特異性而有所變化的,然而又并不完全是一個個體認識、了解、感受世界的一種體系。不是每一個個體都精確地共享同一種文化理論,因為不是每一種文化都在同一文化區域。”從這一角度來說,中美兩國無疑處于兩種文化區域,擁有著不同的文化體系。中國浩瀚輝煌的歷史本身就足以為史詩電影提供各類文化原型和符碼,與之類似的還有如日本、印度等國,而美國盡管立國時間并不長,但其在繼承了以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為主的歐洲文化的基礎上,又在融合中不斷汲取其他文化的養分,如古希臘古羅馬古典神話、中世紀史實文獻和傳說故事等,都是美國史詩電影熱衷表現的對象,也是美國電影在世界電影市場上展開強大攻勢的有力武器。如沃爾夫剛·彼得森的《特洛伊》(Troy
,2004)就來自古希臘的口述文學瑰寶,體現了公元前邁錫尼文明的杰作,又如被譽為“希臘的圣經”的《荷馬史詩》,而梅爾·吉布森的《勇敢的心》(Braveheart
,1995)則取材于金雀花王朝時,蘇格蘭年輕貴族威廉·華萊士爵士反抗“長腳”愛德華對蘇格蘭的殘暴統治的歷史故事。電影的故事本身并不發生在美國本土,但這并不妨礙美國電影通過明星效應、華麗場面等來完成對故事的精心演繹,在歷史畫卷里主人公的愛恨情仇中,潛移默化地傳遞出鼓勵個人奮斗、贊同英雄書寫歷史的美式價值觀。相比之下,中國不僅有著風起云涌的朝代更迭,并且各類文獻浩如煙海、橫貫古今,基本得到了較好的保存,也出現了為數不少的氣勢磅礴、蕩氣回腸的史詩電影。如李翰祥的《西施》(1965)其時代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又如謝晉的《鴉片戰爭》(1997)、馮小寧的《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2012)則將目光對準了近代未有之大變局,講述著中華民族在近代一百余年來中的傷痛。
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史詩電影以其無可置疑的全球票房成績,彰顯了自己在跨文化傳播上的強勢力量。相比之下,中國史詩電影則很少有能夠“走出去”的,甚至在國內市場上常常出現票房失利的尷尬局面。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史詩電影是不具備跨文化討論的意義的。首先,中國史詩電影的產生和創作,往往本身就是跨文化交流的產物。如根據日本歷史小說名家井上靖的名著改編而成的《敦煌》(1988)就是中日合拍的作品,而故事又涉及北宋、西夏、回鶻等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兩國電影人以極其嚴謹的態度,在服裝、道具、布景等方面做到了對歷史的高度還原。與之類似的還有如蕭朗等拍攝的,中國與菲律賓合作,講述大明和蘇祿國兩國交往的《蘇祿國王與中國皇帝》(1987),以及何平的《天地英雄》(2003)等。而在中國國內,史詩電影的創作也有著較為微妙的跨文化交流現象。
在中華文化的同一性下,港臺和內地導演的作品又顯示出了一定的異質性。如魏德圣執導的,由“太陽旗”和“彩虹橋”兩部組成的《賽德克·巴萊》(2011)通過霧社事件讓各地觀眾看到臺灣原住民特有的文化,電影幾乎非臺灣導演不能拍出。而湯曉丹的《傲蕾·一蘭》(1979)也難以想象不出自內地導演之手。又如張徹的《十三太保》(1970)融入了非常典型的港式,尤其是“邵氏”的武俠意味。而隨著港臺和內地電影人的合作日益頻繁,不僅整個文化產業得到繁榮,電影藝術本身也于交流中大為得益。如一直執著于史詩題材的李翰祥的《瀛臺泣血》(1976)在棚內景的有限條件下完成了攝制,而到了得到大陸全面支持的《火燒圓明園》(1983)、《垂簾聽政》(1983)中,故宮實景、內地演員以及內地歷史學者的加入,從硬件和軟件上都為電影更添魅力。其次,進入到21世紀之后,中國史詩電影也同樣向外進行文化輸出,如吳宇森的《赤壁》(2008)、張黎和成龍的《辛亥革命》(2011)等都是借助本國文化資源而加入全球文化資本流動,取得較大影響力的范例。
由此可見,無論中美電影都在進行著跨文化交流,作為各自文化中的構成細胞,電影以一種具有創意的方式實現了本國、本土文化較為穩定的傳承的同時,也在進行著向另一種文化體系的滲透,甚至在這種滲透中存在著再演化和再建構。這就涉及文化本身的“沉重”性和“跨越”導致的理論、實踐上的雙重“拉扯”問題。
二、“文化”之“沉重”
史詩電影與文化之間有著天然聯系。史詩原意為一種長篇敘事體文體或其風格,這種文體的內容主要以民族、國家的發展歷程為主,通常有著事實和虛構的雜糅。敘事內容本身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甚至在個別史詩中,敘事體現出了百科全書式的氣度。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史詩“記載的不是一個行動,而是發生在某一時期內的涉及一個或一些人的所有事件”。在較大的容量下,社會生活、歷史圖景和人物命運等,無不是文化的外化或載體。以羅伯特·道漢的《斯巴達克斯》(Spartacus
,2004)為例,斯巴達克斯被馬克思譽為“偉大的統帥,古代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他在歷代流傳的文獻中逐漸被定型為一個反抗羅馬奴隸寡頭政治的軍事統帥。在道漢的電影之前,庫布里克等也拍攝過關于斯巴達克斯的電影。斯巴達克斯奴隸大軍的壯大、被扼殺的過程,羅馬統治集團之間的內部矛盾等,都一再被展現,美式價值觀中對“自由”的向往不斷被借由斯巴達克斯的起義而宣揚。同時,斯巴達克斯故事中體現的古羅馬文化,以及脫穎而出的英雄在逆境中所表現出來的對信仰、榮譽等的堅持,直接影響了雷德利·斯科特的《角斗士》(Gladiator
,2000)等電影。在《角斗士》中,觀眾所看到的絕不僅僅是鮮血淋漓的角斗士肉搏,還有這背后羅馬人在“民主”問題上的博弈。主人公馬克西姆斯捍衛的除了個人的自由,更是老國王奧里利烏斯等人堅持的共和制,觀眾得以在電影中看到古羅馬的政治文明。缺乏對后者的理解,觀眾就未必能真切感悟到馬克西姆斯人物的悲劇性。與之類似的還有如奧利弗·斯通的《現代啟示錄》(1979)、吉布森的《耶穌受難記》(2004)等。而中國史詩電影在其曲折轉合的影像之中,亦有著這種來自文化的沉重性。如以先秦和秦漢易代為背景的張之亮的《墨攻》(2006)、冼杞然的《西楚霸王》(1994)等。電影中墨子、項羽等人物是特殊時代下的人杰,并且在后世衍生出了大量不同的文化形式中的形象,如戲劇《霸王別姬》中的項羽等。《西楚霸王》中與楚霸王有關的鴻門宴、火燒阿房宮,《垓下歌》“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慨嘆和張良的退隱等,都隱含著復雜的人物信息和史實信息,要求觀眾對歷史有一定的了解。而《墨攻》中墨子的“兼愛”“非攻”思想既和現在的反戰、人道主義思想有一定重合之處,又不可一概而論之,墨子思想的閃耀是與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的。與之類似的還有如蘊含了大量三國文化的李仁港的《見龍卸甲》(2008),與明清易代的文化語境,“忠君愛國”的儒學理想有關的吳子牛的《英雄鄭成功》(2000)、王競的《大明劫》(2013)等。這種文化的沉重性也就導致了最先點燃奧斯卡眼睛的并非史詩電影,而是只摻雜了如山水、道具、功夫等元素,人物全部架空的《臥虎藏龍》這樣的武俠電影。從陳凱歌的《荊軻刺秦王》(1999)到張藝謀的《英雄》,觀眾不難看到,為了實現跨文化交流,電影有時候必須削弱其與歷史的依附性。這也就不得不提及“跨越”中的“拉扯”問題。
三、“跨越”之“拉扯”
電影在跨文化中遭遇的“拉扯”問題,主要表現在保留自身文化個性的同時,又要迎合異質文化與自己的共性之間的矛盾,電影在保留自身史詩標簽決定的嚴謹大氣的同時,又要制造另一文化背景觀眾能接受的賣點。
在“拉扯”中,中美史詩電影擁有一定的共同點。如對愛情、情欲等元素的渲染。弗朗西斯·科波拉的《天與地》(1993)、馮小寧的《嘎達梅林》(2002)、周曉文的《秦頌》(1996)等莫不如此,電影都選擇了讓觀眾在最易認知和共情的兩性關系中完成對電影的接受。
但由于語境的強弱、資本優勢以及電影技術發展程度等差異,兩國史詩電影的“拉扯”又是不同的。美國電影中對歷史原典的改動,更像是一種倚借數字特效等技術和好萊塢品牌對西方古典文明強勢的、主動的闡釋。如蓋·里奇的《亞瑟王:斗獸爭霸》(King
Arthur
:Legend
of
the
Sword
,2017)中給早已被講述過無數次的亞瑟王傳奇加入的魔幻元素。而中國史詩電影則更傾向于是一種對市場以及對政治、民族、宗教等敏感問題進行的綜合性妥協。如在王坪的《止殺令》(2013)、霍建起的《大唐玄奘》(2016)中,就增加的支線人物來看,就有明顯的對明星效應的借重。又如塞夫和麥麗絲的《東歸英雄傳》(Going
East
to
Native
Land
,1993)中邊塞、荒漠等具有異域風情的美麗景觀和游牧民族出身的人物矯捷驚險的打斗,主人公們在飛馳的駿馬上騰挪輾轉;《悲情布魯克》(1995)中夕陽下草原漢子在馬上互相拋擲酒袋,卓拉與車凌熱烈相擁在疾馳的駿馬上的激情戲;蘆葦的《西夏路迢迢》(1997)中特意加入的數名西夏兵在和契丹人的對抗中,為保護漢人的孩子而慘烈喪生的情節等,都試圖在感官和人性層面打動觀眾,不僅絕無美國史詩電影中如《亞歷山大大帝》(2004)、雷德利·斯科特的《天國王朝》(2005)將強權主義、美國中心化價值觀裹挾于故事的敘事,相反盡可能地弱化種族、民族對立,彰顯人和人之間團結、和睦、包容的一面。中美兩國電影都有關注特定歷史時期,刻畫時代巨變,杰出人物的特征,在史詩電影中,電影人們完成著對歷史的當代讀解。但對于兩國而言,史詩電影的創作在有著各自本土優勢的同時,又面臨著要進行跨文化交流的局面。在經濟全球化下,中美史詩電影進入到跨文化傳播領域中,背負著各自文化的沉重分量,表現出了既求同、也存異,既有堅守、也有妥協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