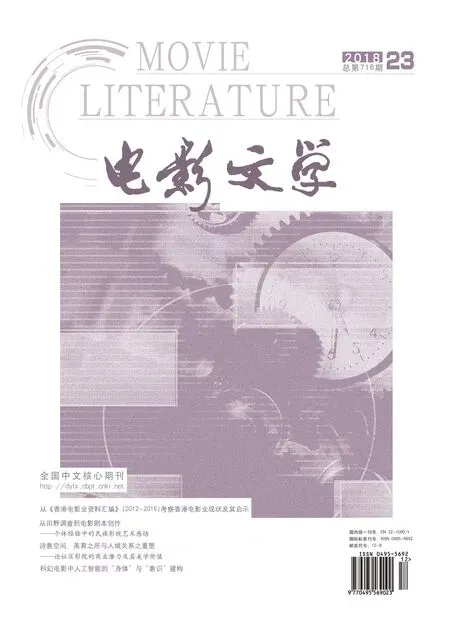《江湖兒女》:情境主義的選擇與哲思
歐陽照 李常昊
(重慶大學 新聞學院,重慶 400000)
新世紀以來,我國電影產業捷報頻傳,不斷攀登票房高峰,從2010年票房首次突破100億元大關到今年《紅海行動》《我不是藥神》《唐人街探案2》票房都超過30億元,與此同時,銀幕數和影院數也在持續上漲,種種跡象都表明中國成為全球最活躍的電影市場之一。縱觀近幾年的國產電影我們可以發現,自張藝謀《十面埋伏》(2006)“牡丹坊擊鼓”之后,出現了包括《滿城盡帶黃金甲》(2006)“血染金甲”、《小時代》(2013)“拜金戀物癖”、《從你的全世界路過》(2016)“山城夜景”等場面大于敘事的景觀電影。這些電影通過放棄部分復雜敘事、提高視覺享受的方式收獲了可觀的票房,似乎也印證了居伊·德波筆下“景觀制造欲望,欲望決定生產。景觀成為決定性力量”景觀社會的深刻影響。
這并非在斥責景觀電影竭澤而漁的功利思想,也不是為了鼓吹實驗性電影佶屈聱牙的深刻內涵。不過,筆者仍然要指出,電影票房蒸蒸日上與敘事結構的轉變很自然地歸結到一個問題上:我們需要怎樣的電影?
一、作為情境的江湖
法國哲學家居伊·德波在《景觀社會》中認為“世界已經被拍攝”。而作為資本物化關系表象的“景觀”更是無處不在,它拒斥對話,遮蔽了社會的本真,極大地影響并且統治著人們。對于電影這種傳播效果極強的藝術形式,更被認為是“景觀”的重要呈現方式,其最大的特征就用視覺景觀呈現代替故事內容敘事,“每一個場景都盡可能讓觀眾感受到打斗的刺激和節奏的緊湊。然而有意思的是,這些牢牢抓住觀眾興奮點的設置都與劇情推進無關,充分調動感官和情緒,卻不觸動內心”。不可否認,“景觀”已經成為國產乃至世界高票房電影中一種新的敘事語境,但我們同樣也需要警惕景觀電影在沖擊高票房并統治著觀眾視線的同時其自身思想價值的流失,借由新奇、刺激“景觀”帶來的票房也會飽和以至消逝。令人欣喜的是,在以賈樟柯為代表的中國第六代導演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一些變化,特別是沒有華麗的景觀、沒有聳人聽聞的故事、沒有植入廣告干擾的《江湖兒女》,僅僅通過貌不驚人的演員以及樸實的敘事手法,呈現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最普通人的生活“情境”。
所謂“情境”則是德波所認為的用于對抗景觀統治的重要手段,即在日常生活中揭露景觀異化的本質,并且指引人們重回真實的生活并且激發人們思考的潛能。“改造社會和日常生活,去征服由景觀所致的冷漠、假象和支離破碎。戰勝被動,才有可能恢復現有的存在,并通過積極的情境創造和技術利用來提高人類生活。”我們可以看到《江湖兒女》無論是立意還是故事內容上都表現出一種對當下“景觀”當道主流語言的反抗,并且從其與情境主義者常用“漂移”“異軌”相同的構境策略來看,《江湖兒女》都為觀眾呈現了一種發人深省的江湖生活“情境”。
(一)撕破表象的漂移
“漂移是對人們現實城市生活驚醒的精神和肉體的雙重反抗。”“漂移”一詞有著濃重的軍事起源,在戰略方面,它指一種通過適當地點的缺陷來決定的有預謀的活動,即對被認為已經成為敵人占領空間的一種進攻。在德波的景觀理論中,“漂移”被引申為對物化且麻木的城市生活的凝固性的批判和否定。特別是對脫離人們生活需求、導致社會關系冷漠的現象進行多角度的批判。而漂移者正是這些時間的親歷者,通過對未知事件和社會的親身體驗,進而呈現問題。簡單來說就是通過日常生活的自身實踐與感知以及和他人或爾虞我詐或真誠相待的交流達到對現實世界的理解。
在《江湖兒女》中巧巧出獄后在各個城市空間中的輾轉、親歷為觀眾奉獻了多次撕破表象、重新認識江湖的過程。在三峽渡船上,吃飯前會虔誠誦經的基督教徒,在禱告結束后悄然偷走了巧巧的錢包;在小鎮,生活優越的成功人士,被“假小三”的拙劣謊言騙得冷汗直流;在火車上,徐崢飾演的科研工作者,貌似對科學有無比的熱情和追求,實質只是新疆偏僻小城的雜貨店店主。江湖生活并不是那么直觀的黑白分明,反而是由有各種欲望和難言之隱的個體組成,沒有闖江湖經歷的巧巧在尋找斌哥的過程中體會到了江湖。也明白了欲望會代替真情,而面對江湖危機沒有更好解決方法的普通人只能順從或者反抗,以自己的方式在復雜的現實中生活下去。她不曾事先了解這些地方,所以她會觀察周邊的環境;她之前沒見過這些人,所以她可能和各種人開始意外的交談,用自己的經驗情緒來定義江湖,也就是情境主義所希望的徹底超越固化、同一的生活束縛。
經過自我解放,人們可以改變權利關系,進而改變社會,這樣的轉變可以說是“漂移”這一行為的歸宿。《江湖兒女》中巧巧出獄后找到斌哥并且放下心中的愛后,失落地搭上火車,原本打算回到大同,但是又短暫地被徐崢扮演的假教授吸引,準備一起去新疆,隨后又因為徐崢對她往事的短暫遲疑,決定在夜里默默離開,并最終在黑色的曠野中認識江湖和自己。對于巧巧而言,在黑色的曠野中已經超脫簡單的“愛情”對她的束縛,有的是賈樟柯為我們描繪的一種忠于自我、平穩內隱的“江湖道義”。
這就是情境主義者所謂的“漂移”,稍縱即逝又漫無目的卻意義非凡。它撕破表象,用充滿哲思的日常生活動搖景觀的統治。而在《江湖兒女》中不僅僅巧巧一人出現了漂移的狀態,斌哥出獄后面對在江湖上完全不同的模式境遇,也選擇了漂移,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開始;“大學生”在告別江湖后,用象征江湖的“關二爺”開始了所謂的企業化管理的公司。不同的是,有的人認清了自己,認清了江湖,比如巧巧;而有的人卻執迷不悟,比如斌哥。但正如德波的《回憶錄》中所言,“漂移者是現代尋找圣杯的圓桌騎士。他們運用自己的激情、行為準則、美德和本領,已經對現代都市主義發動了戰爭”。
(二)魔幻現實的異軌
1956年德波和沃爾曼在《異軌使用方法》中第一次提出異軌的概念。就其概念,簡單來說就是對各種文本、音軌、電影等作品進行無限制的自由使用,通過對各種元素的挪用,使觀眾產生疏離感和震驚的批判性距離,進而使觀眾思考,激發潛能,并且打破景觀現實統治的永恒性的假象。對于異軌而言最基本的規則就是“將最不相關的元素并列在一起,從而創造出不同于原始語境的整體情境”。在德波的景觀理論中相比最歪曲思想的文獻引用,天馬行空的異軌才是激發人們自身思考和潛力的最佳戰略。就像德波在其拍攝的《為薩德疾呼》(1952)中隱喻消失的兒童只有在沉默和夜晚中合適提及的最后24分鐘的黑屏和寂靜,令人在極度詫異中恍然大悟。
《江湖兒女》中,巧巧完成了漫無目的的火車漫游后在大西北一個不知名的黑夜中沉默前行,四周隱隱約約仿佛定格的景物更加反襯出巧巧掙扎式的探索,天邊突然出現了閃爍的白光,接著就是從黑夜中飛過、形象具體鮮明到讓人吃驚的UFO,當然讓人難以忘記還有白光下巧巧那雙帶著釋然和興奮的眼睛。《江湖兒女》本身是一部很嚴肅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但是在這個情節點上“UFO”的出現讓影片多了一分魔幻的色彩,也讓觀眾在突如其來的反差帶來驚詫的同時開始思索自我存在與江湖秩序之間的關系,即再渺小的個體也無須單純地順從江湖或者命運,就像賈樟柯所言“這意味著她在徹底的孤獨感中把握了自己”。這種在黑暗中的頓悟又不禁讓我們聯想起德波的影片《我們一起游蕩在黑夜里,然后被烈火吞噬》(1978),情境主義國際從來就不會有溫和的良夜,只有在高度異軌的反差中才能拒絕一切現實的社會窠臼,“在那個黑暗的夜里去游蕩,如同飄蕩在一個永遠沒有引力、沒有光亮的外太空,一切都在飄浮,同時也被這種飄浮所醞釀出來的火焰所吞噬”。
而片中令人意外的三次鑼聲同樣值得深思。第一次是巧巧在知道公安收繳民間槍械的情況下,依然不惜以進監獄的代價鳴槍救斌哥,在目瞪口呆的安靜之后突然響起鑼聲意味著斌哥式江湖的崩壞以及無可奈何的分別;第二次是巧巧在雨中騎著摩托,毫無征兆的鑼聲漸漸超過雨水的聲音,意味著巧巧仍然不甘心屈服于命運;第三次則是電影結束時斌哥的離開,巧巧坦然而又灑脫地靠著墻,嘈雜的鑼聲伴隨著越來越大的畫面噪點。鑼聲的運用更像是對現實社會的一種異軌式的反映。賈樟柯通過對鑼聲自由的挪用,一方面表達了巧巧在不同階段的人物狀態,更多是在提醒觀眾思索個人生存與江湖規則之間的關系。
《江湖兒女》戛然而止的方式也與德波在《為薩德疾呼》中的結尾不謀而合,其故事內容同樣表現出一種對真我的追尋。現實世界中琳瑯滿目的商品、金碧輝煌的建筑、無所不在的廣告等已經在最大限度地奴役了觀眾,使他們淪入景觀的海洋,喪失了自己的判斷和思考,而唯一可能打破這個無限流動的日常生活鏈條就是“異軌”所帶來的震驚和斷裂。《江湖兒女》中出乎意料的UFO和鑼聲這些讓觀眾感到與常規生活不適應的差異,直接將觀眾帶入對日常生活的質疑之中。也就是在這樣的一些細節和異軌中,引發觀眾對日常生活與江湖道義的深刻思考。
“由一個統一的環境和事件的游戲的集體性組織所具體地精心構建的生活瞬間”,是德波對1958年《情境主義國際》的卷首語中對“構境”的定義。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觀影這個情境而言,并不僅是觀眾對電影影像本身的關注,更多的是觀眾在觀看電影這個過程中的交流與思考。在經過巧巧尋找江湖規則與自身歸宿的漂移以及多種魔幻現實的異軌之后,無論是抱怨的觀眾還是默默思考的觀眾,都在愈加模糊的畫面和近乎轟鳴的鑼聲中,匯聚成一個情境總體。在那一刻,電影播放的重心從銀幕轉向大廳中的每一個觀眾,被景觀所掩蓋的江湖與真實社會倏然間就從畫面中流露出來。疑惑以及無止境的思考成為整部電影的結語,觀眾也因此在這樣的電影中失去了一切生活的常識,重新開始審視這個并不是黑白分明的世界,同時《江湖兒女》的價值也在模糊和噪聲中上升到了巔峰。
二、發現自我的江湖
正如居伊·德波一直刻意避免傳奇、特殊一樣,賈樟柯的電影也將關注的重點放在了平凡人的生活上,正如賈樟柯所言“我一直對神奇的故事有好奇心,但總是傾向于去理解平庸人生,常被平凡人的生命所打動”。與當下大行其道的商業景觀電影相比,《江湖兒女》顯得晦澀而深沉,盡力拒絕一切關于江湖固有的框架,重新刻畫了與《臥虎藏龍》(2000)、《十面埋伏》(2004)等展現俠義精神的中國傳統江湖或《無間道》(2003)、《追龍》(2017)等強調黑白斗爭的港式江湖完全不同的、屬于我們每一個平凡人的江湖形象和規則,同時這也是賈樟柯希望帶給這個社會的深刻反思。
影片中,巧巧最開始對斌哥有的只是樸素單純的愛情,對他的江湖沒有憧憬和認同,不存在江湖中的道義和規則。在第一次巧巧和斌哥的野外散步中,兩人遠望著火山,斌哥握著巧巧的手,教她開槍,并且將槍這種象征著權力和征服的武器作為江湖的標志。隨著斌哥的勢力壯大,巧巧的情也在不惜坐牢也要開槍救斌哥的剎那轉變成了江湖道義。可以看到斌哥的江湖是一種對權威的迷戀,但是這樣依附外在權力之下的江湖注定是脆弱易逝的,所以集市上巧巧一聲槍響斌哥的江湖就分崩離析。然而五年的監獄生活讓斌哥辛苦建立的江湖道義灰飛煙滅但并沒有消磨巧巧心中對斌哥原有的情誼。高峽出平湖、新疆大開發昭示著日月換新天的大變化,經過多番波折,出獄后巧巧在見識過了各種江湖中人才見到了在服刑期間從未探望過她的斌哥。夜色中的相逢顯得格外不安,去除厄運的火盆又仿佛帶著一種諂媚,這一次相見對于巧巧來說是早就明白的一種告別,告別了對斌哥的舊情也告別了他以權力為中心的江湖。當然這也是一個新的開端,巧巧可以坦然離開,開始嘗試接納新事物,開始探索和發現自己。回到大同,巧巧開始重整棋牌室,經營起了屬于她的江湖。多年后當斌哥半身癱瘓前來尋求幫助,巧巧也能毫無保留地接納,而當年開槍的集市、有過爭執的朋友都無法影響巧巧心中江湖的秩序,甚至再次無聲離開斌哥巧巧同樣也能默默接受。在這個江湖中更多的是隨遇而安的坦然和對每個人選擇的尊重,這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經歷的江湖,是貪慕虛榮進而同流合污還是忠于自我,巧巧給出她的回答。經歷了江湖的起伏才能淡然面對人生的風雨,正應了電影的英文標題“Ash is Purest White”(灰燼是最純粹的潔白)。
影片外,《江湖兒女》同樣面對著一個對票房迷戀的電影產業的江湖。無論是國產電影《十面埋伏》《無極》(2005)還是好萊塢系列大片《速度與激情》(2000)、《復仇者聯盟》(2012),都在昭示電影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新趨勢:與其花費時間去追求故事內容上的深刻和對觀眾的啟發,倒不如用炫目的視覺圖像去直接取悅觀眾。但是“因為景觀控制是通過影像投射異化式地偽造了生命欲望,由此重新編碼了人們微觀的日常生活,使人徹底失去潛能”。在這樣的江湖里,電影作為啟迪心智的藝術表達方式徹底淪為人們消遣的玩具,而觀眾更是成為臣服于景觀的奴隸,就像德波警告的那樣,“一切藝術形式都是匆匆過客,應當適時消失,以免落入自己的背面”。而在景觀電影這樣的視覺轉向的背后反映更多的則是復雜的資本涌入。對于站在藝術和商業的十字路口電影產業來說,隨著它成為巨大的利益蛋糕,甚至單純的票房收入已經漸漸不能滿足多方的要求。從全球范圍來看,電影的附屬市場、衍生產品以及廣告都成為繼票房收入之后電影產業的重要支柱,在一些并不賣座的電影中,甚至廣告商成為電影上映的最大支持者,實現電影啟迪心智的最初目的變得難上加難。
與《江湖兒女》中的斌哥和巧巧不同的江湖一樣,從某些角度上來看,如今的電影成為一種經常充滿庸常形式的藝術,它本身同樣在進行著選擇,但這種選擇永遠不會完整。但我們必須意識到的一點是放棄宏大精巧的景觀,并不會妨礙電影成為杰出的藝術作品,反而更容易促進對影片的一般性理解和深刻思索。與其他傳播形式須先承認其偉大才能理解其內涵相比,從最普通的情感出發,才能接觸到最細膩的思想也恰恰正是電影的偉大之處。而賈樟柯也像巧巧一樣在追逐票房的電影江湖中選擇了一種忠于自我的反抗,用《江湖兒女》這樣平凡的故事勾勒了一種深沉的思考,一種極大的情緒波動,一個對票房灑脫有義、對觀眾坦誠有情的新的江湖。
三、結 語
成為景觀的世界要優于真實的世界,精心設計的影像又巧妙地將現實的縮影取代真實的景觀,形成了景觀背后迷惑觀眾的催眠手段。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景觀就不僅是簡單的影像符號的堆積,而是借助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所展現出來的幻象,是所謂的各種復雜資本物化模式的抽象呈現。如今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在生命中的某一時刻,通過環境的集體組織具體而審慎構建出來的“情境”是一種并不尋常的烏托邦,但不可否認,無論德波的情境實踐還是賈樟柯的江湖故事都在激發人們最有價值的擔憂、思考以及潛力。病態的景觀社會采用加大劑量的方式來治療自己的痛楚,而警醒的人只能用越來越深沉的思考創造一種反差和平衡。所以回到最初的問題:我們需要什么樣的電影,《小時代》用紙醉金迷的鏡中生活給出了答案,《唐人街探案2》用33億元票房給出了答案,而賈樟柯也用《江湖兒女》的平凡故事給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