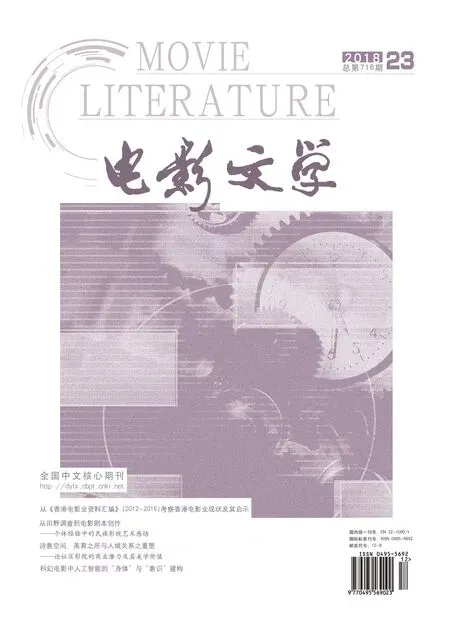信仰:《血戰鋼鋸嶺》戰爭背后的隱喻
周 瑩
(吉林警察學院 繼續教育部,吉林 長春 130117)
《時代周刊》影評說:“無論是否喜歡梅爾·吉布森,你都不能否認他所達到的高度。”是怎樣的高度讓《時代周刊》做出這樣的評價?梅爾·吉布森究竟通過《血戰鋼鋸嶺》向人們傳遞了哪些震撼靈魂的情感呈現方式和對人類命運及靈魂的思考方式?本文將沿著這樣的思考帶您走進梅爾·吉布森對戰爭的記憶、理解、重構與思考。
一、當戰爭與信仰相遇
電影《血戰鋼鋸嶺》從戰爭歷史題材出發,以二戰期間的一場真實的戰斗為背景,以被“珍珠港事件”重創后美國絕地反擊日本的沖繩戰役為載體,全景呈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上傷亡最多的沖繩戰役,承載著難以磨滅的歷史與殘酷的苦難記憶。該影片還原了道斯在沖繩戰場上內心的掙扎與面對信仰與戰爭的勇氣,道斯對信仰的忠誠使他拒絕使用武器,道斯對于國家的忠誠又使他堅定地走上戰場。戰場上,道斯是個拒絕殺戮的醫療兵,他的這種做法遭到同伴和長官們鄙視,認為他是個膽小怯懦、毫無血性的人。然而,道斯卻在血戰鋼鋸嶺的戰斗中,徒手救下了75個戰友的生命,并因此獲得了美國國會榮譽勛章。影片自始至終貫穿著一個主題,那就是道斯是不摸槍的,與煉獄般的戰場上瘋狂殺戮的人們形成了劇烈的對比和反差。道斯對于絕不摸槍、絕不殺人信念的堅守,是對戰爭所打碎了的世界的修補,更是對戰場上的人們靈魂的修補,通過這種修補在拷問心靈的同時更拷問戰爭的本質及歸屬。人們究竟想要在這場戰爭中意欲何為?人們在傷害這個世界的同時,是否也在傷害著自己?究其本質,戰爭需要解決的和信仰所要解決的問題殊途同歸,然而人類大多時候卻選擇極其殘忍的方式解決問題,用毀滅和打碎贏得重生。道斯用不摸槍的選擇,引領人們思考:可不可以有另一種選擇?那些端著槍在戰場上血戰的人們,他們心中也同樣經歷著信仰與戰爭的撕裂,只不過道斯更有勇氣、更加執著,也憑借對信仰的虔誠與堅守,使得一場煉獄般的戰爭有了靈魂的溫度。
那么,當信仰與戰爭相遇時,應該做出怎樣的選擇?影片中兩個場景解答了這一問題:道斯在去救霍威爾的途中遭遇了正在清理戰場的日本士兵,在生死關頭道斯下意識地拿起了槍,爾后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拿起槍的道斯并沒有當作武器射擊日本兵,而是用槍做了一個簡易的擔架,將受傷的霍威爾一路拖行,逃離敵人的追擊;還有一個場景,在道斯安息日的早晨,整裝待發的美軍在鋼鋸嶺下準備再次對日軍發起進攻,按照軍事安排已經錯過了進攻的時間,但是因為道斯對于戰友們來說已經成為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所在,每個人都需要一場有道斯在場的戰斗。因此,在戰場與信仰之間道斯最后選擇了禱告之后與戰友們共赴戰場。影片中多個情節拷問和探尋:如若道斯親見兇殘的敵人用槍指向他的戰友時,他還會堅守信仰拒絕用武器還擊嗎?如果安息日與作戰日相沖突該如何選擇?這些問題導演都用真實的戰爭場景一一進行了回答。影片憑借具有豐富內涵的布局和構思,循序漸進地呈現了閃耀在道斯身上的人性光輝,對信仰的堅守與執著于潤物無聲中造就了道斯的英雄形象。
二、當規則與信仰相遇
主人公道斯出生在美國一個基督信仰濃厚的小鎮,父親是一位一戰老兵,立下很多功勛。然而,戰爭的陰影卻在道斯父親的生命里埋下了撕心裂肺的記憶,生活中時時處處都有可能點燃他內心深處的仇恨、憤怒、暴力及對家人的拳腳相加。年幼的道斯在與哥哥的一次打斗中,一氣之下用一塊磚頭砸向哥哥的腦袋,致使哥哥險些喪命。在親歷了因自己的錯誤造成哥哥于死亡邊緣掙扎的煎熬后,“不可殺人”的戒律從此根植于道斯的內心深處。再加上父親舉起槍對準母親情境的無限放大,道斯從此在靈魂深處向上帝默默許下了一生永不碰槍殺人的誓言。
然而,源自二戰的炮火點燃了道斯內心愛國的情懷,道斯不顧父母的勸說毅然決定參軍到前線去,與剛剛陷入熱戀的女友匆匆告別。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道斯作為一名應征入伍的士兵,竟然拒絕拿槍和拒絕參加任何與槍有關的軍事科目,這使得他受到長官及戰友們的蔑視和嗤之以鼻,大家把他看作是一種恥辱。即便是體能訓練科科優異,道斯仍舊是戰友們口中的笑柄和被排擠的異類,軍隊的長官們想盡辦法將他趕出軍營,甚至以他對抗軍令為由將道斯告上了軍事法庭。這時,道斯的父親這名一戰的老兵出場了,道斯父親舊日老友的一封親筆信令軍事法院撤銷了對道斯的指控,道斯終于如愿以償地奔赴了沖繩戰場。 主人公道斯與戰友們被派遣到鋼鋸嶺攻堅戰中,而之前派去的七個部隊幾乎全線陣亡。道斯作為一名軍隊衛生員,常常是敵軍的首要殲滅目標,但是,手無寸鐵的道斯卻奇跡般地穿越在槍林和彈雨之間,為負傷的士兵急速包裹止血,并給他們注射嗎啡鎮定止痛。面對日軍瘋狂的掃蕩,大部隊準備后撤,就在撤退的懸崖邊,道斯再次向上帝求問:“我該怎么做?”而那些被遺棄在戰場上傷員的呻吟和哀哭,回應了他向神的求問。于是,他轉身奔向戰場,穿梭在尸體遍布的戰地,找尋、搭救,一個、兩個、三個,一共救了75個生命,其中還有兩名日軍。當規則遇上信仰,影片并沒有刻板地將規則捧上神壇,而是用富于理想化的演繹讓規則為信仰讓路,以追尋現實世界難以給予的結局和答案,還觀眾們一個可重構、可超越的世界和靈魂空間。
三、當人性與信仰相遇
尋找戰爭中以及戰爭背后人性的光輝,幾乎是每一部戰爭題材電影所一直追尋的本質所在,《血戰鋼鋸嶺》也不例外。導演梅爾·吉布森在影片中通過一幕幕真實的戰爭場景的還原,向觀眾呈現了血淋淋的戰爭之殤。美軍在第一次進攻鋼鋸嶺之前,已經命令海軍向鋼鋸嶺戰場扔下了上百枚炮彈,按照常理推斷已經幾乎被夷為平地的鋼鋸嶺,日軍一定因遭受了重創而不堪一擊。然而,頑強的日軍卻像幽靈一樣無處不在。剛登上鋼鋸嶺打響戰斗不久,道斯所在的營隊就遭受了重創。這時,導演并沒有將鏡頭過多交給戰爭的整體場景上,而是對準激烈交戰中的美軍和日軍士兵:美軍士兵頭上的鋼盔被子彈穿透、身體被炸得血肉橫飛、腦漿迸裂而出、尸體在爆炸聲中四散而飛、被子彈穿透的鋼盔及迸裂的腦漿、被炸得四散的尸體、血肉橫飛的雙腿;日軍士兵被火槍活活燒死的痛苦、猙獰與慘烈……影片中有一組慢鏡頭尤其值得回味:在激烈的交火中,一個日本兵和一個美國兵同時倒下,相向而死。這組慢鏡頭似乎是在告訴人們:殘酷的戰爭中,沒有贏家。對于戰爭的雙方來說,都將受到身體以及靈魂的雙重傷害,這也是這部影片試圖向人們詮釋的真諦。任何一部戰爭題材的電影所要追尋的意義絕不是描述戰爭本身,而是想讓人們看到戰爭的殘酷性和毀滅性,進而喚醒和引領人類遠離戰爭,追求和平,《血戰鋼鋸嶺》也不例外。
當取得戰爭優勢的美軍以為已攻下鋼鋸嶺的時候,誓死抵抗的日軍瘋狂地反撲,所有的人都撤退了,信仰堅定的道斯卻獨自一人留在了戰場。獨身一人、手無寸鐵的道斯在炮火連天,隨時都有可能遭遇日軍的尸橫遍野的戰場上,絕望而艱難地在一個個彈坑之間匍匐前行,勇敢堅定地確認每一具軀體是否還有存活的跡象,將活著的人用繩子一個個送下山嶺。就這樣,一共救出了75名士兵。撤下山的隊伍在清點人數時發現,全連150名士兵只有32人從戰場上回來了。而道斯一人,就救下了全連一半的生命。這與影片之初,觀眾與片中士兵們面對的那個不拿槍的、可笑的、不可思議的道斯相比,形成巨大的反差。在影片開始有這樣一個場景,在訓練營里,中士在其他士兵面前譏諷道斯:“二等兵道斯不崇尚武力,別指望他在戰場上會救你們!”中士的話不無道理。很多時候,戰場上要殺死敵人,才能救自己的戰友。一個連敵人都殺不了的人,如何依靠他?而道斯卻用孤身一人、徒手救出75位戰友的舉動將觀眾和戰友們徹底折服了。影片試圖引起人們反思,戰爭除了殺戮之外,更大的意義在于救贖。
影片中道斯對于人性及信仰的虔誠,不僅體現在救治自己的戰友上,就連戰場上的“敵人”(日軍)也是他救助的對象。在道斯誤入日軍的坑道的時候,他差點被日軍殺掉。然而,當他面對已經毫無戰斗力的日軍傷兵時,他還是為他充滿呵護地包扎傷口,并將其運下鋼鋸嶺。因此,道斯人性深處的善良不僅代表著一個人,更詮釋著一種信仰。
從打響第一槍開始,電影中的戰爭場面就足以讓人窒息,每一個鏡頭都是如此逼真,每一槍打出來,都能看到肉,每一炮轟出去,都能迸出血。主人公道斯在這種殘酷與冰冷下,卻展現出超出常人的執著與勇氣:在尸橫遍野的戰場上匍匐翻爬,分辨血肉模糊的軀體,把尚有氣息的人拖走,用繩索放到崖下,直到雙手血肉模糊,精疲力竭……雙方士兵像野獸一般相互廝殺,不管身上的血漿和泥濘,只為在恐懼中殺出一條生機,將軍如此,士兵也如此,因為這就是人類的本能反應。而作為虔敬的基督教徒的道斯,他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還能不停地往返戰場,把自己一次又一次放在死亡邊緣,就是希望能從死神的鐮刀下多救一個人。“還能再救一個”,道斯總是對自己這么說著,這早已不是單純靠勇氣就能邁出腳步,而是他拒絕殺戮,熱愛和平的人生信仰,支撐著他在戰場上留下一個又一個義無反顧的腳印,也點亮著永不磨滅的人性光輝。
四、當祖國與信仰相遇
道斯身為一名有著堅定宗教信仰的基督徒,再加之他在工廠工作的實際情況,他本是具備推遲服兵役的資格的,然而在祖國的命運遭遇挑戰時,他仍舊無法抑制心中的愛國熱情和渴望早日奔赴戰場的急迫心情。道斯在家鄉原本有著平靜的工作和感情篤深的女友,他之所以選擇參軍,是因為日軍偷襲了珍珠港,成千上萬的美國青年在愛國熱情的驅使下,幾乎人人產生了參軍的念頭,道斯作為一個熱血沸騰的青年人當然也不例外。這從另一側面勾勒了道斯身上所承載的美國式的英雄主義和無所畏懼的精神,以及每一個美國人身上與生俱來的使命感與榮譽感,這是一個歌頌與憧憬個人英雄主義的國度,更是一個時代,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整體面貌和精神世界。
《血戰鋼鋸嶺》這部影片最后,當道斯被戰友從戰場上救出,用擔架從懸崖上慢慢放下的瞬間,導演用了一個特別華麗的慢鏡頭進行詮釋,受傷的道斯仿佛飄浮在云端,周圍都是光與美籠罩的色彩,仿佛超越了苦難的人間到達天使的世界。影片中關于英雄主義的刻畫不著痕跡,絲毫不見宏大政治敘事格局及背景的勾勒,更不見上天入地、無所不能的大英雄形象,而僅僅是通過小人物作為、細膩的細節布局、人性在生與死之間的真實呈現,將道斯的英雄形象一點一滴地推進和演繹,直至放到最大也是那么自然、水到渠成。
從《拯救大兵瑞恩》《兄弟連》《太平洋》,再到《血戰鋼鋸嶺》,美國式的主旋律影片及其民族英雄主義的呈現模式,一直都通過好萊塢的作品不間斷地得以呈現。影片中沒有聲嘶力竭的口號式的吶喊,卻通過美國大兵們真刀實槍的英勇作戰與瘋狂的、絕命式抵抗的日軍之間的廝殺與較量,血淋淋地詮釋了英雄們本該有的樣子。當日軍碉堡就在面前而無法攻克時,他們一次次攻上去被打下來,又再一次攻上去前赴后繼。影片中,戰場上運回的美國傷兵,他們有的身體已經腐爛和支離破碎,有的血肉模糊失去了雙腿,畫面極度恐懼但沒有一個奔赴戰場的戰士退卻。道斯的一次次重返戰場,在死人堆里匍匐,竭盡全力救回每一個自己的戰友……戰場上的每一個美國人都是那么英勇無畏,這不僅是美國軍人的縮影,更是一個時代全體美國人的縮影。因此,我們不得不盛贊導演梅爾·吉布森的偉大,正是他通過信仰——永恒的力量與歸途,完美地詮釋了美國、美國人、美國式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