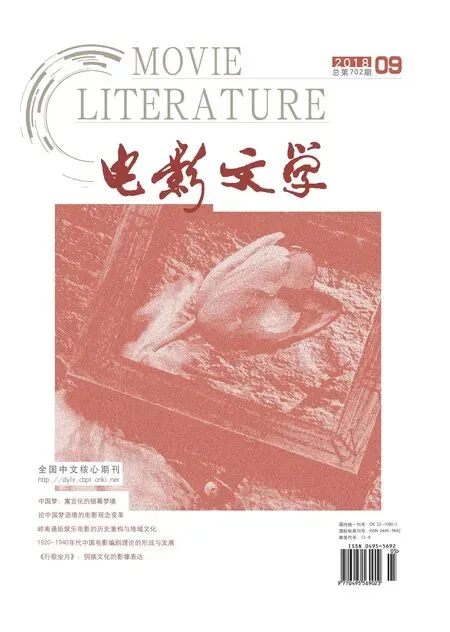當代中國獨立電影的藝術體制
崔劍劍
(中國傳媒大學,北京 100024)
電影誕生的1895年,恰好是現代工業、城市化興起,社會分化加劇的時代,而20世紀接踵而至的經濟危機、世界戰爭、意識形態對立、技術革新、文化沖突及各國內部的權力斗爭等更是直接影響或促發了以此為基礎的哲學、藝術、文化思潮轉向。1911年,從電影理論先驅、意大利人喬治·卡努杜正式宣稱電影為“第七藝術”的那一刻起,電影便作為一種屬性更加雜糅的新興藝術形式匯入現代主義藝術洪流中,也自此奠定了“為藝術而藝術”的純電影理念,而時代藝術的轉變也成為致使電影藝術呈往復、下沉發展的一個維度。
伴隨著工業高速發展所造成的精神物質矛盾、倫理道德失效、理性哲學解構,現代藝術發軔,其表現即是在歐美各國相繼出現先鋒性、現代性的藝術風格和流派,如無調性音樂、意識流小說、達達主義、野獸派繪畫、抽象派繪畫等,就電影而言,尤以20世紀20年代的法國超現實主義、德國表現主義電影為代表。需要指出的是,藝術思潮的迭變并不是完全的替代關系,而會表現為在一定時期內的融合、并存。另外,綜合來看,電影具有相比于其他藝術形式更長的周期性和更強的意識形態性,因此延宕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法國“新浪潮”也同樣是現代藝術。它們秉承現代主義精神,強調自我、純粹原創、曖昧多義,以非常態的方式叩開改造電影藝術的大門。與此同時,二戰后的冷戰格局、精神頹靡、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等也孕育了源于現代主義而又反叛現代主義的后現代藝術的發生,這種反叛表現在“拒絕經典主義藝術的傳統價值和現代主義藝術的自主價值,并且拒絕經典主義意識形態原則與美學原則,拒絕現代主義的形式限定原則與黨派原則”,在電影方面則是以新好萊塢電影,及至后期的《羅拉快跑》《猜火車》《低俗小說》等為代表。
后現代藝術的反權威、去中心等主張正是基于20世紀60年代大眾文化的蔚然成風。科技進步彌合著精英與大眾的鴻溝,驅動著消費社會建構,以波普藝術、觀念藝術等為代表的后現代藝術悄然完成了藝術階層的下沉和藝術格調的置換,安迪·沃霍爾的《布里洛盒子》更是啟發了藝術及藝術品的邊界問題,將藝術理論引向更深層的繁榮。
當陽春白雪式的藝術作品與日常用品難以分辨時,“何為藝術”的問題便被推向高潮。當先鋒派藝術家以反常規、毫無美感的方式挑戰藝術時,以描述方式界定藝術本體的學者們終于將目光投向了從外部限定入手的“何以為藝術”,困囿藝術理論已久的問題似乎就此豁然開朗,由此產生關于“藝術體制”的思考。
一、藝術體制
1964年,分析哲學家阿瑟·丹托率先對此進行了研究,他認為“把某物看作是藝術,需要某種眼睛無法看到的東西——一種藝術理論的氛圍,一種藝術史知識:這就是藝術界”,即某件作品是通過具有審美能力的人闡釋、解讀而變成藝術品。由此可知,成為藝術品,除卻其自身屬性以外,還有三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作品被觀看到、欣賞者的審美鑒賞力、作品與欣賞者共處的時代語境。其中,“語境”意味著作品的闡釋要“合時宜”,當作品與其產生或被解讀的時代思想語境發生錯位時,藝術便會被重塑或消解。比如,《紅樓夢》誕生之初只是普通長篇小說,但經過歷代紅學家的闡釋,它發展為一門跨學科、跨語種、跨流派的學問;“十七年”及“文革”時期對于一切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產品諱莫如深。
“但是,在迪基看來,丹托的藝術定義理論仍然沒有超出傳統藝術定義的范圍,因為它還沒有超越從功能方面來定義藝術”,因而,迪基另辟蹊徑,從程序、體制上定義某物如何獲得藝術品資格。這里的“體制”就包括作品被解讀時代的社會制度、慣例、習俗等。如果說,丹托的“藝術界”理論仍是在形而上學范疇內,那么迪基的“藝術體制”理論就已經溢出哲學而跨入社會學的研究路徑上。
隨后,在兩位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和皮埃爾·布爾迪厄的專門研究下,藝術體制理論愈加清晰。“如果說貝克強調的是作為關系網絡的藝術世界中的合作性,布爾迪厄的藝術場理論則更側重的是藝術世界中的沖突與競爭維度”,從傳播效度來看,顯然布爾迪厄的理論更具影響力。布爾迪厄強調藝術品價值的產生,被認同才會產生價值,繼而才會成為藝術品。受結構主義影響,他試圖構建起一個理論模式,引入“文化資本”“慣習”“位置”等概念來分析藝術場域的內部運作,同時布爾迪厄超越結構主義圈囿的是增加了“權力空間”維度的思考。一個作品獲得認同即是在由觀念、理論、人員、組織、經濟、空間、歷史地點等構成的權力空間中獲得相應的位置。
二、作為文化資本的電影
與其說“藝術體制”理論預示著“藝術的終結”,毋寧說它拷問著“純藝術”,暗示著藝術的相對獨立,這對于商業性、藝術性、科技性、意識形態性并存的電影而言更是如此。電影作為一種文化資本,無時無刻不與經濟資本發生互換。對應布爾迪厄對文化生產場的分析,即“將文化生產場分為兩個次場:有限生產場和大規模生產場。前者即自主的藝術場,后者則是以消費文化為主導的大眾文化生產場,遵循的是他律原則”,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恰好互為補充。作為分支的藝術場域有其自身的運轉法則和資本形式,稀缺性和自主性使藝術作品受到精英階層、知識階層的青睞,而這類掌握話語并具有良好經濟基礎的人群通過品評、展覽、闡釋、再發現的循環,將其合法化、等級化、神圣化,從而造就出一種與眾不同的藝術品,從而賦予它轉換為經濟資本的主要條件。因此,任何形式、任何類型的電影在完形的過程中,都會受到資本的裹挾,此處的資本既可以是經濟的,也可以是機構(組織)的、意識形態的。
比如,新人導演深諳“墻外開花墻內香”之道,他們借助國內外電影節展的平臺主動邁出嶄露頭角的第一步——被看到、被發現,但是悖論也由此產生,自此念頭(“被看到”)產生的那刻起,創作者就不再自我,“藝術品”不再是“為藝術而藝術”,然而從體制論的角度這又是獲得藝術之名的先決條件。繼而,作品在“作為信仰的空間的生產場”里“被有審美素養和能力的公眾”“加以制度化”,“作為偶像的藝術品的價值”從而產生,即電影作品被節展批評家、評審團、贊助人……正名,隨后絡繹不絕的獎金、合作、買斷、投資……即標志著電影完成了一次文化資本變現的行程。
三、當代獨立電影的藝術體制
獨立電影是一個相對概念,隨著電影工業的發展、電影格局的轉變而發生位移。作為電影的一個分支,自電影格局初定時期,獨立電影便已經出現。例如,美國電影業創立初期,旨在打破愛迪生的電影專利公司而成立了獨立電影公司,也就是后來形成新的壟斷的八大公司。只不過,此時的“獨立”主要指主流制作方式以外的電影生產。直到新好萊塢時期,獨立(創作)精神的加入才構建起完整的獨立電影雛形。1985年,羅伯特·雷德福專門為獨立電影的評選而創辦了圣丹斯電影節,隨著該電影節影響的擴大,“獨立電影”概念在美國才逐漸確立下來。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正經歷著最激烈的思想碰撞,“獨立電影”概念很快被引入并吸收,一群在體制內“碌碌無為”的電影人開始自籌資金及設備,拍攝一些帶有濃重個人色彩的影像,1990年吳文光的《流浪北京》和張元的《媽媽》正式開啟中國獨立電影創作浪潮。此后,獨立電影協同中國電影市場改革、產業改革的步伐存續至今,歷經“地下”“邊緣”“第六代”的打磨而呈現出與觀眾、藝術市場自覺的對話性。同時,恪守美學追求、獨立思想、獨立制作也使獨立電影被認為是藝術電影的搖籃之一,以“藝術品”為標準的獨立電影便勢必受到藝術體制的規約。
比格爾曾這樣定義藝術體制,“藝術制度的概念既指生產和分配機制,也指流行于某個特定時期,決定作品接受程度的藝術觀念”,據此,筆者將約束獨立電影發展的藝術機制分為硬性的生產、分配和軟性的觀念三個方面,并具體從制片環境、發行及放映環境、觀念語境對其進行分析。
(一)制片環境
如今的獨立電影已不再是“極小化”的格局,電影票房的激增正刺激著電影行業各個環節的擴容,來自官方、企業、個人的注資為獨立導演的起步提供了更多可能。2010年是中國青年導演計劃的轉折點,這一年,政府給予16名青年導演每人50萬元的拍攝資助,同時,優酷土豆、天畫畫天、光線傳媒、阿里影業、并馳影業及很多中小型電影公司也紛紛推出了自己的青年導演扶持計劃。
就目前而言,獨立電影導演可以獲得資金扶持的途徑有:政府、機構類扶持,如國家廣電總局的“扶持青年優秀電影劇作計劃”;大陸地區節展(活動)類扶持,如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項目創投”;港臺及國外電影節展(活動)類扶持,如鹿特丹電影節“HBF基金”;影視企業、基金類扶持,如華誼“H計劃”;電視臺、視頻網站類扶持,如優酷出品“青年導演扶持計劃”、黑龍江電視臺“百萬電影創投基金”計劃國內的青年導演扶持計劃;名人扶持類,如賈樟柯“添翼計劃”、劉德華“亞洲新星導”計劃、“崔永元·新銳導演計劃”等。其中,來自企業或個人的創投市場試探性、目的性強,資金周轉、機構運營能力存疑,因此多是曇花一現。而無論何種樣式的扶持,都勢必夾雜著評議機構的價值取向和閱評人的審美趣味,進而淹沒絕對的獨立。
另外,從藝術組織的角度,當前的獨立電影人也不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以散兵游勇的方式存在,開始有公司化、正規化的集群組織。除了獨立影人自主追隨大導演,積累拍攝經驗和人脈,或者作者型導演持續角逐電影節積累名氣的方式外,一些民間資本構筑、公司化運營的組織正將有潛質的影人網羅其門下,通過孵化優質作品的途徑做大自身,如藝瑪公司、天畫畫天公司、FIRST影展等。其中,天畫畫天公司開創了獨立電影導演簽約制的扶持策略,2010年該公司簽約了李睿珺、郝杰、楊瑾、彭濤和萬瑪才旦等幾位獨立電影導演,每月為他們繳納社保并提供少量的薪資,這種從商業移植而來的簽約手段使獨立影人獲得基本保障和拍攝資助的同時,自動默許創作上的鉗制。
在人和資本鑄就的隱形圍墻之外,來自管理機構的顯性制片和審查政策著實震蕩著獨立電影制片的整體走向。“南方談話”后的電影市場復蘇帶動著制片改革的持續松弛和升級。1995年《關于改革故事影片攝制管理工作的規定》頒布,拍片權下放至省級以下各地區的相關部門各制片單位,打破了原有的國務院審批制度。1997年,全國第一家電影國有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獲批組建。2000年,由國家廣電部、文化部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深化電影業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積極推行院線制……逐步建立以院線為主的供片機制,通過競爭活躍電影市場,促進影片收入在制片、發行、放映三個環節上的合理分配”等,標志著中國電影改革開始全面提速。2002年起施行的《電影管理條例》賦予民營影視文化公司獨立完成影片制作的權力,一大批,如保利博納、華誼兄弟等巨頭民營電影公司崛起,中國電影也由此進入井噴式發展階段。
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電影審查制度改革進展緩慢。1994年3月,廣電部批文《關于不得支持、協助張元等人拍攝影視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對田壯壯、張元、王小帥、吳文光、何建軍、寧岱、王光利七人私自參加國外影展的行為予以懲罰,自此,獨立電影便繞不開“禁片”的命運。1995年,路學長的《長大成人》、王小帥的《扁擔姑娘》、王朔的《爸爸》與黃健中的《大鴻米店》因“需要修改”相繼被擱置,一些導演拒絕修改或放棄等待修改意見,其作品便最終未能獲得合法的放映渠道,只有《長大成人》在1998年獲得公映。隨后,“第六代導演”中的大多數都遭遇了被禁,直到2003年獲得解禁,并且隨著同年頒布的《電影劇本(梗概)立項、電影片審查暫行規定》,獨立電影也被納入體制內。
然而,政治解禁的獨立電影馬上又變成市場經濟中的地下電影。在之后的數年中受到來自市場的新的“專制”。然而,即使是像賈樟柯這樣最典型的、國內最具影響力的獨立電影導演也承認,“我們都不是市場的敵人,自由經濟是諸多自由夢中的一種,我們沒有什么好抱怨的,雖然知道市場有時候會跟權力勾肩搭背,但我們也愿意擁抱市場,并為此付出全部的精力和財力”。如果說,獨立電影前輩對于審查、市場的妥協還頗具一絲無奈,那么晚近的青年導演對此則更加溫和、樂觀,他們認為,“至于(中國電影的審查制度,筆者加)會不會扼殺導演的思維以及創作自由,我覺得不會。睡不著覺不能怪床小……全世界各地的電影創作環境來說,也都各有各的困難和局限性,看你怎樣去適應。像伊朗這樣嚴苛的審查制度下也能誕生像阿巴斯一樣偉大的導演”。國內的制片、審查制度和獨立電影導演正在發生彼此漸近的和解。
(二)發行放映環境
1993年,廣電部正式頒布《關于當前深化電影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及其《實施細則》,電影發行權自此下放到省級公司,1994年,《關于進一步深化行業機制改革的通知》又解綁了各制片廠的發行權。此后,隨著每一次電影業改革的深化,電影發行機制基本都會做出相應調整,然而,這一切并未與回歸體制前的獨立電影發生關系。隨著獨立電影與體制、市場的和解,其宣發渠道從過去單一的“朝外看”而逐漸多元。但受制于資金和人員問題,獨立電影團隊通常并不能夠獨立完成硬廣投放、線下活動、衍生品開發等,其線下宣發還是主要依靠國內外的電影節或獨立影像節展。而獨立宣發方面則主要依靠以互聯網為載體的新媒體平臺,如視頻網站、APP、票務平臺(格瓦拉等)、社交平臺(微博、微信、豆瓣等)。值得一提的是,業內早已關注到獨立電影的價值和能量,并且意識到缺乏專業獨立制片人的現狀,因此許多知名的商業或獨立電影導演會自覺挖掘并推廣優秀的獨立電影,如爾冬升擔任《提著心吊著膽》的監制,萬瑪才旦擔任《清水里的刀子》的監制、《太陽總在左邊》的藝術指導。
然而,獨立電影始終是小眾藝術,在全國藝術院線聯盟成立之前,獨立電影曾以DVD的形式流傳于“地下”,也曾以點映、展播的方式出現在一、二線城市的部分電影院、電影沙龍或電影節展上。此后,在中國電影市場的繁榮、電影產業結構逐步完善的驅動下,獨立電影放映平臺、體系也逐漸擴容。以創建于2006年的FIRST青年影展為例,它一方面效仿歐美藝術電影節展,建構藝術電影標準,支援青年影人發聲;另一方面創設作品與資方接洽平臺,以全國巡展的方式培養影迷文化。FIRST的“主動放映”(全國巡展)讓精神生活寡淡而又向往文藝的二、三四線城市青年有了規律、合法的觀影渠道,在各高校學生團隊的依托下,產生了在大學的教室、報告廳、禮堂以及后續開發的書店、青旅、咖啡廳等場所的多元化放映形態。同時,它又分為春季巡展和冬季巡展,從2013年起,“主動放映”的展映場次和觀影人數都在逐年增長,到2016年,僅春季巡展就已經延伸至101所高校和機構,共計放映305場。并且,春季巡展完全是在自發組成的學生志愿者和電影愛好者團隊的籌劃下進行,因而就會篩選、組建一個具有凝聚力、吸引力、自主性的影迷群體,并在年輕一代中培養起美的、藝術的、電影的影迷文化。除此之外,還有鳳毛麟角的獨立電影得以登陸主流院線,但相比于主流電影及主旋律電影所占據的宣傳、放映資源,獨立電影在排片、受眾、反饋等方面都顯得局限。
(三)觀念語境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藝術思潮、人文思想從全盤蘇化漸而西化,中國獨立電影的流變即可以看作是西方藝術變遷的縮影。藝術發展至當代,受到趨于穩定的政治、社會局勢和甚囂塵上的消費文化帶動,而對抗性變弱,它制作精良、工藝精湛,時常以極簡、轉喻、反問的方式反復琢磨受眾的口味,從而確定藝術場中各方占據的位置。因此中國當代獨立電影的和解姿態其實是藝術界集體無意識的外露。
此外,電影的藝術教育、藝術學科發展、建設也在影響著關于獨立電影的觀念塑形。北京電影學院是我國成立最早、體系最完備的電影專才培養機構,并且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占據著寡頭地位,至今也仍是電影新力量的主要輸出地之一,大部分獨立電影導演,尤其是早期的20世紀90年代,都有“北電”學習經歷。但是最早的“電影教育不是專業教育,是精英教育……(未來要成為大師的)教育體系使中國導演在很長時間內完全跟工業結構不融合”。但是,隨著電影市場化改革進程的深入,電影專業院校及時調整思路,細化教育結構,全國各高校,不僅是省屬藝術類院校,還包括綜合類大學的相關院校、美術類院校、高職類院校也紛紛開辦影視類相關專業,因而沖淡了電影、電視、戲劇、動畫等的藝術邊界,打破了電影教育一家獨大的局面。學院派的教學風格使學生能夠掌握影視創作的基本素養和技能,但由于各高校學科底色、人才培養方案、學生素質相異,對學、產銜接的理解和實踐深度不同,最終并不能對學生的個性發展、電影觀念一言蔽之。顯見的是,院校專業性的程度與優秀獨立電影的產出成正比。
通常,評價一部獨立電影價值的標準大致有:是否參加過國際、國內的重要節展;是否獲得重要電影期刊、平臺、影評人的推介;被放映的頻次、范圍;是否獲得具有電影素養的公眾認可;是否被重要的藝術電影公司賞識等。也就是說,由專業影人、影評人和一般觀眾構成的電影評論中介對獨立電影創作者及其作品的價值建構有著直接影響。參照法國電影的藝術等級體制,我國的獨立電影標準主要受具有影響力的電影節展、學術批評和電影期刊,基于互聯網的職業影評人、選片人、電影網站和影迷的觀念影響。以電影節展為例,風格、賽制和評審人的主觀意愿使評選結果,即藝術標準,既有通約性,更具隨機性。比如,鹿特丹電影節極為“左派”“叛逆”“實驗”,宣揚個人主義,與此相比,戛納、柏林、威尼斯電影節似乎都有些保守、主流,但就歐洲三大電影節而言,獎項的歸屬依賴于評委個人的審美趣味與傾向,主流中又有些“隨意”。
鑒于獨立電影受到的藝術體制規約,史蒂文·索德伯格(《性、謊言和錄像帶》的導演)斷言,獨立電影運動已經不復存在。于是他轉變了風格,與主流共生。賈樟柯、王小帥、寧浩、張楊……這些中國獨立電影先驅也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有人說他們是被商業邏輯收編,但從時代文化藝術流動、國內電影產業發展現狀分析,筆者更愿意相信這是順勢而為、迂回戰略。獨立電影與“權力”、觀眾對話、共生已經是當前的最優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