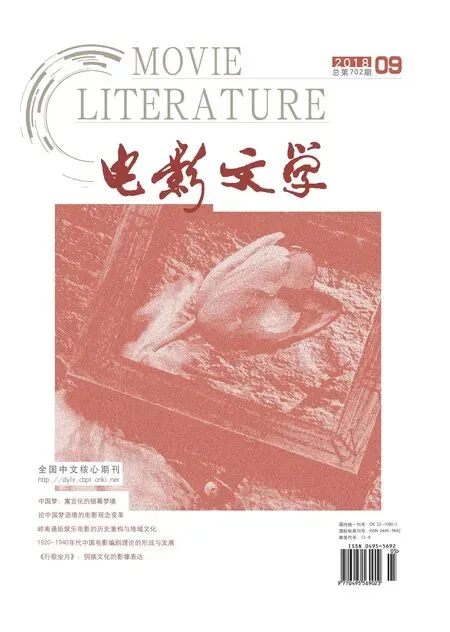華語同性戀電影作品的創作與傳播流變
譚 力
(江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欽州學院 人文學院,廣西 欽州 535011)
一、前 言
由于受傳統婚戀觀念以及孝文化的影響和沖擊,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一提及同性戀這個詞語,很多人通常會聯想起“變態”和“流氓”。同性戀群體受到社會主流群體的排擠和抨擊,不得不保持低調,長期游走于社會的邊緣。因此,以同性戀為題材的電影也游走于社會的邊緣,無法進入大眾視野。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經濟的發展、互聯網的出現以及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大眾對多元文化有了更大的需求與渴望,同性戀電影漸漸成為大眾了解、接近同性戀群體的一條全新路徑。特別是在傳統觀念根深蒂固、文化環境相對封閉的我國,華語同性戀電影已經逐步開辟出屬于自己的發展之路——從最初的默默無聞到小眾的熟知,再到進入大眾視野持續吸引人們的關注。可以說,華語同性戀電影經歷了從“失語”到“隱語”的傳播流變,在電影領域顯現出其獨特的藝術水準和審美價值。
二、失語:華語同性戀電影禁忌時期的表征
同性戀自古有之,只不過稱謂不一罷了。回顧中國古代歷史不難發現,從春秋戰國時代的“余桃”到唐代“男妓”的出現再到清朝的“私寓”制度,同性戀者一直存在卻一直未能真正為主流社會所包容。相較于西方發達國家,中國的同性戀題材的電影起步較晚。華語同性戀電影的出現與發展,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從最初的小眾到現在的流行,已發展將近50個年頭。
回顧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華語電影可以發現,大多數影片是以贊揚革命斗爭精神和歌頌美好新生活為主題的,以同性戀為題材的電影基本沒有。雖然有那么幾部電影出現了同性戀元素,但也是以曖昧為主的躲躲閃閃、點到即止。例如,1934年孫瑜導演的電影《大陸》中出現了女孩親吻擁抱,1972年邵氏電影公司出品的電影《愛奴》中的春姨對“愛奴”的愛戀,1974年上映的影片《面具》中提及的歌手盧綸和林偉賓等,都或多或少地隱含了同性戀文本,向大眾暗示了同性戀元素。但是這些影片均來自港臺地區,我國內地幾乎沒有出現過暗含同性戀元素的影片,這一現象后來被影評人稱之為“失語”現象。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一方面是受傳統婚戀觀念和孝文化的沖擊,特別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無論是在道德方面還是法律方面,都缺乏對同性戀的正確認識,每每談同性戀則色變,對同性戀的關注也就少之又少。另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電影審查制度過于嚴格,一部影片的上映需要經過層層把關,而電影審查者的態度是受當時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文化影響的,因此同性戀被視為一種社會丑惡現象,不能大肆宣揚。總的來說,90年代之前的同性戀電影在華語電影界仍是一個無人問津的“禁區”,固然有提及同性戀的少數幾部電影,但人們對同性戀電影和同性戀人群還只是處于相當初級的認知階段,并沒有深刻的認同感和人文關懷,更別提去接受和喜愛了。
三、打破禁忌:華語同性戀電影“破冰”時期的特殊表達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大眾開始逐漸接受并欣賞華語同性戀題材的電影,很多作品質量上乘,屢次獲獎。例如,李安的《喜宴》以及關錦鵬的《愈快樂愈墮落》等,將同性戀電影的知名度提升了很多。這說明同性戀題材電影借助獲獎之后的媒體報道,以一種開放的姿態進入大眾視野,而觀眾也開始慢慢敞開懷抱接受它。與20世紀70年代的同性戀影片相比,這一階段的影片有了較大的改觀,但是仍存在著一些局限性,比如,影片并沒有直面同性戀這一主題,也沒有在影片敘事中直接呈現同性戀情節;而是將同性戀情節“化整為零”,巧妙地隱藏在故事主線的背后。嚴格來說,這并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同性戀影片,但它展現的藝術風采依舊讓人折服——獲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的影片《霸王別姬》和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的《喜宴》均是如此。這種變化和進步主要得益于三個原因:
第一,從歷史比較的視角來看,華語同性戀電影的產生和發展要晚于西方其他國家。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酷兒理論流入中國,創作者與受眾的思維都得到空前解放,這為中國同性戀電影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第二,1997年我國施行的新《刑法》中,刪除了過去常被用于懲處某些同性戀行為的“流氓罪”。作為同性戀非刑法化的一個重要信號,這對受眾重新認知同性戀群體產生了重要影響,繼而對衍生出來的影視文化產品產生了高于以往的接受程度。
第三,電影分級制度的出現也為同性戀電影這一敏感題材的電影創作提供了相對寬松的創作環境。特別是在香港地區,將影片劃分為四個等級,受眾觀影的選擇性得以被滿足,也使得受眾的需求變得更加多元化。
四、狂歡:多元文化背景下華語同性戀電影的商業化
進入互聯網時代,媒介的發展帶來的是文化的多元。正如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的早期預言“媒介即信息”,每一種新媒介的產生都開創了社會生活和社會行為的新方式。著名傳播學者伊尼斯也曾有過一句名言:“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誕生。”由此可見,網絡及新媒體的發展創造了一種新的媒介尺度,使得原本只能在角落里孤芳自賞的華語同性戀電影獲得了一個絕佳的平臺。而這個平臺甚至有一段時間幾乎沒有接受太嚴格的監管,于是大量的同性戀電影在網絡、新媒體平臺上出現,形成了一場不同尋常的“狂歡”。在土豆、優酷、愛奇藝等視頻網站上隨處可見大量同性戀微電影和自制長篇電影,這些影片的點擊量曾一度超越以往某些傳統院線電影的票房影響力,使得傳統院線也來小范圍參與發行、傳播該類影片。例如,2014年9月24日,北京UME國際影城(安貞店)為同志題材電影《類似愛情》舉辦了首映活動。《類似愛情》首映活動的成功舉辦標志著網絡電影也取得了與傳統院線放映相同的商業效果。從當晚的入場情況來看,人頭攢動,甚至要出動安保人員來維持現場秩序,這也說明華語同性戀電影其實是有著巨大潛在市場的。這種“影院點映”模式對探索華語同志電影的未來發展道路具有積極意義——如今互聯網技術日益發達,互聯網、電視、手機等現代化傳播媒介日益融合,我們應當正視華語同性戀電影的“融媒體傳播”,并深刻探討這種“狂歡”形成的機制與問題。
除了傳播方式由小眾走向了商業化,這一時期的華語同性戀電影在內容上也漸漸偏向了主流市場,與一些商業化色彩較強的影片題材產生了融合。
(一)與幽默喜劇的完美融合
隨著華語同性戀電影的日益發展,以敘事內容為主導的創作傾向在華語同性戀電影中越來越明顯。沒有奪人眼球的片名,沒有嘩眾取寵的噱頭,同性戀群體被書寫成為社會普通成員,極其自然又積極地呈現在影片中。在此類影片中,沒有人刻意地強調性別取向,而是輕松地以真實狀態融入故事主線,展開故事情節。臺灣電影《十七歲的天空》就實現了同性戀題材與搞笑幽默喜劇的完美融合,一掃之前同性戀電影的悲劇、灰暗的色彩,在當時引起轟動。隨后出品的影片《下午茶》也融入了喜劇的因素,淡化了同性戀電影的悲劇色彩,使大眾在歡聲笑語中了解同性戀這一群體。
(二)與青春校園劇的完美融合
進入21世紀以來,青春校園劇盛行。關錦鵬的《藍宇》、陳正道的《盛夏光年》等同性戀影片實現了與青春校園劇的完美融合。這些影片通過講述發生在學生時代的一些簡單純真的小故事,吸引著大眾的眼球。此類影片中對同性戀的表現總是淺嘗輒止或者是隱而不發,沒有濃烈的情欲色彩,有的只是真情流露和美好的學生時代的回憶,從而贏得大眾的喜愛。
五、隱語:華語同性戀電影創作與傳播的生存之道
“孤單是一個人的狂歡,狂歡則是一群人的孤單。”看似熱鬧的華語同性戀電影其實并沒有真正成為主流電影的分支,其創作與傳播依舊面臨著眾多的困境。在內容生產與影片創作方面,盡管華語同性戀電影已經逐步開辟出屬于自己的發展之路,從小眾變得慢慢流行起來。但是與主流電影相比,同性戀電影的創作仍然處于閉門造車的狀態。除了部分在網絡視頻網站“原生態”制作并發行的所謂同志影片以一種高調的姿態發行之外,其實主流影片市場中的很多類型片,依舊以一種“隱語”的方式在完成著同性戀文本的創作表達。“隱語”的本意是人與人交流的另外一種方式,是個別社會集團或秘密組織內部人懂得并使用的特殊用語。在此,可以把其理解為“一種隱晦的電影敘事語言”。與網絡上的狂歡不同的是,主流電影一直以隱忍的姿態、隱語的方式在進行創作。一方面,出現了《春光乍泄》《美少年之戀》《藍宇》《刺青》《蝴蝶》等純粹的華語同性戀影片;另一方面,很多主流影片以隱語的方式在體現著同性戀元素,進行著同性戀敘事。如在陳凱歌執導的影片《霸王別姬》中主角程蝶衣命運多舛,原因之一就是其同性戀取向。不過這種取向被時代背景和人物設定所掩蓋,觀影時受眾并未反感。但克制的鏡頭語言仍產生了巨大的藝術效果,其同性戀元素的比重也高于以往的影片。有一些商業電影則以同性戀元素作為搞笑的手段之一,使影片散發出愉快的氣氛,增添了不一樣的魅力。如古天樂和成龍就在電影《寶貝計劃》中成功地以此博得了大家的歡笑;還有《東成西就》中梁家輝的角色、《金枝玉葉》中曾志偉的角色等,其中暗含的同性戀元素均被改裝成逗樂觀眾的戲謔手段,在快節奏的情節發展中笑料百出,使同性戀元素成為影片的娛樂調味劑。
與此同時,我國互聯網的管理和治理也走上正軌——一系列管理條例的出臺,使得對網絡視頻網站的監管成為常態,曾經在互聯網上“圈粉無數”的同性戀影片也面對調整和轉型。2017年上半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印發通知,對網絡視聽節目的創作播出提出進一步要求。通知強調,“……堅持網絡視聽節目與廣播電視節目同一標準,未通過審查的電視劇、電影,不得作為網絡劇、網絡電影上網播出……”這一通知對網絡視聽節目的審查標準做出了解釋,以往在主流傳統媒體無法播出的內容在網絡平臺也不得播出。因此,一大批影視作品只能刪減、修改甚至重新制作直至通過審查后才能播出。這種相對嚴格的管理和審查制度,也使得未來在網絡平臺播出的華語同性戀影視作品,必須得以隱語的方式去表達,以特定群體內的話語體系去敘事才可以生存和發展。如愛奇藝網絡劇《決對爭鋒》改編自網絡小說《爭鋒對決》,原著是一部同性戀小說,在改編時為了通過審查已經調整成為一部商業諜戰片;但影片中很多主角之間的臺詞和互動依舊“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地隱約指向了同性之愛。這種含蓄的表述、隱語的呈現只有特殊受眾群體可以體會,但這也并不妨礙普通觀眾把它當作一部正常的商業諜戰片來進行觀賞。
其實,無論是主動調整還是被動整改,都是當下華語同性戀電影創作與傳播要面臨的,前進的道路依舊需要不斷地探索。
六、結 語
總之,華語同性戀電影在經歷了“失語”“小眾”“狂歡”等階段的表達樣式之后,以“隱語”的姿態進行創作和傳播,既不悖逆主流觀眾的審美趣味,又可以被主流意識形態所接受,更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受眾、擴大影響力。它所展現的藝術美感和情感力量成為華語電影的獨特話語,并以特殊的創作與傳播方式為邊緣題材的電影作品找到了一條通向成熟的解救之路,爭取到了更自由開闊的創作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