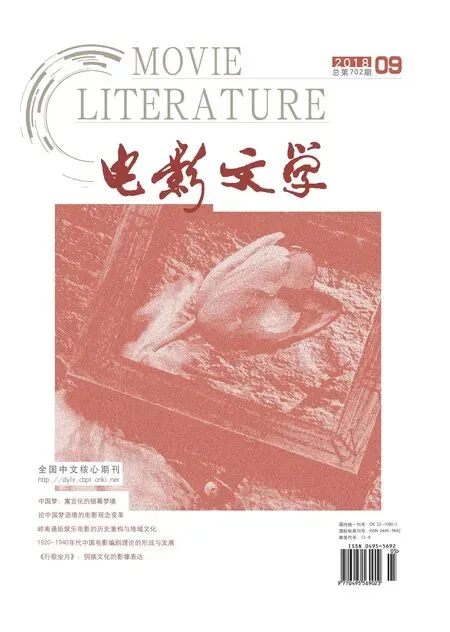尼基塔·米哈爾科夫導演藝術研究
李 茜
(綏化學院 外國語學院,黑龍江 綏化 152000)
俄羅斯導演尼基塔·米哈爾科夫·謝爾蓋耶維奇在俄羅斯電影界,乃至世界電影界都有著重要的地位,被人們稱為“俄羅斯的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在多年的藝術探索中,米哈爾科夫已經(jīng)形成了一定的美學風格和與俄羅斯話語環(huán)境息息相關的藝術思想,被認為是新俄羅斯電影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對米哈爾科夫的導演藝術,我們完全有進行深入探索的必要,這不僅在于其個人的藝術實踐本身就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米哈爾科夫也是我們接近全球化語境之下的俄羅斯電影的一把鑰匙。
一、米哈爾科夫的電影之路與創(chuàng)作背景
米哈爾科夫出身于俄羅斯著名藝術世家,其父母均為作家,曾外祖父則為俄羅斯著名畫家,年長其8歲的哥哥米哈爾科夫·安德烈也進入了蘇聯(lián)國立電影學院學習電影拍攝。在安德烈的一次年級作業(yè)中,14歲的米哈爾科夫臨時幫哥哥安德烈扮演了一個女性角色,從此與電影圈結緣。在考入了史楚金戲劇學校和蘇聯(lián)國立電影學院前后一段時間之內(nèi),米哈爾科夫對自己的定位一直都是一名演員,也正是因為自己執(zhí)意在上學期間拍戲,他才會被史楚金戲劇學校終止學業(yè),轉而到蘇聯(lián)國立電影學院就讀。也正是這次轉學,米哈爾科夫得以進入導演系學習,雖然此后也還擔任演員,但他已經(jīng)得以更近一步地接近導演這一身份。從蘇聯(lián)國立電影學院畢業(yè)后,米哈爾科夫就在莫斯科電影制片廠獲得了執(zhí)導筒的資格,拍攝了《敵中有我,我中有敵》(1974)、《愛情的奴隸》(1976)等具有濃郁“蘇氏”意味的影片。在此后的十年中,米哈爾科夫的影片幾乎都由莫斯科電影制片廠出品,盡管當時蘇聯(lián)的電影制片體制對于米哈爾科夫來說多少存在束縛,但是他盡可能地在體制內(nèi)進行多種嘗試,包括嘗試拍攝各種類型片,嘗試反映各類題材,嘗試對著名小說進行改編,建立起風格化的,觀眾又喜聞樂見的電影語言等,從而全面地發(fā)展了自身的能力,并且他這種對觀眾觀感的重視,也為自己后來能夠兼顧影片的藝術性與商業(yè)性奠定了基礎。在蘇聯(lián)解體之前,米哈爾科夫脫離莫斯科電影制片廠建立了自己的電影公司:3T公司,加上外部的社會原因,米哈爾科夫一下獲得了空前的創(chuàng)作自由。此后,他如魚得水,大放異彩,其最為知名的影片如《西伯利亞的理發(fā)師》(1998)、《十二怒漢:大審判》(2007)等便誕生在這一時期。
而要對米哈爾科夫進行較為全面的了解,不得不提及米哈爾科夫進行創(chuàng)作的大背景。米哈爾科夫身處的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處于一種較為復雜的境地,一方面全球化已經(jīng)不僅是各國進行文化交流的背景,甚至已經(jīng)成為某種動力。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則無疑因為經(jīng)濟、科技等方面的壓倒性實力而掌握著文化輸出的強勢力量,而被輸出者的本土文化和民族意識、價值觀等都面臨著沖擊與威脅;另一方面,蘇聯(lián)解體導致俄羅斯民眾在文化的接受和需求上更為多元,整個俄羅斯文化界在某種程度上被動地被全球市場所滲透,電影界也不得不迎來好萊塢電影等大量外國電影的涌入和競爭,這種競爭并不僅僅是藝術理念上的,還包括了一套價值觀、行為方式等意識形態(tài)內(nèi)容。如果此時俄羅斯沒有優(yōu)秀的本土電影人脫穎而出,那么觀眾和資本的流失,本土電影質量的一落千丈將是不可規(guī)避的結果。可以說,在這樣的背景下,米哈爾科夫成為一個經(jīng)歷了蘇聯(lián)時代和俄羅斯時代的人,時代的碰撞對于他來說既是挑戰(zhàn),也是機遇,接受著標準的蘇聯(lián)藝術熏陶成長起來的米哈爾科夫深諳已經(jīng)輝煌不再的“蘇氏”話語的優(yōu)點與局限性,也敏銳地意識到了什么是暫時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觀眾想要的,什么是自己想表達的,于是他選擇了“人”(不僅僅是俄羅斯人)這一點來作為溝通新與舊,俄羅斯與世界,自己與觀眾的橋梁。他的電影也因為總是蘊含著全人類共同的人文話語與一定的俄羅斯民族性,而受到了普遍的認可。與米哈爾科夫同時代的俄羅斯導演們,并不都能如他一般,既積極地擁抱西方、擁抱世界(如米哈爾科夫曾經(jīng)公開表示自己將奧斯卡作為衡量自己是否成功的標志),又能對本民族在政治風云變幻下的社會生活有著如此精妙的捕捉,并像他一樣擁有常常身兼導演、編劇二職于一身的全才,他也就得以扛起了當代俄羅斯電影的大旗。
二、米哈爾科夫電影的藝術特征
從外部形態(tài)來看,米哈爾科夫電影無論是在敘事模式,抑或是具體的視聽語言上,都有著其非常明確的、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追求。
首先就敘事模式來看,米哈爾科夫電影最大的特征就是追求情節(jié)性。情節(jié)性在一個觀眾呼喚娛樂的時代可以說是極為重要的。如前所述,從莫斯科電影制片廠成長起來的米哈爾科夫深知老蘇聯(lián)電影以及在蘇聯(lián)電影之前的沙俄時代電影的特征。尤其是蘇聯(lián)電影創(chuàng)造的紅色經(jīng)典敘事模式,對于米哈爾科夫來說更是再熟悉不過。在新的時代,米哈爾科夫選擇對其揚長避短,即去掉紅色經(jīng)典之中的革命話語,并且克服蘇聯(lián)、沙俄電影受俄羅斯文學影響而產(chǎn)生的重抒寫和哲思、輕敘事的弱點,但是保留紅色經(jīng)典敘事中的大規(guī)模、大氣勢,更重要的是,米哈爾科夫在充分地挖掘了好萊塢電影的敘事策略之后,將情節(jié)性置于電影的重中之重。其實在早年的“像旋風一樣闖入驚險片的行列”的《敵中有我,我中有敵》《愛情的奴隸》這樣的所謂紅色影片中,米哈爾科夫就已經(jīng)顯示出了重懸念的特征,電影吸引觀眾的往往不是英雄主義激情,而是米哈爾科夫精妙編織在電影中的令人緊張的懸疑情節(jié)。在后來的影片中,米哈爾科夫更是高度重視設計尖銳的、充滿趣味或震撼性的戲劇沖突。以有“俄羅斯的《泰坦尼克號》”之稱的《西伯利亞的理發(fā)師》為例,正如《泰坦尼克號》的巧妙之處在于讓兩個地位懸殊的青年男女的愛情故事,發(fā)生于生離死別的船難之中,《西伯利亞的理發(fā)師》也將一個肝腸寸斷的愛情故事置于沙皇統(tǒng)治的俄羅斯帝國的背景下,尤其是寒冷、荒涼的流放地西伯利亞更是使得影片本身就具有與死亡掛鉤的悲劇感。男女主人公一個是俄羅斯青年士官,一個是美國的美貌寡婦,兩人相愛、錯過、分別。男主人公安德烈對于尊嚴的維護具有一種光芒萬丈的古典式的崇高意味,為此而被發(fā)配到西伯利亞,與《泰坦尼克號》中杰克的為愛獻身是類似的。而《西伯利亞的理發(fā)師》中以伐木機“西伯利亞的理發(fā)師”對白樺林的砍伐,暗示美國、歐洲對俄羅斯的咄咄逼人,也與《泰坦尼克號》中隱含的歐洲的沒落、美國的興起相似,令人嗟嘆不已,回味無窮。
其次,在視聽語言上,米哈爾科夫被譽為一位“修辭大師”,其對于用聲畫來進行言說,給予觀眾審美愉悅方面,無疑有著較高的造詣。例如,在《愛情的奴隸》中,米哈爾科夫采用的是一種“戲中戲”的敘事方式,“愛情的奴隸”本身就是電影中沙俄的電影攝制組拍攝的影片的名稱,而在戲外,女演員沃茲涅先斯卡婭和身為紅軍地下黨的攝影師波托茨基兩個人相愛但立場有別,后來沃茲涅先斯卡婭真的成為“愛情的奴隸”而寧可犧牲自己的性命也要為愛侶復仇。為了區(qū)別戲內(nèi)和戲外,米哈爾科夫分別用黑白片和彩色片對兩個故事進行表現(xiàn)。最后,沃茲涅先斯卡婭用戲里自殺的手槍打死了殺害愛侶的憲兵隊長,戲里戲外的時空融為一體,戲中戲也被以彩色片的形式呈現(xiàn)。又如米哈爾科夫熱衷于使用長鏡頭,在不動聲色之間以長鏡頭完成背景的交代或以人物的心理活動、命運等震撼觀眾。如在《蒙古精神》(1991)中,俄羅斯人謝爾蓋因為卡車出了問題而意外地介入了蒙古牧民貢巴一家的生活中,然后發(fā)現(xiàn)對方的生活狀態(tài)簡直與自己有著天壤之別,仍然以原始方式生活的貢巴甚至沒有接觸過可樂、避孕套等東西。米哈爾科夫有意用兩個長鏡頭,一個是貢巴夫婦說話的場景,一個是謝爾蓋夫婦說話的場景,分別表現(xiàn)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環(huán)境,并暗示著他們不同的文化背景、精神氣質、宗教信仰等,從而讓觀眾為這兩個連語言都不相同的男子能夠結為莫逆之交而感到震撼。對于觀眾來說,他們也得以在長鏡頭中慢慢走近這兩個主人公。又如在聲音方面,米哈爾科夫也能夠利用聲音來擴展鏡頭的內(nèi)涵。如在《西伯利亞的理發(fā)師》中運用的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使男仆費加羅對地位遠高于他的阿瑪維瓦伯爵的抗爭和電影中安德烈和將軍,安德烈的兒子在軍校和教官這兩場抗爭形成互文,并將這種抗爭精神上升到俄羅斯民族精神的高度。
三、米哈爾科夫的美學追求
如前所述,米哈爾科夫最為關注的是“人”,包括人的本質、利益與生存訴求,在美學上,他反復探索人性,表達著自己對于作為個體的人和作為集體的民族的前途的憂慮。
米哈爾科夫擅長表現(xiàn)人與外在環(huán)境之間的矛盾。從這一點來說,蘇聯(lián)的解體成為部分俄羅斯導演的一次打擊,但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卻成為米哈爾科夫的“賣點”,斯大林時代人們遭受的高壓政治,被政治暴力踐踏的親情和愛情等,而在蘇聯(lián)解體之后的葉利欽和普京時代下,俄羅斯社會依然面臨種種問題,這些都成為米哈爾科夫喜愛表現(xiàn)的內(nèi)容。人被米哈爾科夫置于某種因為時代等因素而極為不利的環(huán)境中,讓觀眾感受他們無法把握命運的無奈和痛苦。例如,在《十二怒漢》中,被指控弒父的小男孩之所以陷入極為不利的局面,除了各種證據(jù)以外,還有他出身車臣,而養(yǎng)父是俄羅斯軍官這一原因。而陪審團的12個成員,也都在各自的生活中有著種種沉重的往事。更令人嘆惋的是,最終盡管陪審團認為應該做出無罪判決,但是卻因為擔心小男孩在社會上遇害而不得不判其“有罪”,監(jiān)獄反而成為人的庇護所,這是極為諷刺的。
個人的悲劇對于米哈爾科夫而言,往往具有影射整個民族的意義。如《蒙古精神》被人們認為,米哈爾科夫之所以選擇了千里迢迢之外的蒙古草原,不僅是想展現(xiàn)一種自然淳樸的生活,而是借助蒙古族人對于自己的民族認同問題(如貢巴夢見祖先成吉思汗等)的思索,用以指涉蘇聯(lián)解體之后,夾在“東方”與“西方”、過去與未來之間的俄羅斯民族的民族認同境況。這也是為何《烈日灼人》(1994)也被認為具有和《蒙古精神》的同構性,也寄托了米哈爾科夫的民族憂患意識的原因。在《烈日灼人》中,米哈爾科夫使用了契訶夫戲劇中的“舊情人回歸”范式來制造戲劇性,讓觀眾從一個表面的家庭故事中看到蘇聯(lián)的“大清洗”的血雨腥風,斯大林成為扭曲了除娜佳之外所有人人性的“烈日”,科托夫、米迪亞等人都被以革命的名義傷害,或傷害他人,最終科托夫被捕,米迪亞自殺,幾乎沒有人能在“烈日”之下獨善其身。而娜佳這樣純真的孩子則代表了米哈爾科夫對于俄羅斯未來的希冀。
在俄羅斯新舊交替的時代,尼基塔·米哈爾科夫在時代的錘煉下,表現(xiàn)出一種開放性的,積極擁抱世界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始終圍繞“人”這一核心來進行探索,讓人陷入在矛盾中不斷與他人、與命運發(fā)生碰撞,加上其在電影形式上的精益求精,最終,米哈爾科夫在俄羅斯電影史上當之無愧地占有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