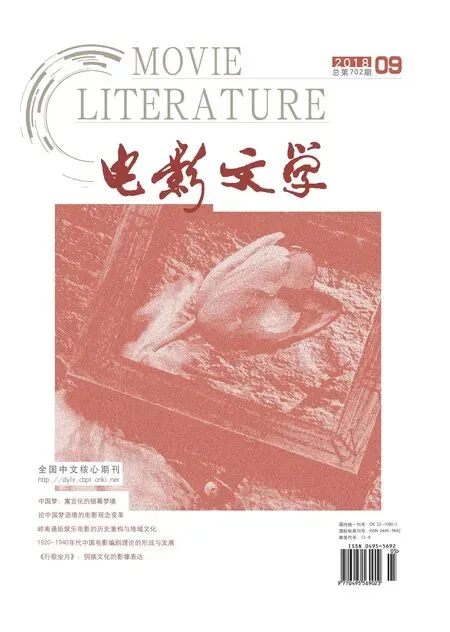《芳華》:讀取青春的兩重密碼
何穎利
(北京信息科技大學,北京 100192)
芳華,即美好的年華,亦指代青春。一部《芳華》,顧名思義,是與青春有關的日子。這里的青春,有劉峰、何小萍等的青春,也有馮小剛、嚴歌苓的青春。前者的青春,是埋藏在劇情中,讓我們感同身受而又潸然淚下的故事情節;后者的青春,是對時代和社會欲語還休、悵然若失的回顧與反思。馮小剛的鏡頭顯然已經穿越了敘述故事和宣泄悲情的境界,而試探地將視角投射到了更加廣闊的歷史空間和人文環境。他的娓娓道來,一如既往的百味雜陳,其間淡淡的憂傷,既是對個體青春的紀實文學般的真誠記錄,也是對獻身于轟轟烈烈的家國情懷中一代人青春的緬懷和思考。
一、個體青春:游走在政治和愛情之間的別樣年華
青春期是個體成熟的必經階段,但是青春和時代的碰撞,會受到特定歷史文化背景中具體因素的影響,在這部《芳華》中,這一抹時代背景成就了一代人青春成長的特殊體驗。
何小萍是右派的女兒,母親改嫁他人,開啟了何小萍尷尬的青春序曲。右派這個身份,在中國歷史沿革中是一個有著鮮明特色的詞匯,在接下來的歷史走向中,或許還會繼續出現與生俱來的血統里就帶著優越感的高干子女,還會出現不求回報只求奉獻的活雷鋒,還會出現虛榮的、漂亮的、嬌俏的姑娘,唯獨右派及其子女,屬于一個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特殊身份。而那個特定的歷史背景,產生了特定的生存方式,其青春也會閃爍著不一樣的色彩。 “愛”的匱乏,是那個年代的共同特點,而親情的缺位可能是何小萍最刻骨銘心的傷痕,所以這種特殊身份標簽下的青春最具有表現張力。何小萍把屬于她的青春留在了文工團破敗的地板下,那里隱藏著她曾經驕傲過的記憶,穿著軍裝,戴著軍帽,洋溢著燦爛而自豪的笑容。但她的青春故事也是破碎的,雖然經過劉峰的修補,但是一條條縱橫的裂痕永遠留在了照片上。她的傷痕,來自郝淑雯、來自林丁丁、來自朱克……來自身邊的那個環境和人群別樣的眼光:歧視的和排斥的,那些特定歷史環境下需要承受的、無法逃避的態度。恰恰是因為環境的苛刻,才使得她對于具有自主權的愛情付出得無怨無悔。那些與青春有關的記憶,在文工團的渲染下大放異彩,宣泄著一代人充滿幻想和激情的青春時代。
不同的政治身份,對愛情的表達也有所不同,蕭穗子的父親得到了平反,因此才有資格欲語還休;郝淑雯是革命的后代,張揚和凌厲顯得無可厚非;林丁丁出身于城市小資產階級,她只需要保持自己的俏麗和嬌憨;劉峰作為標兵,愛情態度既隱忍又堅決……唯獨看不出來何小萍是愛過的。可能踏雪無痕是那個年代里青春最難忘的感傷?劉峰與何小萍初次見面,劉峰排練場自告奮勇地與何小萍搭檔,何小萍送別劉峰……是從哪一段開啟的愛情?影片中何小萍唯一的一次公開反抗,是她在劉峰的樓下無懼無畏的那一句“走的時候叫我一聲,我送你”。在劉峰觸摸事件之后,兩個人在身份上取得了平等性,才有了何小萍告白的機會。而身份反差出現的荒誕性又使得何小萍對人情冷暖徹底絕望,絕望之外,是她對愛情的不肯放棄和對善良的堅持——“一個始終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識別善良,也最珍惜善良。”
劉峰的形象既蘊含著時代影響又寄托著一代人價值觀的取舍。“文革”時期對文化的重新審視,是由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一次重建,政治和精神層面的再認識是青年人改造價值觀的重要前提。禁欲主義是“文革”時代文藝導向的一大特點,“文革”時期的愛情大多是不能言傳和公開表現的。劉峰也有著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但是作為標兵,有著時代賦予他的行為標準和精神生活,附加在他身上的是與小資產階級思想有著天壤之別的特殊要求。而劉峰這樣一個先進人物,不但心存愛情,而且居然把手碰觸到了林丁丁胸罩的紐襻,這種“下流”的思想甚至公開實踐,在當時是不可饒恕和大逆不道的。劉峰的手玷污的不是林丁丁,而是“文革”時代的文化符號。他冒了禁欲主義之大不韙,觸犯了階級斗爭為綱的天條,褻瀆了他作為勞動人民應該具備的樸素情感,踩了青年人思想改造的紅線。劉峰的問題,不簡單是揭發、批斗、背叛等人性險惡的問題,也不能作為同齡人羨慕嫉妒恨的直觀宣泄來看待,這是一個可以上升為階級站位的問題、思想認識的問題、政治立場的問題,在那個年代有著充分的批判和改造的空間。
影片中,劉峰情愿戰死在祖國的南疆,以生命譜寫一曲戰歌,讓心愛的女人記憶并傳唱,足以看出劉峰仍然懷抱著英雄主義情結。而那個年代所需要的英雄人物是不近女色的,貌似寓言的觸摸事件,是政治和愛情之間矛盾的一次激化。縱然劉峰身上有諸多高尚的細節,都抵不過那一指觸摸。與其說劉峰以后半生為自己的一指觸摸付出了代價,不如說是劉峰為自己的高尚付出了代價。正是為了維護高尚,劉峰“低俗”的念頭才不被他人原諒,甚至不被他自己原諒。或者影片已經將標兵劉峰作為一種象征,成為創作者潛移默化中無法割舍的人生追求。對于劉峰事件的認識,可以以劉峰失去的那只手臂作為他這個錯誤的救贖。走下圣壇之后,劉峰徹底淪為一介平民,也自此過上了普通人可以有的生活。在小說中,他成了書販子、與妓女同居、被城管扣押車輛、以普通人的姿態死去……圣人和普通人之間,一個“高尚”的距離,鑄就了劉峰的悲劇,也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
維護高尚,是劉峰本人和創作者的共同心愿。于是那條“骯臟”的手臂離開他圣潔的精神。作為標兵和英雄,劉峰的情愛和性愛是分離的。他愛著林丁丁,卻始終無法跨越肉體的隔閡,在小說中,他有同居女友小慧,卻無法與她產生靈魂交融,他又不肯“欺負”何小萍……他的靈與肉,始終處于無著的狀態。作為特定文化在價值觀念上的投射,導演馮小剛甚或編劇嚴歌苓,潛意識里按照那個年代的標準為主人公劉峰保持了英雄的光輝形象。
二、社會青春:集體無意識參照下的時代芳華
弗洛伊德認為人的精神分為意識和無意識兩種,榮格認為無意識分為個人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兩個層次。這里的集體無意識,是社會心理結構,也是歷史文化積淀。影片所透過導演的視角審視的個案,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只是榮格所形容的高出水面的那一角海島,而作為島嶼基地的海床——集體無意識,即我們生活其中的文化背景才是讀取影片內涵的關鍵密碼。怎么評價那些事件,導演帶著怎樣的情懷去表現那些事件,都是基于民族特定的歷史階段中的文化背景。
何小萍為什么會精神失常?“大白菜在屋外凍久了,一搬進溫室就會爛掉。”冷遇和溫暖的反差,造成了何小萍的悲劇。冷遇來自于她右派子女的身份,溫暖也來自于她變成了英雄所造成的身份改變。被同齡人排斥和歧視下的右派子女是時代特色,被主旋律轟轟烈烈歌頌的戰斗英雄又何嘗不是時代特色?
劉峰的愛情是青春期的正常現象,而劉峰因為觸摸事件被下放就變成了特殊現象。英雄也有作為正常人的七情六欲,人的七情六欲被文化導向有意識淡化,繼而在淡化之后又被政治無限制放大,就成了特殊現象。劉峰的悲劇,不是每個時代背景下都能夠發生的,發生了,就說明這是特定環境造就的特定矛盾。
影片中的人物,分別代表著那個時代的不同群體,有目空一切的高干子女,有精打細算的市民階層,有高尚得不食人間煙火的活雷鋒,有自卑和隱忍的右派子女等。右派子女何小萍感動于活雷鋒劉峰的善良,活雷鋒劉峰愛上了市民階層林丁丁的溫婉情調,市民階層林丁丁幻想跨入上流社會,而上流社會的郝淑雯和陳燦又強強聯手,導演出一幕門當戶對的姻緣聯合戲碼。一條愛情線索貫穿下來,將當時的社會各階層及其等級表現無遺。每個階層的思想都在活躍地涌動,充滿著訴求和期待。這不僅表現著一段愛情故事,也是中國曾經有過的社會現實的真實描摹。
馮小剛的這部《芳華》和張藝謀《歸來》、陳凱歌的《霸王別姬》不同的是,一邊是用輕描淡寫的筆墨,在小資產階級的情調中尋找無處安放的青春,另一邊深刻彰顯時代特點,不濃墨重彩不足以提煉傷痕。作為一代導演和編劇,生命中這一段經歷是無可回避的,也是那一代人鮮明的烙印,在作品中無法不體現。有且只有的那些情節,從不同的角度闡述和詮釋,表達自身最深刻的體會。如何挖掘隱含在《芳華》作品中看似云淡風輕的敘述風格下的那種痛徹心扉的思考,不妨將視角投放到更廣闊的空間,去尋找時代洪流如何碾壓過他們的青春之后滾滾而去的軌跡。
發生在何小萍身上的幾段故事:穿林丁丁的軍裝去照相,在胸罩里加襯墊,群舞的托舉被歧視,在人群中默默愛著,也看著那些被愛著的人。從這些人際交往的矛盾沖突上看,本質上和普通的集體生活無異,甚或可以參看現今的大學生活。無非是群體生活中男男女女之間的糾葛、友情和愛情。從內容和情節結構上看,導演無疑是有意識要和時代擺脫關系的。《芳華》的時代感,從表層上看,來自于聽覺:《繡金匾》《草原女民兵》《沂蒙頌》,來自于視覺:紅色標語和綠色軍服的鮮明對比。看得出來,導演在拍攝過程中是矛盾的,既想突出時代背景,給自己刻骨銘心的青春形態一個完整的復原,又有意識地消解時代背景,把一段無法忘卻的青春記憶歸結為所有人都曾經歷過的生理年華中去。
反觀過往,梳理過歷史發展的每一個階段才能清晰比對不同時代的鮮明特點。從深層上看,“文工團”“右派”“戰爭”才是那個時代更為醒目的標簽。只有曾經身處其中,經歷過的人,才能深刻體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對人脫胎換骨般的改造,這些痕跡,是作品中的人物,同時也是創作者那一代人最難忘的情感歸皈——縱然歲月變遷,縱然身隔萬里,縱然一代人的過往被重新審視,他們的芳華都曾經和國家緊緊捆綁在一起,榮辱與共,這是中國人深厚的家國情結的外在表現,也是馮小剛想逃避又不得不去面對的,對于歷史和文化的思考、審視和批判的緣由,作品不由自主想表達的主題,具有特殊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何小萍在草地上的翩翩起舞,是久被壓抑的少女對于青春無法遏止的綻放,如果說導演對于芳華的展示在這里停止,是完全有理由的。這也是影片對于作為個體芳華的表現告一段落。不管那種青春是如何在荒漠中頂著烈日,在巨石下伸展枝芽,依舊會舒展雙臂去擁抱春天,仰起臉感受陽光的溫暖和雨露的滋潤。然而影片并沒有結束。繼何小萍起舞之后,鏡頭轉向的是劉峰和何小萍的掃墓,是劉峰在海口被城管刁難。劇情在殘疾的劉峰假肢被扔出來,掙扎中的人被按在地上的那一刻達到了另一個高潮……
——那一代人的芳華已逝。
根本不需要感謝導演馮小剛的悲憫情懷,讓權貴郝淑雯及時出現,給了劉峰一個擺脫困境的借口。陳燦海南拿地的大手筆,與劉峰為一千元而挨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個時候能夠出場解圍的,似乎也只能是郝淑雯或者陳燦之流,而不會是蕭穗子,更不會是何小萍。因為我們都知道,以這兩個人的生活背景處理這類事情是無能為力的——既無權也無錢。郝淑雯的出場與其說是交代故事中所有人物的結局,不如說是殘酷地拋出了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經歷了什么樣的生活,才使得同一個隊伍中并肩戰斗的戰友產生這么大的地位反差?劉峰曾經是先進、是標兵、是戰斗英雄,劉峰和郝淑雯的差距,真的只是搭上過胸罩紐襻的那只右手的距離嗎?
馮小剛終于沒有讓影片在溫情脈脈的時候戛然而止,他用了簡短筆墨、畫龍點睛般的鏡頭,瞬間將指代個體青春的芳華得以升華到時代和現實的層次。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馮小剛以其特有的尖銳視角賦予觀眾在影片中峰回路轉的人物命運之外以耐人尋味的思考。何小萍的精神復活不是結尾,劉峰與何小萍在一起也不是結尾,結尾在于那些活著的和死去的,他們曾經奉獻的青春,他們與共和國生死相依的情感,真誠、善良、勇敢、熱情和堅忍的那些美德,是我們要面對的和我們要正視與反思的,這才是故事中個體芳華綻放之后,時代所需要銘記、社會需要思考的另一種芳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