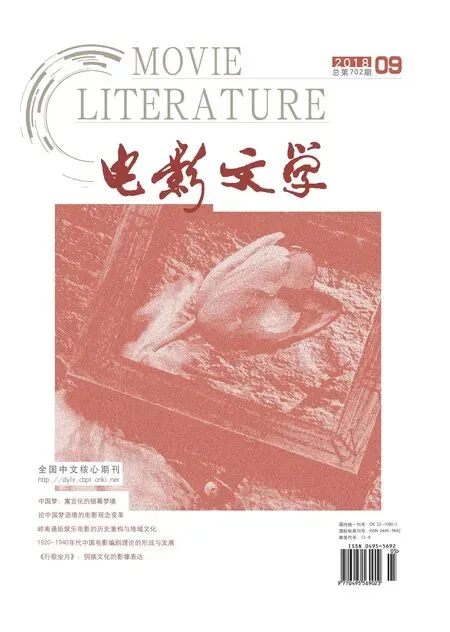《柳如是》:儒家思想道德的影像化
陳詠賢
(福建師范大學 閩南科技學院,福建 南安 362332)
吳琦執導的《柳如是》(2012)以明末清初著名才女,富有傳奇色彩的柳如是的一生,尤其是她和錢謙益之間的愛情故事為主線,為觀眾展現了一段宏富精彩、凄婉哀傷的晚明史。電影在傳遞出人物的精神人格魅力,重新建構起一個個人物形象時,也用影像對支配人物行為、主宰人物心理的儒家思想道德進行了闡釋,甚至是意義的再生產。在人們普遍認為,文化名人的傳記電影極難駕馭的今天,《柳如是》可以說提供了一個值得效仿的范例。
一、歷史人物儒學思想搬演
在對電影的情節進行組織和串聯時,電影就已經注意到了將能夠體現人物踐行儒家思想道德的掌故搬演出來。
(一)柳如是:舍生取義,修身齊家
歷史中的柳如是被錢謙益戲稱為“柳儒士”,而在電影中,柳儒士是柳如是給自己起的一個別號,這在一個側面反映了她個人對于儒家思想道德的認同。對于柳如是而言,她信仰修身齊家,完善自身素養,實現生活的高雅化,并要求錢謙益以匹娣之禮迎娶自己,實現名分的正當化。另外,她又認定“天下興亡,匹婦有責”,真切地為濟南等地的失守而痛心,在揚州城陷于危難,錢謙益自請督師時,柳如是將二人以韓世忠、梁紅玉作比,已有捐軀赴國難之決心;在眼看南都即將失守時,柳如是對錢謙益表示:“你殉國,我殉夫,天經地義。”而在得到錢謙益拒絕的回答后,心痛于自己看錯了人的柳如是毫不猶豫地獨自投水。在得知錢謙益要去做清朝的官時,柳如是出于情感而給錢謙益準備了盤纏,但又出于大義而怒斥他的首鼠兩端、寡廉鮮恥。電影中將黃毓祺向錢謙益募兵籌餉一事改到了陳子龍身上,以使情節更為集中,此時柳如是對于襄助陳子龍的義舉毫不猶豫,而在錢謙益被清兵下獄后,柳如是更是想盡辦法營救,在錢謙益出獄后,夫婦二人繼續多方聯絡,不忘復明之志。在家國風雨飄搖之際,柳如是在保全“忠”“節”等儒家強調的道德上可謂竭心盡力,無可指摘。
(二)錢謙益:經世致用,濟世救國
錢謙益作為東林黨魁、南明的重臣,卻在清兵兵臨城下之際失節投降,對此,史學和文學界的觀點有忍辱存身說、性格軟弱說、追求享樂說與追求功名說等。而電影選擇了在不否認錢謙益的人格具有游移性的同時,以較為正面的避免屠城,隱忍反抗說,解釋他的進退失據等一系列行為。而這二者都是服務于柳如是的形象樹立的,錢、柳二人,既有矛盾對立的一面,又有相互理解的一面,因此對于錢謙益的形象,絕不能進行全然的否定或肯定。
錢謙益是明末反對空疏無用的學問的儒者之一,他始終秉承著關心時政、經世致用的儒家理念,也正是他的這種思想深深地影響了鄭成功等人。因此,相較于單純的忠君,錢謙益更渴望對百姓、對“天下”做出更大的貢獻。因此,他既長期流連煙花之地,又“身在江湖,心存魏闕”,感慨自己不為明廷所用,他既可以為了報國而寫下血書,又可以為了保全百姓而在得到清廷許諾不屠城、開科舉以后決定獻城,并背負貳臣之名剃發出仕,為的是能在新朝傳承“周禮”。而在被清廷拋棄后,錢謙益又一直暗中聯系著鄭成功等反清力量,為陳子龍變賣自己珍藏的書籍,鼓舞他們繼續抗清。
(三)陳子龍、鄭成功:《春秋》大義,華夷之辨
云間才子陳子龍和收復臺灣的英雄鄭成功都是矢志抗清的義士,都與錢謙益有交往,以晚輩門生自居,在對抗清廷的態度上,曾經在軍事上與清兵正面為敵的二人都要比錢謙益堅決得多。電影中,陳子龍和鄭成功秉承著來自“尊王攘夷”的《春秋》中的華夷之辨,寧死而不剃發迎附新朝,最終鄭成功于臺灣建立政權,仁政安民,陳子龍則在舉兵失敗后投水自盡。
而陳、鄭二人的形象同樣是對柳如是起著襯托作用的,他們和柳如是之間的關系體現出電影對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的考量。電影除了表現了史上確有其事的陳子龍和柳如是之間的情愫外,也安排了鄭成功一直傾慕著這位“師娘”。在錢謙益北上做官后,心灰意冷的柳如是選擇留守南方,而鄭成功則已經下定決心,整編水師抗清。在臨走前,鄭成功前來試圖帶走柳如是,他試圖用柳如是內心深處的最大愿望來打動對方,即“如果你還有那一個做梁紅玉的夢,今天晚上就是你最后的機會了”。盡管最終柳如是沒有跟他離去,但是鄭成功對柳如是渴望“做梁紅玉”愿望的了解,從一個側面再次烘托出了柳如是與鄭成功共同的民族氣節。
二、符號的選擇和演繹
在對思想這一較為抽象的內容進行影像化上,對視覺符號的選擇和演繹是不可或缺的。符號學家趙毅衡曾經指出:“符號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電影可以說就是符號的集合體,正是符號搭起了觀眾和抽象思想之間的橋梁,重建了銀幕內外人和人的關系。
在《柳如是》中,花就成為一個反復出現的重要符號。柳如是本身就有愛花品花的個性,錢謙益在《玉蕊軒記》中載:“河東君評花,最愛山礬。以為梅花苦寒,蘭花傷艷。山礬清而不寒,香而不艷,有淑姬靜女之風。臘梅茉莉皆不中做侍婢。”山礬是一種代表了堅韌頑強的山野小花,柳如是的品評也是符合儒家美學“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溫柔敦厚,中和適度”的論調的。電影攫取了花代表了生機與美好,但是花期有限,在雨雪風霜(時代的風云變幻)之前十分脆弱這一點來對柳如是的人格和命運進行具象化,又對柳如是對花的喜好進行了一定調整。電影虛構了柳如是為陳子龍掩護,使其免遭官兵追捕的初遇,在這一段戲中,由于柳如是為陳子龍擦血而衣襟帶血,柳如是馬上當著官兵的面在衣服上的血跡旁點染了一朵梅花。而與此同時,妓院之中正在進行花榜評選,柳如是被譽為梅花而奪魁。電影到此就將柳如是和花之間建立起了某種意義關聯。而在柳如是勸說錢謙益投水自盡前,電影又虛構了一段情節,即兩人在畫舫之上把盞后,柳如是脫下衣服,請錢謙益在自己的后背上畫一朵家鄉的九里香,并通過柳如是之口表示往年錢謙益都會在她背上畫百花圖。而這一朵九里香,則寄托了柳如是“城破之后,南都最美的一朵花”的理想。在柳如是看來,自己就是一朵花,絢爛地開放過就已足夠,此刻她希望時間能在花開荼蘼的那一瞬間停止,以此暗示錢謙益自己自殺之決心,這也是電影對柳如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人格的一種演繹。這種以花喻人的修辭也給了錢謙益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枯榮自有天定,我們為什么要讓時間停頓,花開一年又一年,不更好嗎”這樣的蒼白解釋表達了自己不愿意殉國的心思。電影也在此達到了高潮。此后,柳如是和錢謙益相濡以沫時,老邁的錢謙益依然記得兩人初識的那句“桃花得氣美人中”,錢謙益臨死時紅豆樹時隔20年(錢謙益迎娶柳如是的那一年)又再開花等,都是花這一柳如是人格符號的反復出現。
三、新的意義生產
在我們肯定《柳如是》對于柳如是、錢謙益等人篤信的傳統儒家思想道德的理解是基本到位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電影并不是一部儒家思想的宣教片,電影人在進行表述時遵循的依然是當代人的思維和語言系統,電影要獲取觀眾的理解和認同,實現人物和觀眾之間的交流,就不能單純地介紹儒家思想,或以舊時代的儒家道德為立場對人物進行評價。在《柳如是》中,我們可以發現,電影在不違背史實的前提下,對人物的行為進行了新的意義生產,使之更能迎合當代觀眾的價值觀念或審美趣味,這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在柳如是這一形象身上體現出來的女性主義思想。
傳統儒家思想道德與女性主義思想在大體上是矛盾的。自周禮設定以來,男女兩性就進入了“一種階級和性別的雙軌等級制”中,女性在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的權利要遠遠弱于男性,在三從四德的要求之下,成為男性的附庸。然而在晚明,世風放誕之下,部分婦女受到的束縛得到了一定的減弱,如柳如是、王修微等女子,能夠學習知識,進行文學創作,參與社會交游。這一點也被《柳如是》大肆渲染,觀眾得以看到一個聰明靈慧、自由獨立的女性形象。如柳如是時常做男裝打扮,頭戴儒巾,不卑不亢,瀟灑自如,或在岳王廟題詩,或出入萬松書院聆聽錢謙益講學,主動登門拜訪錢謙益;又以女子身份公開招婿,一一考量當時杭州城里的青年才俊,在招婿過程中,電影借柳如是的男性追求者之口說出柳如是還曾為陳子龍寫出《男洛神賦》。男女兩性之間,男性觀看女性,選擇女性,用文學歌詠、賞玩女性的陳規,在柳如是這里實現了顛覆,女性也可以憑借自己的才情在兩性關系中占據主動位置,保持著自己在人格上的獨立和在愛情觀上的堅持。觀眾仿佛看到的是一個才華出眾、意志獨立、性格篤定的現代女性。在電影的結尾,萬茜等角色扮演者還以現代裝出現在一個掛有柳如是畫像的博物館中,人物仿佛實現了在時空上的穿越,這更是強化了觀眾將柳如是與現代女性進行聯系的觀念。
實際上,電影中如招婿等情節在歷史上是確然存在的。這些離經叛道,看似違背了儒家思想道德的言行,其實是儒家思想在晚明的一種自我糾正(如王陽明對人的主體意志的肯定)和如李贄等“異端”對儒家思想的攻擊結合之下的產物,女性得到的解放也是極為有限的。然而電影卻無意于從這個角度對柳如是的行為進行解釋,而是從現代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讓觀眾去理解晚明江南女子這種獨立颯爽、自由開放的新風尚。這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意義生產。在電影中,柳如是(楊影憐)干脆利落地結束和陳子龍的感情,并馬上改名明志,表明自己不需要“顧影自憐”,而是有著“我見青山多嫵媚”的主體意識,而在得知陳子龍死后,又不顧他人眼光為陳子龍設立靈堂;在鄭成功登臺鼓舞水師官兵士氣時,柳如是替臥病在家的錢謙益對官兵講話,代表全南都的女性,聲言自古美人愛英雄,號召大家為了保護城中姐妹奮勇作戰;在錢謙益北上做貳臣后,柳如是既因為忠于情感,沒有跟隨鄭成功,又因為錢謙益突破了自己的底線而離開錢家,不懼“河東夫人和大木(鄭成功)私奔了”的流言而孤身漂泊。對于柳與陳、錢二人的閨房之樂,電影也有所表現。這些都是電影新創或對史實進行加工了的情節,與電影專門以鄭成功生長于日本,不懂中原禮教來解釋鄭成功的種種行為不同,電影中的柳如是以一種完全自然而然、當仁不讓的態度表現出自己與傳統儒家理念格格不入的社會責任意識,女性理所當然地服務社會,激勵男性,享受性愛,以主動的態度面對人生中的每一個重大關節(也正因如此,電影沒有表現柳如是被迫自縊而死的結局),散發出耀眼的光芒。
歷史人物的心態、思想等內在要素的展現,是電影人在拍攝傳記電影時頗感掣肘、棘手的問題。尤其是擁有經典佳話,內心世界極為豐富,文化修養極為高深,卻難以落實到具體本事的文人墨客,更是相對于政治、軍事人物等而言更難以被搬上大銀幕。吳琦、高峰在電影《柳如是》中展現出了高度認真的創作態度與較為嚴謹的考據精神。同時,在上述問題上,吳琦、高峰表現出了精湛的掌控能力,電影以恰到好處的方式呈現、點染了在柳如是等人的意識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儒家思想道德,在不損害影片戲劇性的前提下,又使得人物行為合乎史料及情理,也為電影賦予了一定的文化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