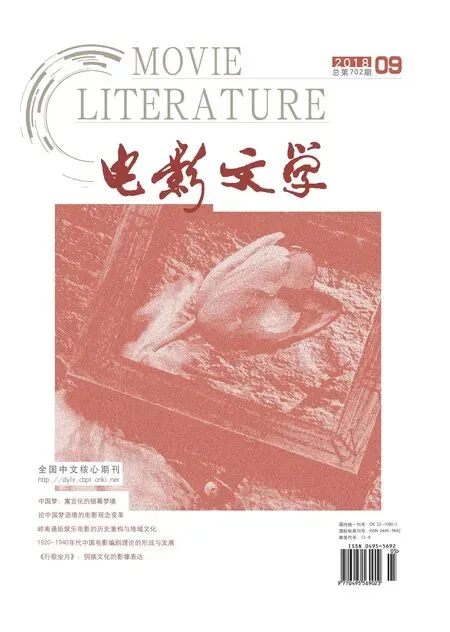淺議《月光男孩》的克制表達
王 娟
(湖北中醫藥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5)
巴里·詹金斯的《月光男孩》(Moonlight
,2016)以真誠、工整的敘事和精致、細膩的鏡頭語言,摘取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以及最佳改編劇本獎。在對《月光男孩》的討論中,除了其頗為小眾的題材外,便是其極具克制性的表達。一、主題表達的克制
電影《月光男孩》改編自麥卡尼具有自傳意味的話劇《月光下憂郁的黑人男孩》,因觸動了詹金斯對自己童年的回憶而被其搬上大銀幕。整部電影關注的其實是主人公奇倫的內心世界,電影也因這種向內的探索而具有極強的藝術感。
電影涉及四個主題,即很容易使電影被標簽化的少數族裔、同性戀、毒品和貧窮。這四個主題都可以進行情節線索上的展開,都可以擁有不同的意義走向。如黑人在生活中被白人主流社會公開或半公開式地放逐,如此可以完成對人性陰暗、自私一面的批判;又如吸毒的父母對未成年人的成長產生持久的、揮之不去的負面影響,如此可以表達個體在一個有著種種癥結的社會中的命運軌跡;又如主人公的性取向導致其生活遭遇諸多打擊和困擾,最終陷入一種悲劇境地中,如此可以展現一個有待提升的社會境遇對于一個正常公民的扭曲等。如果詹金斯選擇進行這樣一種雜糅式的,飽滿的敘事,建立起一個擁有多維度的影像闡釋空間,那么《月光男孩》盡管講述的還是有“以政治正確迎合評委口味”之嫌的故事,但無疑將從小眾轉向大眾,得到更廣泛范圍內觀眾的共鳴。
但這樣一來,從藝術上而言,在電影時長有限的情況下,任何一個主題都必須面臨著在完成度上被削弱,整體敘事顯得渙散的風險;而從主創的主觀意愿而言,這也是違背他們表達的初衷的。詹金斯無疑明白上述主題都可以傳遞出強大的情感力量,但他更傾向于進行對個人境遇的專注展現。因此,電影盡管表現的是黑人的生活,但是卻并不利用所謂“膚色優勢”,全片沒有出現一個白人,不同族裔之間的歧視傾軋也就退出了表達;電影在展現主人公身為邊緣者中一員的苦痛時,也并沒有運用如搖滾、嘻哈等具有狂暴、發泄姿態的元素;在涉及毒品問題時,電影也僅是較為委婉地展現了奇倫母親吸毒帶來的惡果,如情緒上的失控、私生活的混亂等,奇倫本人以及對他來說有人生導師意義的胡安都不是癮君子,他們只是將販毒作為一種職業來從事。自始至終,詹金斯都將表達的重點克制地停留在奇倫在時光周轉、物是人非中孤獨沉默的成長上。或者可以說,詹金斯將電影處理成了一次觀眾目睹奇倫一個人對“月光下的黑人男孩是藍色的”這句話的追尋、體驗過程。
甚至這種個人境遇也是被以一種個人化的方式處理過了的,即電影以三個篇章的方式,截取奇倫分別被稱呼為“小不點”“奇倫”和“老黑”的童年、少年和中青年這三個人生階段,傳統敘事的起承轉合和圓滑的戲劇性被消解掉了,這種斷裂的、串聯式的,沒有過場戲而言的敘事,顯示的是敘述者記憶的選擇性和非連續性。
二、情節內容的省略
而在這種非連續性敘事中,自然有大量情節內容被詹金斯舍棄,其中不乏一些關鍵的,令觀眾疑惑叢生的問題,電影沒有給出答案。比如從奇倫和憔悴的特蕾莎之間的對話觀眾得知,胡安竟然已經死去,電影并未交代胡安的死因,一個關鍵的角色就消失在了奇倫的人生中。又如奇倫在童年時代因為母親吸毒而極為痛苦孤獨,在他知道對自己來說近乎養父的胡安是一個毒販時,他憤怒地轉身離去。然而在電影的第三段中,成年奇倫出場的時候已經成為稱霸一方的毒販,換言之,他成為自己曾經最討厭的人。在這十年的成長過程中,奇倫究竟經歷了什么才選擇了這種生存之道,又是如何逐漸開拓了自己的“事業”,這也是詹金斯有意省略了的。
接受美學指出:“作品的意義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作品本身,一是接受者再創造的成果,作品本身只不過是用語言文字或其他藝術符號建構而成的一整套龐大的符號系統,而任何符號的東西只不過是一張網,這網對創作者所表現的全部意蘊來說,已流失了許多東西,必然留下了語義的空白或模糊。”在編織《月光男孩》這張網時,詹金斯是故意留下空白處,對觀眾進行再創作上的召喚的。實際上,在第二段敘事中,奇倫掄起椅子砸向曾經欺負他,慫恿凱文打他的校霸后,奇倫就被送進了少管所,這可以視為奇倫的第一次以暴制暴,第一次反抗。從此以后,他就為了不再被現實摧毀而走上了胡安的道路。如在體格上,奇倫模仿胡安這樣的典型“男子漢”,練就了強壯的身材,與“小不點”時代有著天壤之別。在黑道上,奇倫也一直堅守著強勢地位,對手下呵斥起來毫不留情。在外表上,奇倫鑲金牙,戴金鏈,連汽車上也像胡安一樣放著金色皇冠,他全方位地使自己具有威脅性,因為胡安曾經示范過他是如何通過上述包裝來被他人尊重甚至羨慕的,但是這并不能改變奇倫依然處于一種孤獨的、受困的狀態。
另外,與李安的《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
,2005)不同,電影在奇倫和凱文相會后就戛然而止,不僅沒有交代奇倫在慢慢接受了現在這種生活以后的發展,對兩人的關系也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結局。而令觀眾容易產生聯想的,是奇倫已經在自己身上復制了一個新的胡安,而胡安的英年早逝,很有可能便是因為販毒導致的黑幫火并或被警方殺死,奇倫是否有可能也會重蹈胡安悲慘去世的覆轍,或是在與身為廚師的凱文相愛后,放棄自己危險的毒販生涯轉而謀求一份更為安穩的職業,這些都是觀眾合理的猜測,詹金斯通過情節上的省略使得觀眾能夠參與到藝術活動中后,發揮想象、聯想能力,將自己的經歷、氣質灌注其中,對作品進行闡釋與創造。三、影像語言的含蓄
如前所述,胡安用金表、金鏈和金皇冠等來裝飾自己和自己的車等,這實際上就是電影設置的有意味的影像語言。在《月光男孩》中,這樣的語言比比皆是。詹金斯深受王家衛影響,正是王家衛的《重慶森林》(1994)讓詹金斯決心投身于電影創作,一心想向王家衛致敬的詹金斯也善于以含蓄的、有隱喻義的影像來打開觀眾的思緒,但是與王家衛習慣在電影中運用大量旁白不同,詹金斯在《月光男孩》中并不使用旁白、對白等常規語言直接對人物的心理進行介紹,而是用與之相關的視覺形象進行表現,給予觀眾體會和挖掘的余地。
例如,在電影一開始,詹金斯選擇用一段跟拍來表現奇倫被小伙伴們追打、慌不擇路的狀態。奇倫躲進了胡安的一間用于吸毒販毒的房子,捂著耳朵蹲在一邊。由于窗戶被木板釘死,屋子里極其黑暗,地上還散亂地放著癮君子留下的針管。而沒多久,目睹了這場追打的胡安拆下木板,破窗而入,站在光線之中對奇倫說:“出來吧,外面壞不到哪里去。”在這段影像中,小黑屋無疑就暗示著童年奇倫封閉、陰暗的內心,并且這是由于吸毒者(母親)造成的。而胡安卻是打破他的心防,帶他走進光明中的人。胡安不僅和女友特蕾莎一起,給予了奇倫一個溫馨的避難所,還給奇倫零用錢,彌補了奇倫成長中父親的缺位,而且正是胡安給奇倫講述了“月光下的黑人男孩是藍色的”的故事,是胡安告訴他同性戀并不應該被歧視,“在一定程度上講,成為什么樣的人,是由你自己決定的,你不能讓別人左右你的思想”。這些話語都如同陽光一般照亮了奇倫的世界。
又如胡安與奇倫的一次重要的互動便是在邁阿密的海邊,胡安教奇倫游泳。胡安站在海里雙手托起奇倫,對他說:“好好感受,你就在世界的中心。”胡安是教會奇倫如何在這個社會上立足的人,電影將其具象化為教游泳這一技能。海成為奇倫生命中的一個重要意象,他甚至在回家后躺在浴缸里,將水染成藍色,幻想大海的感覺。胡安所教導奇倫的是,這個人類社會是與海洋一樣的,人浮在其中時感受到的是自由與歡暢,但是海洋又是極為危險的,如果人泳技不佳,就有被巨浪吞沒的危險。這是胡安作為一個毒販的生存經驗。在海里,他是童年奇倫最信賴、最能依靠的對象。因此當長大后的奇倫再想與異性發生親密關系時,他總是想回到海邊去再一次感受到那種自由和人與人之間的親近。可以說,這種含蓄的影像語言是引人入勝,有著多重解讀空間的。
四、人物塑造的洗練
《月光男孩》中出現的人物不多,詹金斯在將電影的主視角始終保持在奇倫身上的情況下,在奇倫之外的配角上并不安排復雜的情節,配角人物在電影中的有限出場只能是奇倫所看所知的。但配角依然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主要在于詹金斯以一種洗練的筆法,在簡要的鏡頭和臺詞中就表現出了人物與奇倫至關重要的聯系,或屬于人物特殊的心態或處境。
除了胡安以外,凱文則是奇倫成長過程中另一個重要的男性角色。在幼年時,凱文以“你想讓那些傻瓜天天捉弄你嗎”的激將法刺激奇倫和他打了一架,奇倫也正是在這一架后逐漸樹立起了對自己的信心,他開始將凱文視為自己一個特殊的朋友。而在上高中之后,奇倫繼續忍受著同齡人的孤立和排擠,人們甚至公然嘲笑他:“那個黑鬼忘了換衛生巾了。”在簡短的臺詞中,奇倫的處境就被展現了出來,同學以女性特有的行為來譏刺奇倫是一個同性戀者,對男同性戀者的誤解和輕視溢于言表。這對于一直無法直面自己性取向的奇倫來說無疑是痛苦的。但觀眾和奇倫一樣,此時并未意識到,處于同樣環境下的凱文也在忍受著社會這種對同性戀的歧視,并為此惴惴不安。詹金斯以一種極為含蓄的方式展現了凱文的狀態。凱文和奇倫在學校的走廊相遇后,凱文熱情地向奇倫打招呼,并開始滔滔不絕地對他講述自己和幾個姑娘之間的交往等,以一種看似青春期少年炫耀式的方式說:“艾梅斯抓到我和一個女生在樓梯間里搞了。”臺詞雖然簡單,但是卻暴露了凱文復雜的內心世界。在人人都以欺負疏遠奇倫為常事時,凱文卻主動與他說話,但說話的內容卻不斷強調兩個信息:第一,自己是一個異性戀,并且是一個女性緣不錯的異性戀;第二,有人來“抓我”,調侃自己吃禁果行為的哥們,自己的同性人緣也相當好。這些無疑都是在將他自己和孤僻的奇倫之間畫上一條界限。因為年少的凱文完全無法接受自己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中有同性戀取向這個可能,他必須做出一種合群的姿態以自保。有了這句臺詞的鋪墊,凱文后來對奇倫的毆打也就順理成章,并不顯得突兀了。
《月光男孩》以一個黑人同性題材講述了一個個體成長的故事,其內容是簡單的,但是其中蘊含的情感與人文關懷思考又是極為復雜的。奇倫身處一個不平等的,充滿偏見和歧視的社會環境中,經歷了電影中的三段式成長,完成了一個從不知所措、自我封閉,到奮起反抗,最后到與生活進行了艱難的和解的過程。詹金斯將屬于奇倫個人的不幸投射出來,在一種高度克制、隱忍的表達中,讓觀眾認識了奇倫,也看到了內心脆弱的自我。這也是《月光男孩》能給予觀眾長久、積極的解讀興趣與寬闊的解讀空間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