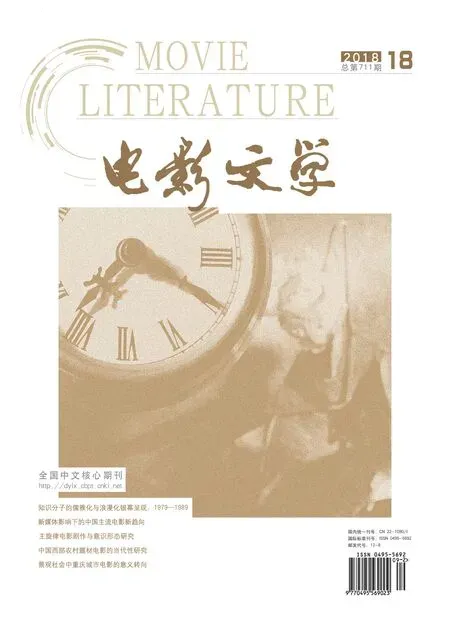淺析文德斯電影中的身份認同
黃 華
(同濟大學 藝術與傳媒學院,上海 201804)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身份認同就開始出現在文學、文化學、社會學的研究中。德國的戰(zhàn)后一代,無論是普通青年還是電影人都對自身及所在群體的身份認同產生了巨大的焦慮和困惑,這種情緒廣泛存在于新德國電影中。作為新德國電影運動的代表人之一的導演文德斯(Wim Wenders),在其作品中大量呈現了對身份認同問題的理解。本文重點關注文德斯電影作品中關于“身份認同”的建構,既包括作為戰(zhàn)后德國人、歐洲人對個人身份,包含對生命、時間、歷史的反思,又包括作為電影人、藝術人為歐洲電影發(fā)聲以及開展更為廣闊的藝術探索。
一、 電影故事和主題:文德斯的選擇與思索
文德斯電影中關于身份認同的表達有兩部分。一是關于作為德國人的“身份認同”,很顯然這根植于德國復雜的民族歷史狀況。二是作為電影人的“身份認同”,這一部分既有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影響作用,也有文德斯個人實踐探索的經驗積累。
(一) 主題:孤獨的旅程
1.德國青年的身份認同危機
文德斯的散文、影評和談話記錄中很少直接涉及德國歷史的討論。但這并不表示他的作品與歷史無關。相反,文德斯的大量作品都是基于戰(zhàn)后德國、戰(zhàn)后歐洲的社會現實所創(chuàng)作的。在談《柏林蒼穹下》(Der
Himmel
über
Berlin
,1987)的創(chuàng)造構思時,文德斯表示電影故事發(fā)生在二戰(zhàn)結束后,“上帝顯得很生氣,并將天使放逐到地球上最糟糕的地方:柏林”。“流浪”“旅行”一直是文德斯電影的主題。事實上,“漂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學母題,在人類文學史上古已有之。在漂泊的旅途中,人得以離開都市的喧囂,有一段空閑的時光思考人生。而這些思考,在文德斯的電影里,變成了德國青年對自身存在的探索。文德斯的影像用“旅行”的方式來展現德意志民族進行身份認同的成果。《愛麗絲城市漫游記》(Alice
in
the
Cities
,1974)所描述的就是獨自出行中的人學會面對和戰(zhàn)勝恐懼的故事。在《道路之王》(Kings
of
the
Road
,1976)中,主人公同樣是依靠旅行找到了自我。電影中的人物故事,象征著那個時代里人們的掙扎浮沉。德國青年對于個人“身份認同”的困惑,也是歷史的困惑。難能可貴的是,導演將它們細心記錄于影片中。那一代人的迷惘、不安、孤立均是電影一直反復探討的話題。因此,它們共同表現了文德斯作為德國人的身份認同困惑這一主題。
2.歐洲電影人創(chuàng)作觀念的認同危機
文德斯的電影有濃烈的內省色彩,而這一份“內省”也包含其作為德國、歐洲電影人的身份意識,這也是其身份認同構建的珍貴證據。
影片《事物的狀態(tài)》(The
State
of
Things
,1982)像極了文德斯的自傳。片中的導演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對演員與攝制小組說:“故事只存在于故事中,隨著時間過程的流逝,生命繼續(xù)進行,無須制造故事。”此外,文德斯在拍攝完《德州巴黎》后,將自己的“故事觀”做出歸納,“故事就在那里,它們沒有因我們而存在。沒有必要去創(chuàng)造它們”。在影片《尋找小津》(Tokyo
-Ga
,1985)中,文德斯認為,小津的影像是接近于電影的真實目的的,即“為20世紀的人類塑像,一個真誠、可信而有用的影像”,這樣的電影能幫助人們認識自我和世界。文德斯也表明了其拍攝電影的初衷——在現實世界里尋找到單純、明晰又真實的影像。像這樣表達個人藝術觀念的影片還有《里斯本的故事》(Lisbon
Story
,1994)。電影中,主人公抱怨他們拍出了和垃圾一樣的影像,影像已經變成了垃圾。但電影人依舊應該相信手搖式攝影機,用心創(chuàng)造有價值的東西。這其實也是文德斯的創(chuàng)作信仰。由此可見,文德斯把個人的創(chuàng)作觀點融合在影片里。不論是含蓄或是直接的表達,都體現了文德斯作為德國、歐洲電影人的堅守和探索,也由此成為文德斯電影里表現身份認同的另一主題。
(二) 情節(jié):反經典敘事
很顯然,文德斯的電影沒有復雜的情節(jié)設計。與經典好萊塢電影大多將矛盾建立在人物沖突上的戲劇手法相比,他的電影矛盾直接來源于現實社會。同時,故事情節(jié)也是反“三幕式”的“插曲式”結構。這樣獨特的劇情結構也體現了文德斯的個人創(chuàng)作觀念。
文德斯承認,其本人創(chuàng)造的影像故事有兩種編劇方式,一是依靠個人構想,二是對原著進行改編。由于他認為世界有一種混沌美,因此其劇本往往少有戲劇性極強的情節(jié)段落。與影片《道路之王》相似的“游走情節(jié)”,在文德斯的電影里也是比比皆是。同系列的“道路三部曲”里的《愛麗絲城市漫游記》以及《歧路》(False
Movement
,1975)都是主人公旅途“見聞”的疊加。主人公的行動變化都是由其所處地點的變化或是他們遇到的人物變化而展開的。主人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他們的行走、對話構成了電影的主體。整體而言,文德斯并不偏好好萊塢的故事觀和他們的敘事手法。因此,他的電影“講述”故事的方式也與其極為不同。這種不同,也就是有著鮮明文德斯個人特色的敘事方式。而這種獨特的電影敘事方式,正是文德斯作為德國、歐洲電影人強調個人“身份認同”的有效手段。二、電影風格和表達:文德斯的構建與演繹
文德斯認為,風景有訴說故事的能力。因此,在文德斯的電影里,除了故事的講述、情節(jié)的設計之外,鏡頭里所捕捉到的空間、色彩也充滿了文德斯耐人尋味的思考,而這些部分也幫助他呈現了其關于身份認同的困惑。
(一) 電影空間:公路和城市
米歇爾·福科(Michel Foucault)在《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一文中,提出了“我們時代的焦慮與空間有著根本的關系”的觀點。即,我們的生命、時代與歷史都與我們所處的空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同樣,文德斯電影中的空間也無時無刻不在渲染著屬于他的時代焦慮。
文德斯曾經說過,“我許多的電影都是以公路地圖而非以劇本開拍的。”由此可見公路空間對于其電影的重要性。“公路片的核心沖突就在于原始空間與現代空間的對抗。”由此可見,公路作為公路電影中時常出現的元素,連同它道路旁的加油站,也包括汽車、輪船、飛機都成為逃離現代社會空間的有力助手。影片里,主人公駕駛著交通工具,在逃離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就能夠發(fā)生思考、審視內心,開始進行有關身份認同的思考,文德斯的電影里有大量類似橋段。
如同上文提到的《道路之王》里的布魯諾和藍德一路上都在思考如何改變。同樣一路上都在試圖得到自我身份認同的還有影片《歧路》里的威廉。在影片《事物的狀態(tài)》的最后段落里導演和制片在漫漫長路上徹夜長談。以上都體現了公路空間的重要性。
此外,城市也是文德斯電影中的另一空間。城市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逐漸成為現代人迷失的標志,也成為人類在后工業(yè)社會中精神陷入困境的象征。無論是《公路之王》里在東西德邊境游蕩的布魯諾和藍德,還是《愛麗絲城市漫游記》里菲利普帶著女孩愛麗絲去烏伯塔爾找外婆,這些主人公都明顯還處在戰(zhàn)爭帶來的“后遺癥”中,目光呆滯、表情麻木。而德國的大街小巷更是讓他們“惶惶不可終日”。影片《柏林蒼穹下》更是直接暴露了世人關于“柏林”的困惑。
城市空間解釋了文德斯電影里的主人公能夠“一直在路上”的原因。影片通過不同城市空間的呈現,暴露出城市的“病癥”,揭示主人公們各式各樣的身份認同困惑來源。也正是這些原因,使得文德斯電影里的主人公們能夠一直在路上,穿梭在不同城市間,一直開展“身份認同之旅”。
(二) 電影色彩:黑白、彩色與心理投射
文德斯的電影作品偏好以黑白影片的方式呈現。例如,《公路之王》《愛麗絲城市漫游記》《事物的狀態(tài)》等。這在彩色電影大行其道的今日,已是屬于他獨特的身份標識。文德斯對于電影的色彩有著獨特的見解。他認為,黑白影像比彩色影像更加具有還原真實現場的能力,黑白能過濾掉畫面里多余的如塵埃一般的色彩,更容易讓觀者看清本質。
同時,在文德斯的電影里,黑白與彩色夾敘也時常發(fā)生。對于文德斯而言,色彩的變化是人物心理的投射。影片《柏林蒼穹下》前半部分為黑白,而后半部分的色彩隨著天使變?yōu)榉踩说膭∏樯钊胫饾u變?yōu)椴噬cy幕之上的色彩正是影片中天使的心理投射,即,導演對于城市、歷史思考的變化過程。而這一番心理變化,就是文德斯進行身份認同的表達,是創(chuàng)作者在穿越歷史塵埃之后對于歷史、社會、現實的新認識。因此,色彩的運用也是文德斯電影中有助于表現人物進行身份認同的重要元素之一。
(三) 電影鏡頭:“時序和動作的持續(xù)”
對于電影鏡頭,文德斯認為,“影像運動與動作的持續(xù)必須是真的”顯然,文德斯電影里的一些鏡頭持續(xù)時間夠長,動作也很完整,它們體現了文德斯的“鏡頭觀”。
文德斯電影中有很多類似于行車記錄儀拍攝的畫面,大多數記錄的都是旅程中的風景。影片《里斯本的故事》開頭有一個超過4分鐘的鏡頭。在這個鏡頭里,都是一些長短不一的類似于行車記錄儀的畫面,內容則是公路沿線的自然風光。《里斯本的故事》拍攝于電影誕生100周年,探討的是關于“真實影像”的話題。影片《事物的狀態(tài)》開頭就提到了“片中片”《幸存者》里由于資金原因而沒有辦法在海邊拍攝長鏡頭。在影片最后,導演和制片在車里暢談的鏡頭,也是使用固定機位長鏡頭拍攝,較為完整地記錄了馬路上的車來車往以及人物對話。在此處,文德斯除了使用“色彩”“故事”來強調“身份認同”以外,還通過他獨有的鏡頭拍攝和剪輯方式,再一次巧妙地強調了自己作為藝術電影人的“身份認同”。
三、結 語
文德斯影片中對于身份認同的構建使得其電影極具特色。在題材和故事的選取設計上,他牢牢關注戰(zhàn)后社會現實,敏銳地捕捉到了彼時社會主流的思想動向。開展了大量關于戰(zhàn)后存在的思考。尤其偏愛汽車等運動空間里發(fā)生的故事,一再描繪遷移、旅行。而在電影敘事手段上,堅持走歐洲電影不同于好萊塢技術主義的路線,極少使用蒙太奇,對鏡頭運動和場景幾乎不加剪輯。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電影發(fā)展都需要深刻挖掘民族精髓,精準把握民心走向,構建主流生活現場,形成具有文化身份和文化意識的作品,才能促使電影真正被大眾接受、記憶、認可,而文德斯的電影作品恰恰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寶貴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