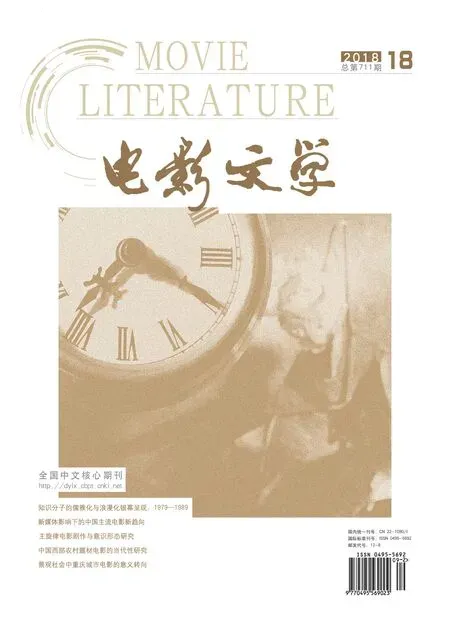賈樟柯電影的抒情意蘊和人文反思
高勝利 薛巖松
(運城學院,山西 運城 044000)
電影是一門藝術,通過話語蘊藉來體現獨特的審美價值。它用直觀的方式組合起美的形式,在幻燈片中擬造出一個真實之境,觀眾在與之產生共鳴后得到精神上的滿足。這便引發出電影的終極價值追求,即“人文關懷”,它“是一種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嚴、價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與關注人的全面發展、生存狀態及其命運、幸福相聯系。”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化驅使電影求新出奇,這種快餐式的消費潮流讓本有著人文情懷的第五代導演漸漸迷失,《霸王別姬》《活著》《紅高粱》,這些拷問人性的作品仿佛電影中的悲歌一樣,成了歷史回眸后的深沉。而賈樟柯導演則用一種反好萊塢式的創作手法,用平實的鏡頭表達人們日常生活的情感,展示出在經濟騰飛下中國百姓最為普遍的精神困惑。
一、賈樟柯電影的風格特征
“文學風格就是作家在用客觀事物本身的語言表達和突出客觀事物的本質特征的同時,通過對象表現自己精神個性的形式和方式。”電影和文學相同,都是表現人類審美意識形態的藝術形式。通過分析一位導演的創作風格,可以了解到導演所關注的客觀對象以及在精神層面上的價值追求。賈樟柯作品的風格主要有兩點:
(一)歷史視點下的電影真實
在不同的歷史視點上,人文關懷也相應呈現出不同的價值維度。童慶炳先生云:“文學作為審美創造的自由空間,作家完全有權利而且能夠在不同的歷史理性視點上去展現人文精神。”賈樟柯曾談到拍攝《小武》的契機:“真正以老老實實的態度來記錄這個年代變化的影片實在是太少了!整個國家處在這樣一個關鍵性轉折時期,沒有或者說很少有人來做這樣一種工作。”通過電影反映社會現實成了賈樟柯的創作動機。他用真實的鏡頭去記錄在時代變遷下人們的生存方式與精神狀態。
(二)平實的藝術風格
因為要紀錄時代下人們的精神狀態,賈樟柯的電影把日常生活的細節做出整理,使得這些細節的組合符合人們內心變化的節奏。影片《小武》中有這樣一段情節,小武去看望生病的胡梅梅,他們并排坐在靠窗戶的床上,梅梅背后是歌星王靖雯的海報,象征她的明星夢想,小武背后是一面鏡子,象征雖是扒手的他也有著善良的一面。兩人談論著未來,長鏡頭的延宕使之產生一種間離效果,觀眾游走于現實和影片之間,情感在這里悄悄彌合。賈樟柯樂于用平實的方法去描述一個現實世界,這便是他的價值追求,即真實的情感只需要客觀的態度來表現。
二、賈樟柯電影中的抒情意蘊
賈樟柯對社會轉型期間人們精神狀態的變化投入了較多的關注,用民眾的心靈動態來表達特定時代下的人文情懷,體現了賈樟柯電影正回歸中國抒情文學的傳統。
(一)心靈的故鄉
中國處在社會轉型期,時代的浪潮必然淹沒舊有的社會秩序。賈樟柯為了記錄這可能消失的民族記憶,在他的作品中常有各種懷舊的因素。
1.符號懷舊
(1)拆遷——時代的變革
賈樟柯早期的電影中,“拆遷”符號常常出現。如《小武》,小武在遭受愛情、友情以及親情的拋棄后,獨自行走在灰蒙蒙的街道上,身邊磚瓦房的墻壁上都赫然寫著“拆”字。這樣的符號不僅可以交代小武身處的環境正在經歷著劇烈的變化,而且也映襯出他內心的彷徨、孤獨與無措。此外,《站臺》《任逍遙》等影片中,這樣的“拆”字符號隨處可見。導演用白描的手法將這一事實呈現出來,體現了對往昔歲月的懷舊和當下命運的不安。
(2)戲劇——新與舊的碰撞
傳統文化符號是表現懷舊情懷的最佳工具,賈樟柯也善于使用這一手段。《三峽好人》中,來到奉節縣尋找前妻的韓三明,在渡口看見了一位表演噴火絕技的川劇演員。川劇已有上千年的歷史,它承載著地域的文化內涵和歷史記憶,導演運用這一文化符號來象征三峽古城的悠久歷史。而在一家飯館內,三名戲曲裝扮的人物圍坐于桌子旁,手里玩著游戲機。傳統與潮流在這里發生碰撞,有著強烈的時代變遷感。
(3)關公——對傳統的回望
電影《山河故人》里,充滿了對傳統的回望與思考。影片里多次出現“關公”意象,其中“男孩兒扛著關公大刀游走在街上”出現了三次,而且街上的人群逐漸稀少,象征著傳統在流浪。另外一組“關公”意象分別出現在煤礦廠上和梁子的家。梁子和他的同伴下礦井前都要祭拜關公,乞求平安。多年后,梁子因患肺癌回到家鄉,重新燃起關公前的香火,祈求康復。這其中都有撫慰弱勢群體的意味,當心靈在痛苦中煎熬時,作為福祿平安的守護神——關公,實現了他神圣古老的價值意義。
2.情感懷舊
(1)友情
《小武》是一部真誠的電影,每個人都能夠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都做過扒手的小勇與小武是好朋友,但改革開放后,小勇依靠販煙和開舞廳瞬間致富,從而擺脫了舊日的扒手角色,社會地位獲得空前提高。而小武依然從事著舊業,兩人懸殊的社會地位決定了曾經的友情必將解散。小武得知小勇要結婚但沒有請他而感到懊惱,詢問之后得到小勇不耐煩的回答:“確實是忘了,就是忘了。”小武的落魄是身份轉化之后帶來的尷尬,昔日的友情被時代的浪潮打翻在地。
(2)愛情
《三峽好人》頗有紀錄片的味道,賈樟柯把三峽的變遷保存在銀幕上,向未來講述著這塊古老土地上的歷史。沈紅費盡周折找到多年未見的丈夫時,發現他已經有了情人,時間和地域的差異使兩人的關系沒有了復合的可能,最終兩人在三峽大壩前黯然分手。 “社會生活的外表和內里、個人身份和內心世界的統一性是賈樟柯電影的關照中心,而這些又通過個人以及與他人的關系連為一個整體。”郭斌、丁亞玲與沈紅這一組三角戀糾葛在社會的外層,而郭斌為了生計不得不轉換身份的無奈與沈紅為了尊嚴放棄丈夫的痛苦被時間的生疏潛藏于內心。兩人的愛情也像三峽古城一樣,永遠淹沒在歷史的記憶中。
(3)親情
“母親”給予人生命,是一切命運與生活的開始。《山河故人》里的張到樂從小失卻母愛,19歲的他在孤獨與彷徨中決定去找尋母親。多年的異地相隔使兒子對母親的記憶愈加模糊,游蕩澳大利亞的他雖然住著別墅,享受著優越的物質條件,但精神卻一直在流浪。“我想,或許疼的時候,才能感受到愛。”這一句臺詞是在遭受異地漂泊之苦后發自內心的感嘆。失去母親的愛,也可以理解成是失去故鄉的根,流浪的辛酸或許只有回到生命最初的故鄉,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
(二)真實的生活
真實的生活是平淡的,正如賈樟柯所說:“我們關注人的狀況,進而關注社會的狀況。我們還想以文載道,也想背負理想。我們忠實于事實,我們忠實于我們。”
1.靜止的命運軌跡
《站臺》有著極強的象征意味,講述了一群對未來無限憧憬的歌舞團青年,為生計在社會上努力奔波,最后不得不安于命運的故事。影片的兩對情侶:崔明亮和殷瑞娟,張軍和鐘萍,都懷揣著走出汾陽小城、走向世界的夢想。但現實卻那么不堪,他們經歷了青春的狂歡,內心開始慢慢成熟,最終接受現實生活。在影片中有這樣一段情節,二勇在張軍的家里聽到廣播后有一段對話,問了一通后,又回到原點,頗有些宿命的意味。影片最后,當載著文工團的那輛破舊大巴駛回汾陽時,標志著年少的熱血宿命般歸于平靜。
2.平淡的人生旅途
賈樟柯影片中對日常生活的認識,主要是依靠碎片化的故事情節來消解事件的邏輯性,緩和緊張的戲劇沖突。在文學的閱讀活動中,讀者的鑒賞可以使文本實現更高的價值,正如姚斯所言:“一部文學作品并不是一個自身獨立、向每一個時代的每一讀者均提供同樣的觀點的客體……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樂譜,在其演奏中不斷獲得讀者新的反響。”這種理論同樣適合于影視語言,彼此關聯不甚密切的故事情節拼合在一起,消解了影片的戲劇沖突,觀眾心理的緊張感隨著緩慢的故事節奏沉靜下來,從而形成“虛靜”狀態。如《站臺》中的一個片段:“瑞娟一個人在辦公室聽著收音機中的音樂跳舞,騎著摩托車平靜地行駛在灰色縣城中。”這段情節和影片的前后并沒有太強的聯系,而是橫空一筆將故事敘述的連續性截斷,從而轉變了觀眾的心理預期。
三、賈樟柯電影的人文反思
賈樟柯電影側重于關懷中國民眾的心靈,把這種人文關懷置于中國時代變遷的浪潮中仔細審視,可以以此發掘出賈樟柯電影帶給我們的現實意義。
(一)中國社會集體的心靈顫動
賈樟柯的作品意欲表現在時代脈搏的影響下,中國社會集體的心靈顫動和精神困惑。改革開放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城市的高效便利吸引著無數的鄉村勞動力,他們懷揣著對夢想的激情,渴望憑借著努力去贏回物質上的豐裕。但生活的現實讓他們承受著失落、無力與痛苦,不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過程都會是同樣辛酸。《世界》里,日夜奔波在“世界公園”里的成太生,依舊是城市中的流浪者。《山河故人》里的張晉生雖在澳大利亞置辦別墅,有了立足之地,但始終無法融入異國的生活。從賈樟柯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不同身份的人物生活中,都有一種極其普遍的情感流露——與初心愈加疏遠的孤獨。
(二)人際情感的追尋
賈樟柯善于捕捉掩藏在人際關系下濃厚的情感,向我們展示平淡生活中最真摯的人文情懷。
1.人類生命的尊嚴
“在任何一種情況里面,人都在試著保持尊嚴,保持活下去的主動的能力。”《站臺》里的韓三明不善言談,目不識丁,為供妹妹上學與煤礦廠簽訂“生死合同”,他好像是被命運遺忘的孤兒,表面上木訥與懦弱。但是當他單薄的身影走上蒼涼的黃土高坡時,一種生命的沉重與堅守才猛然喚醒了觀眾。原來他并不懦弱,而是以一種沉默的方式去詮釋他對生命的尊重。《三峽好人》里的小馬哥是個玩世不恭的混混,為“討活路”跟著一群社會青年去打架,結果不幸喪命。舉目無親的他只有結識不久的好友三明為他料理后事。這樣的人物在我們現實的世界中不會被注意,忙碌的社會更無暇顧及他們的存在。但是賈樟柯態度沉靜,用淡然的筆法描繪了在時代變化中國民的生存方式,表達了對人類生存本能的尊重。
2.人類本性的善良
多數人面對生存環境的變化,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回應著這種變化,漸漸忽略人本性中的善良,但這份善良是永恒的,它從未改變。
三峽工程便是當代中國的一個縮影,“老縣城已經淹沒,新縣城還未蓋好,一切該拿起的要拿起,一切該舍棄的要舍棄。”《三峽好人》中,小馬哥的一句戲諷:“現在奉節哪還有什么好人啊!”他不相信三峽有好人,其實是他忘了自己就是好人。因打架落魄于拆遷廢墟上的小馬哥被三明救起,兩人在飯館里結下江湖友誼,小馬哥知恩圖報,仁心猶存,在時代洪流的沖刷下,顯得愈加生輝。 此外,家鄉被淹的摩的小哥,旅店面臨拆毀的蒲扇大叔,為生活做了妓女的奉節少婦,我們看不到他們人性中的邪惡,反而呈現出他們對生命的堅守和頑強,黝黑的皮膚和深壑的皺紋在陽光下熠熠生輝,在雜亂的古城和飛揚的塵土中流淌著人性本有的善良。
綜上所述,電影導演賈樟柯是一位有著社會良知的文藝工作者,他不趨附于現代電影的華麗浮躁,不跟從于快餐消費的票房比拼,而是長年如一日,堅守著藝術所擔負的最高價值追求——人文關懷。他把鏡頭對準時代變革下中國普通民眾的生活,在緩慢的節奏中勾畫百姓的生存狀態,通過外在的藝術形式來呈現他對生命的關懷與思考。他相信變動的背后有著從未泯滅的人性光輝,他所追求的情感是當下國民共有的生活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