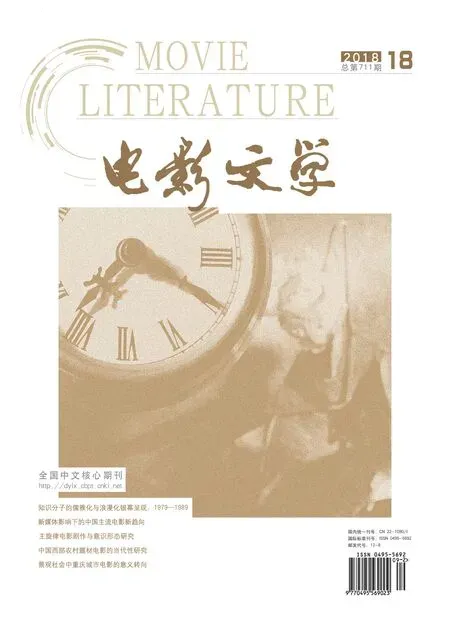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長江圖》《路邊野餐》之詩情與哲思
朱 慧
(中央民族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北京 100081)
戲劇電影與詩電影代表兩種不同美學方向的電影形態,導源于對電影是戲劇本性還是抒情詩本性的不同理解,其概念闡釋涉及對電影本體論的辨證。回顧中國電影百余年發展歷程,不難看出,戲劇性敘事一直占據著影片結構中心地位,成為中國主流電影敘事傳統,其主要功績在于締造了一系列帶有時代歷史特色的家國神話、道德神話與票房神話等影像傳奇,無論是早期背負的改良社會、教化民眾等社會功用主張,還是當下以大眾娛樂為導向的商業片濫觴,戲劇性電影更多指向與迎合的是一種集體話語與狂歡。相較而言,詩意電影在歷史發展長河中只能屈居一隅,然其雖脈感微弱卻也具備著綿亙影史的持久生命力,它以一種突出個體生命意識流動、淡化外部情節沖突的私人話語風格,呈現出相較戲劇性這一主流敘事傳統下的潛行泛泭之姿。2016年上映的兩部當代佳作《長江圖》與《路邊野餐》,不僅讓我們看到了詩意電影在其堅守的電影美學方向上的突進,更流露出對人歷史生存情境的西方現代性哲思情感體悟。基于此,本文試以此兩片為互文性參照,探尋中國當代詩電影在詩意敘事結構中呈現出的共同美學表征,及其映現出的獨特藝術形態氣質。
一、祛幻與入幻:虛實相生的反線性敘事結構
戲劇性敘事偏向表達外部現實,詩意敘事則注重描畫心理現實,由于對待現實關系的角度不同,導致影片最后整體敘事風格面貌呈現的迥異之態。詩電影主張電影應像抒情詩那樣達到“聯想的最大自由”“使想象得以隨心所欲地自由馳騁”“應當擺脫與情節的任何聯系”,這種淡化外部戲劇沖突的電影美學觀,主張通過鏡頭畫面與蒙太奇的重組來結構影片的人物心理時空邏輯表達,從而提供超越外部情節理性發展的詩情畫意。簡而言之,戲劇性敘事倡導故事外部情節流動的線形時空敘事,注重故事發展背后的邏輯推理與理性經驗,傳承著現實主義與寫實風格,影片基調是祛幻的;而詩意敘事則弱化情節與理性,呼喚著知覺經驗的回歸,肯定人物心理時空的非線性表達,人物主體是唯心的感性存在,故事演繹與情感表達則呈現出一種入幻的審美訴求。
盡管外部現實不是詩意電影言說的重點,但作為引領觀眾進入人物內部情感世界的入口卻也必不可少,只是筆墨分量較少,因而在內部情感的濃厚隱喻與外部情節弱化簡述的結合下,詩意電影營造出虛實相生的間離張力與復式敘事審美效果。如影片《長江圖》通過“溯洄從之”這種時空結構的逆推倒轉,構建出由實入虛、虛實相生的雙向發展時間軸。在故事構架的現實情境中,男主人公高淳與商人羅定協議將10噸魚苗運送到宜賓,然而隨著故事發展的推進,這一現實情境早已被另一重情愛詩意時空沖淡虛化為遠景。影像利用大量遠景構圖,建筑了一個不斷流動、不斷變幻、不斷生成的世界,隨著溯江之行中高淳視角中展現的女主人公越發年輕的容顏,我們知道這里時間不是前邁而是后退的。
《路邊野餐》則在影像開頭借用《金剛經》中一段引語統攝全片的時空觀,其中“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成為全片時空敘事中表現虛無主義情韻的“詩眼”。影片前半段以“祛幻”的敘事情節為主,男主人公陳升年輕時因斗毆傷人而入獄九年,用他呢喃在嘴邊的現代詩可表達為“沒有了心臟卻活了九年”,這期間妻子與母親相繼離世,對妻與母的負罪意識衍化為對侄子的責任意識,由此陳升踏上了去鎮遠接小侄子衛衛回家的旅程。隨著旅途的深入,影片正式進入“入幻”的詩意時空情境,在蕩麥,已逝的妻子在理發廳為他剪發,長大后的青年衛衛騎著摩托載他到河邊,這里記憶、現實、未來同構交錯為當下同一時空情境,“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得其“不可得”之顯。“在時間中,每個瞬間只有在消滅前一個瞬間——自己的父親,從而使自己同樣快地被消滅的情況下才存在。過去和未來都像任何一個夢一樣微不足道,而現在只是兩者之間沒有維度和綿亙的界限”,詩意敘事手法實現了影像時空表達的自由化,這里時空可以倒轉逆行,可以停滯不前,亦可與未來和歷史發生多重折疊碰撞,過去、當下與未來之間的嚴格界限得以融通,它們相互消解而又相互構筑。記憶與現實的虛實真假無須考辨,因為詩意敘事最終實現的不是戲劇性情節發展的真實,而是在入幻與祛幻的復式敘事結構中抵達情感的真實。
二、癔癥式吟游:負罪意識詢喚下的抒情囈語
詩意電影中,深層記憶的綿亙永恒性與現實表象的破碎易逝性構成對比,當下生存情境如此乏味,未來又如此虛無,唯有珍貴的情感記憶聊可慰藉,成為主人公們逃離當下的生命出口。換言之,唯有歷史記憶可以重整修葺現實這座已然崩塌的生存廢墟,抵制、對抗時間對生命情感意識的無情沖刷汰換。主人公們對歷史與記憶一再表露出的這種深切歸返欲望,毋寧說是受到尋鄉返根意識的潛在召喚與驅動。《長江圖》中高淳逆水溯源,最終抵達長江源頭楚瑪爾河,回望記憶中的江水在歷史歲月中翻騰時不覺熱淚盈眶,《路邊野餐》中陳升由物理空間層面上的家鄉踏入精神情感上的記憶之鄉,事雖有殊,其理則一也,他們在入幻與祛幻間上演的茫然迷醉之態,顯露出人與故土分離的情感創傷。由于長久失去了與故土的經驗性關聯,個體生命意識中沉淀的懷鄉意識、歷史意識、歸返故土的原始欲望被一再反復點燃激發,這種歸鄉渴求造成人當下生命激情與生命欲望的龜縮、退卻,自我意識與當下身體所處時空再也無法結合、呼應、交流。
詩意電影中的主人公便表現出這樣一種人與自我分離的“癔癥”式病態人格特質,他們意識朦朧,軀體感官功能缺失,與當下生存情境處于“感官剝奪”的隔離狀態,對自我當下身份無法認可,行為軌跡猶如漫游癥患者。那么,為什么主人公們與當下時空發生了交流障礙?為何會生發出一種所思在遠方的歸屬感?為何當下如此不堪、面目可憎?以上種種雜疑也許可從主人公們身掮的負罪意識揣得端倪。《路邊野餐》中這種負罪意識在情節敘述實線上指向母與妻,在詩意敘事虛線上則指向宗教上的“人生而有罪”與因果輪回觀。《長江圖》中這種負罪意識更是指向多元對象,首先,就故事現實層面而言它指向亡父;其次,這種負罪意識由“家”的人倫情懷指向“國”的社會發展批判意識,不難看出影像涉及三峽大壩修建帶來的生態環境、移民拆遷等沉重社會歷史問題;最后,通過安陸與塔中佛僧的辯難,也可看出作者對人群兼具“負罪”與“賦罪”的雙重情感,安陸質問佛僧“什么是罪”,她覺著“活著就是罪,因為只要你活著,就要跟別人爭奪生存的空間和資源”,這里罪與無辜二元違戾,罪是生存宿命,注定清繳無辜。
在負罪意識的體認與壓抑下,主人公們對當下的逃遁欲望、對回憶的歸返渴望也就不難理解了,“一定有人離開了會回來/騰空的竹籃裝滿愛……”“我從未體驗過由衷的快樂/心滿意足如在母親懷中……”(《長江圖》),“我”對當下的鄙憎毋寧說其實就是對自我的鄙憎,“我”想逃離當下其實就是想逃離自我,這種對當下自我身份的否定與厭惡產生了自我分離、自我撕裂。依據拉康的鏡像理論,自我與他者的差異感知是確定主體身份的前提,這里負罪之我成為自我的他者,確認這種異質性才能獲得主體身份,然而,“我”是厭惡排斥這種異質性他者對自我的填充的,“我”排斥成人世界必須承擔的各種缺陷與不完滿,意味著“我”對獲得主體身份認知的棄權,因而就某種意義而言,“我”是拒絕成長的。回憶中的無罪狀態猶如母體般溫存,恰如嬰兒誕生之初的自我完滿圓融之態,這種無罪之“我”,沒有任何缺憾、缺失與缺陷,是“我”所渴望回歸的自我同一狀態。然而,這種回歸欲望必定要陷入失落,因為成人之我既已感知負罪之我的異質性,便丟失了自我與他者的融合統一狀態,又如何再逆反成長為孩童,重獲原初那種未分化的存在?這種悲劇性也便催發了主人公們自我見放的癔癥式吟游,唯有脫離對當下在場的感官知覺,才能擺脫自我撕裂帶來的情感苦痛,囈語此刻是生命意識深淵的回望呼喊,是被壓抑、被禁錮、被封存的心理能量的無意識釋放。對自我同一性回歸落空產生的焦灼感、喪失感、受挫感,唯有在這種漫游囈語中,才能得以短暫地宣泄、緩釋、撫慰。
三、激情的疏離:虛無主義暈染下的存在之傷
歸返欲望的落空使得精神主體陷入一種“無家可歸”的流亡狀態,“我”既無法再次獲得生命元初的自我統一圓融感,也無法抵達碰觸生命存在的終極意義,“通過生成是得不到什么的,在一切生成中并沒有一種偉大的統一性可供個體完全藏身”,在這個異己的世界中,“我”對自我異化與分離的一次次抵抗在負罪與必死面前最終不過都是徒勞。對反抗價值的貶黜消解了人的存在意義與價值目的,而目的論的喪失引發出虛無主義人生觀。具體到電影文本中便體現在人物行為動機的生成與消解上,《長江圖》中無論是世俗動機上的販運協議還是詩意精神空間中對女主人公的尋覓,都在男主人公高淳突然被刺身亡,或言在他抵達長江源頭楚瑪爾河,見證到那塊象征生命源頭與死亡、起點與終點的墓碑前清零了。《路邊野餐》中陳升由凱里到鎮遠的旅程肩負多重使命,他要接侄子衛衛回家,替女醫生跟老情人慰問告別,轉交一件衣服與一盒磁帶,然而這多重目的最后一件也沒有達成,人物對生命的虛無體悟便在這種對目標的棄尋與抵達失敗中實現了同構。
就此,虛無主義成為詩意電影呈現出的主要美學范式與原則,在虛無主義哲思情感的暈染下,主人公們呈現出欲望野性退化的、與生命激情相疏離的病態生命面貌。需要注意的是,生命激情的抽空不僅影響了主體人物形象的構建,它最終扭轉的是影像文本整體的抒情基調,實現了由“抒情”到“疏情”的情感轉向。換言之,影像在不斷構筑頹廢、傷感、失落的詩情詩意時,也在不斷反噬、消解、稀釋它,以此走向平靜、淡漠、一切皆空的虛無主義情韻。這種抒情消解策略不僅體現在前文提到的人物行為動機的最終歸零上,還體現在影片對充斥其中的現代詩的處理上,兩部影片皆以主人公沉浸過往的回憶之態呈現詩歌,相對于追憶狀態中所指涉的抒情對象,語言符號堆砌而成的詩歌永遠只是對情感記憶的一種遲到表述,而影像畫面符號既在描繪“此情可待成追憶”的此時此地此情,亦在呈現“只是當時已惘然”的彼時彼地彼情,就此,傷逝成為詩電影表現的主要敘事情境與抒情癥候。這也契合了華茲華斯的經典詩論,他認為詩“起源于在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正是這種“在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使得詩電影主人公在入幻與祛幻的往返游離間,上演出“平靜→抒情→回歸平靜”的作詩狀態與情感波動回路,影像情感基調最終由隱喻構建的濃厚“抒情”滑向“疏情”的平淡、悠遠、虛無之境。
四、結 語
“從模仿外部世界的藝術,走向了本體論的詩(藝術),詩不再是去意指實在的絕對本體,而是生存本體自身的詩化,是感性存在自身的詩意顯現。”以此觀照,相較電影誕生之初對外部物質世界的記錄、再現、模仿,詩意電影實現了由“外”向“內”的場面調度,聚焦于對人內心感性世界的詩化呈現。在戲劇性故事片、商業片宰制電影市場的今天,《長江圖》與《路邊野餐》以獨特的藝術形態氣質彰顯了詩意電影的反抗、獨行之姿,在對現代人生存情境的詩化表達與現代性哲思觀照下,沉靜而自信地開拓著電影美學意蘊表現手法的新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