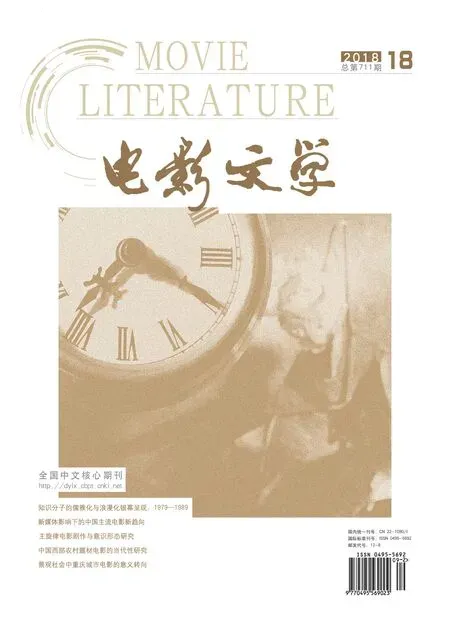解讀《寂靜之地》中的性別話語
張宋濤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加拿大 溫尼伯 MB R3T 2N2)
繼在北美收獲成功的票房與口碑之后,《寂靜之地》于2018年5月18日在中國內地上映。雖然該影片在中國的票房并不如在北美那么理想,但自上映以來連續四天蟬聯票房前三的紀錄已經足以反映這部影片的名聲與口碑。可以說該影片兼具恐怖片嚇人的元素與藝術片的審美價值,然而這部影片所建構的性別話語卻是那樣的保守與刻板。基于此,筆者通過性別研究與女性主義的解讀方法對該影片進行多角度的文本細讀以試圖剖析影片呈現出的性別表述。本文認為該影片呈現出極為鮮明的二元對立式的家庭性別結構,在其間父親與兒子,母親與女兒分別被賦予了截然相反的所指。
一、恐懼與溫情之外
影片的恐怖來源于兩個元素:一個是兇殘而一招致命的神秘生物;另一個則是令該生物極度興奮的“聲音”。影片里的未知生物對聲音異常敏感,它們以一切發聲生物為攻擊對象,因而人類首當其沖。面對死亡甚至滅種的威脅,影片所聚焦的一家人因此不得不在噤聲中尋求逃離與抗爭之法。因而他們的“聲音”作為災難的誘餌成為整個故事情節的核心動力。故事正是在一次次地“制造聲音”和“躲避怪物”的捉迷藏式的劇情結構的展開中拉扯著觀影者的神經。影片寂靜如死般的基調為觀眾營造了一種強烈的壓抑感,而發聲必死的環境法則則又給這些與主人公一同深處寂靜的觀眾一種不自覺的畏懼聲音的代入感與參與感。影片正是借助觀影主體與電影之間的這種心理學上的聯系,成功地放大了觀影主體的恐懼。這也正是該影片作為恐怖片類型所表現出的獨到之處。
此外,影片還力圖表達愛與親情。在經歷家中最小的一員被未知生物獵殺之后,全家都籠罩在哀傷、矛盾與無助之中。可以說這一開場的遭遇所帶來的悲傷感貫穿著整部影片。而當全家人開始正面遭遇怪物時,躲避怪物襲擊時的每一次重聚都攜帶著無限的感動,但每一次短暫的溫馨卻又隨即面臨著被迫分離。父親為解救子女而犧牲生命的那一刻則將故事的情感的表達推向了高潮。這個家庭在威脅面前所展現的強烈的感情上的凝聚力不斷地沖擊著觀眾的內心,而伴隨著哀悼式的背景音樂,深刻而持續的感動與揮之不去的緊張相互交織,反復糾纏。
或許也正因此,影片在敘事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更深層次的社會話語則被悄然地掩埋至了一場緊湊而緊張的神經盛宴以及情感的發泄與滿足之間。而筆者則試圖從影片所編織的這些重重表象之間,揭開它所聚焦的這一美國典型核心家庭典型的矛盾式的性別話語。恐懼與溫情之外,呈現的是另一種表述。
二、秩序與反秩序
影片以一段線性敘事組合開場:六組環境鏡頭過后,一家人在超市里準備必需品。母親為生病的大兒子尋找藥物。小兒子伸手拿玩具火箭,火箭不慎掉落,姐姐接住火箭。父親出場,站在門口。將走時父母發現小兒子手里拿著玩具火箭,于是父親謹慎地從小兒子手中拿過玩具卸下電池并把玩具擱置一旁。爾后姐姐把火箭給了弟弟,但在大家都走后小男孩卻拿走了電池。回家的路上火箭發出響聲,父親跑去營救但為時已晚,小男孩被怪物獵殺。
在這段線性敘事組合當中,水平與縱深調度幾乎參半的交叉剪輯一方面交代了人物所遭遇的由環境所施加的某種壓迫式的生存境遇;另一方面又強調了人在適應和改造環境上所做的努力。當小男孩走過廢棄的汽車時,當攝影機以上帝視角觀望在沙地上光腳徒步行走的一家人時,攝影機采用的是水平調度,呈現出了某種扁平的、頹廢的、被壓制的生存狀態;而其間所穿插的縱深調度則又將這家人所開辟的生存之道嵌入絕望的歷史與環境之中,暗示著人在這種生存境遇之中所力圖爭取的些許的可能與希望,一種建立在父親所領導和維系的以“別出聲”為秩序法則之上的生存希望。
影片中父親的出場被安排到所有人之后,且正是玩具火箭險些掉落的時刻,同時也正是光源的所在地。這一安排顯然賦予故事中的父親以“父神”般的形象。可以說,影片中的父親這一角色本身就代表著秩序。當發現小兒子手里拿著玩具火箭時,他如遇怪物般小心翼翼地出面阻止;當大兒子模擬開汽車時,他的到來讓兒子垂頭放棄……他們住所周圍的各個角落都安裝有監控,父親在工作室內通過這些監控觀望,監視著周圍一切可能發生的危險,當然也必然監視著他的家人。同時他永遠都是以一種高大、穩重、深沉而孤獨的形象出場,譬如他坐在瞭望塔頂悼念逝去的小兒子時的一段場景。這段鏡頭中攝影機采用仰拍的角度,上移,首先呈現出他的背影形象,接著仰拍,呈現出側面形象,居畫框左上角。類似的人物調度還如他在地下工作室工作時的場景。影片中對父親所做的人物調度是最為豐富且最為正面積極的,從而進一步指涉,強化了父親的律法式的角色。從情節邏輯上講,秩序是為了躲避怪物的襲擊,父親則在影片中自然而然地承擔起了踐行和維系這一安全鐵律的責任。影片正是在這些敘事情節的呈現中,在嫻熟精到的調度上,在影片邏輯的展開上將父親秩序般的存在表露無遺。
如果說父親所代表的“秩序”意味著和平、安全和穩定,那么故事的推進、災難的降臨也必然需要“反秩序”的存在。當然這是一種基于影片邏輯發展而言的表述。而另一種表述,一種類似克里斯蒂娃式的表述則是:正是那種從秩序中分離出來的另一種存在確保了崇高的、超越性的父系秩序法則的維系。筆者之所以將兩種表述都呈現于此,是因為影片在將父親設定為秩序般存在的同時卻將母親和女兒安排成了“反秩序”的存在。父親高大偉岸的“父神”形象正是通過“母女”直接或間接制造的“另一種興奮”而得以確立。因而這個在災難面前如此凝聚、如此深情、如此虐心的家庭確乎是將這種凝聚、這種深情、這種虐心建立在一個傳統的二元對立式的兩性性別結構之上。
影片開場弟弟的死是由姐姐間接造成的,因為她把玩具給了弟弟。而姐姐又是出于對弟弟的同情與寵愛才把玩具給了他。這是一種基于情感而導致的對秩序的破壞。如出一轍的是,母親也是受到情感的驅使而走進小兒子的房間獨自垂淚,但此時的她已經接近臨盆,行動極為不便。臨走時分娩發生,急忙下樓的她手里還拿著小兒子的照片,結果下樓時腳踩中鐵釘,相框掉落打碎發出聲音因而招致怪物。從這里不難發現,無論是上樓悼念兒子,還是臨走時拿走相框,這些因情感而牽扯的行動都是災難發生的直接原因。此外,在當姐弟倆站在谷堆塔頂上面給父親發求救信號時,正是姐姐感情用事與弟弟發生爭執才導致弟弟不慎掉落谷堆而招致怪物。這三處致命性的失誤皆是或直接或間接地由故事中的兩個“感性著的”女性所導致的。同時當問題發生時,父親永遠是缺失的,以致他永遠都是以營救者的英雄形象出場。而當他在場時,盡管問題也會出現,譬如兒子不慎打翻燈盞,他卻能及時解救。父親的在場因此意味著安全;相反,他的不在場則預示著危險。
除了女性的情感作為秩序的破壞者之外,母性的身體也在影片中表現出某種“反秩序”的意指。鐵釘因何而來?是接近臨盆而行動不便的母親提著衣服上樓時把裝衣服的袋子掛住了打彎的釘子頭而把它牽拉起來的。母親的身體在制造和遭受鐵釘的兩組動作中都被賦予明顯的身體上的“反秩序”的指涉。正如西方女性主義思想家Margrit Shildrick所指出的那樣,母性的身體在某些西方文化語境下被視為“非秩序”(disordered)的甚或是“妖魔化”的存在(monstrosity)。
三、父與子:男孩成長的秘密
如若母親和女兒是需要被規訓,被保護,被秩序化的與秩序相對立的主體,那么兒子作為父系權利的沿襲者與替代者必然要經歷從母系空間出走而進入父系經驗的過程,這便是影片所昭示的關于男孩成長的秘密。
有趣的是影片中的兒子本是羸弱的、膽小的,他不愿跟隨父親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也就是說,他從最初,從最伊始的階段是和母親緊密連接的,他屬于那個襁褓式的陰性母系空間。當父親要求他和他一起外出學習求生技能時,他竭力抗拒。而母親是這樣勸說他的:“你學會了這些技能會很有用的,它能幫助你照顧自己,當我老了,牙齒掉了,頭發白了,你也能照顧我。”所以他必須走出這個原初的空間場域而完成與父親的連接,完成男性氣質的建構,因為母親需要他來照顧,未來的秩序需要他來維持,這是他成長的必經之路。與兒子抗拒外出所截然相反的是女兒極力央求能與父親外出,可是父親拒絕了女兒的要求。如同他拒絕讓女兒進入地下工作室一樣,他再一次以愛與保護的理由拒絕讓她進入他的領域,他的歷史。父子倆整裝待發與母親臨別時的這段場景在布光、構圖以及視點上的處理做得別有用心。它采用的是自然光,在光源的左右兩邊分別站立著兒子與父親二人,父親則更靠近光源。此時的女兒與父親發生爭執,成了某種介入般的他者化的存在。在遭遇拒絕之后,她氣憤地走出兩父子所在的位置背著光朝著相對昏暗的另一條岔路走去。此時的母親站在正對著兒子且稍有些許距離的對面凝視著這一切,她對兒子投以鼓勵,對女兒表達無助。這套精細完美的鏡頭語言可以說非常成功地呈現了這個典型的美國核心家庭成員之間的角色劃分與成員關系,也極其成功地對這對父與子臨近的行動賦予了某種正面的積極的價值指涉,同時當然也成功地強化了影片在性別結構上的設定。正是在這次外出探索的過程中,這個原本膽小懦弱的男孩成長了起來,這使得他成功地燃放了焰火,完成了對母親的最后一分鐘救援;也使他堅信父親總會找到他們,前來解救他們;同時在父親大聲叫喊,犧牲自己的那一刻他也不摻雜任何猶豫地、果敢地發動了汽車帶著姐姐逃離了怪物。在影片故事中父親除了作為引導者之外,他對男孩而言還意味著欲望與本能的成全者。父親把兒子帶到河邊,帶到瀑布下面以此成全了兒子“言說”的本能。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本能的釋放是經由父親所驗證過的一種絕對無害的釋放,是一種經由科學和理智所指導和支配的本能的變奏。可以說,父與子的“外出”這一情節線索濃縮了男孩們成長的邏輯,一種建立在父系標準之上的經由承繼他的權利,進入他的歷史,追隨他的腳步而從男孩走向男人的路徑。
四、結尾的隱喻
影片結尾母女倆并肩抗擊怪物的行動與“木蘭從軍”的中國傳說有著極為相似的性別隱喻,即戴錦華所揭示的“花木蘭式的隱喻”——女人以英雄的身份出演于歷史的唯一可能,仍是父權、男權衰亡、崩塌之際。同樣的結論還出自于加拿大社會學家Murray Knuttila。Knuttila對二戰期間加拿大的性別結構做過這樣的分析:“加拿大的經濟之所以在二戰期間得以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持續增長的女性勞動力對二戰時期加拿大經濟建設的參與。”換句話說,也正是投入邊疆的男子們在經濟建設上的讓位才給了女性們投入社會歷史建設的機會。在影片的結尾,也正是父親的犧牲才使得保衛家園的權利得以讓渡給了母親和女兒。而這對母女之所以能夠擊敗兇殘的怪物,也在于女兒終于得以進入父親的場域,得以獲取了父親的經驗知識并找到了怪物的致命弱點。
從以上的論證不難發現,《寂靜之地》在北美的成功絕非偶然,因為它不僅在電影敘事上表現出獨樹一幟的風格,更重要的是,它顯然昭示著美國傳統家庭價值觀,傳統家庭性別角色與性別結構的復現,抑或是關于這種家庭結構的美麗而崇高的想象。
注釋:
① 克里斯蒂娃的原話是:“若沒有性別鴻溝,沒有這種多形態的局部化也即另一種極度興奮的身體,另一種性別的笑和需要,那就不可能在象征性領域里分離出一種法則——這個唯一崇高的,超越性的法則,確保了共同體的理念和旨趣。”參見朱麗婭·克里斯蒂娃:《中國婦女》,趙靚譯,同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