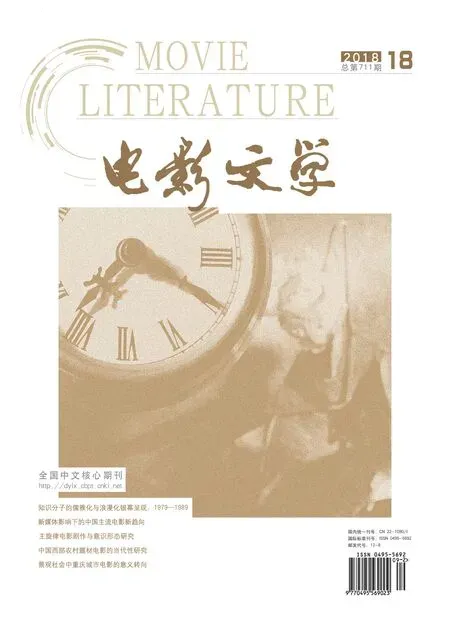主旋律電影劇作與意識(shí)形態(tài)研究
邵君立
(四川電影電視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1331)
1995年電影局的“長(zhǎng)沙會(huì)議”明確提出了“弘揚(yáng)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的創(chuàng)作方針和口號(hào),此后十年間乃至更長(zhǎng)的時(shí)間維度里中國電影的創(chuàng)作中明顯地出現(xiàn)了對(duì)這一政策相呼應(yīng)的現(xiàn)象。作為反應(yīng)之一就是自1996年開始的夏衍電影文學(xué)獎(jiǎng)的舉辦,而這一獎(jiǎng)項(xiàng)的獲獎(jiǎng)劇本的相當(dāng)部分被拍攝成片。這些電影雖然具體構(gòu)成各有不同,但其深層建置具有明顯的一致性:劇作法和意識(shí)形態(tài)這兩種力量的博弈。近十年間的華表獎(jiǎng)的贏家時(shí)常由這一類電影扮演,因其制作、放映、觀賞的特殊性(不完全由市場(chǎng)規(guī)律決定)也使得這一類電影在更多的時(shí)間內(nèi)、更大的范圍內(nèi),以多種方式被為數(shù)不少的中國電影觀眾看到。本文所論及的則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生產(chǎn)的具有自己明顯特點(diǎn)的中國電影。
一、形 態(tài)
有論者對(duì)這類電影根本形態(tài)的描述為:敘述內(nèi)容符合意識(shí)形態(tài)合法化功能,影像呈現(xiàn)滿足了大眾的期待與想象,并使他們的欲望得到象征性宣泄的同時(shí),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現(xiàn)了他們生存狀態(tài)以及顯示境遇的作品。也有人從電影的人物形象的角度將其總結(jié)為:貫徹中國當(dāng)代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并以塑造英雄人物形象(或正面人物形象)為主要導(dǎo)向。
在更廣闊的視野中審視這些主旋律電影會(huì)發(fā)現(xiàn)它們除了有明顯的政策催生外,“十七年電影”和“文革電影”都在不同的方向上影響著主旋律電影的創(chuàng)作。主旋律電影中占有很大比重的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如《我的1919》《國歌》《太行山上》)在敘述內(nèi)容上完全是對(duì)“十七年電影”在敘事上的繼承。而以樣板戲?yàn)榇淼摹拔母镫娪啊泵枋鋈宋锏氖址?高大全)——雖然頗為詬病——也或多或少地在主旋律電影中得到了延續(xù)。
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關(guān)于意識(shí)形態(tài)的論述在本質(zhì)上揭示了主旋律電影在不同模式中的靈魂實(shí)質(zhì):意識(shí)形態(tài)通常被感受為自然化和普遍化的過程。通過設(shè)置一套復(fù)雜的話語手段,意識(shí)形態(tài)把事實(shí)上是黨派的、論爭(zhēng)的和特定歷史階段的價(jià)值,顯現(xiàn)為任何時(shí)代和地點(diǎn)都確乎如此的東西,因而這些價(jià)值也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變的。伊格爾頓的這個(gè)說法比起中國的論者似乎更加深刻——在主旋律電影中所彰顯的意識(shí)形態(tài)有一種傾瀉和蔓延的力量,時(shí)常并非完全敘述著觀者的本在情感。對(duì)這個(gè)問題的解決是通過“設(shè)置一套復(fù)雜的話語手段”來實(shí)現(xiàn),而所謂的“設(shè)置一套復(fù)雜的話語手段”在主旋律電影的創(chuàng)作中就是一個(gè)劇作問題了,但這個(gè)劇作問題要解決的是如何讓故事講述意識(shí)形態(tài)的東西。這里的關(guān)鍵問題是:主旋律電影中故事和命題之間不是簡(jiǎn)單的內(nèi)容與主題的關(guān)系——電影和其他文藝作品一樣都面臨著如何闡發(fā)主題的問題——它的敘事是十分小心謹(jǐn)慎且刻意地選擇著意識(shí)形態(tài)許可的范圍進(jìn)行創(chuàng)作。在這個(gè)過程中意識(shí)形態(tài)和劇作這兩種力量彼此是有待于調(diào)和的,但這種調(diào)和無法實(shí)現(xiàn)的時(shí)候往往犧牲的是電影劇作。
如果梳理一下主旋律電影,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它的三個(gè)方向:民族歷史話語的再敘述、后革命時(shí)代英雄的贊歌和經(jīng)濟(jì)中國的模范傳奇。這三個(gè)方向上的創(chuàng)作排序是有其固定方法的,它們所體現(xiàn)出的意識(shí)形態(tài)和劇作之間的關(guān)系有所不同:如果說意識(shí)形態(tài)的力量愈被強(qiáng)化劇作的空間愈有限的話,那么按照這個(gè)順序劇作者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所獲得的自由是呈現(xiàn)遞增的。
二、民族話語的再敘述
在主旋律電影當(dāng)中這一類是最經(jīng)常被制作和被觀看的,其中最開始的就是革命歷史題材電影,逐漸擴(kuò)大到“革命歷史史前史”。1949年的政治變革非常迅速地影響到了文藝創(chuàng)作,除了政治激情對(duì)創(chuàng)作者的自發(fā)的鼓勵(lì)外,其后迅猛而至且此起彼伏的政治斗爭(zhēng)越來越教育了創(chuàng)作者,經(jīng)過幾十年的摸爬滾打,電影創(chuàng)作者們積累了一套這類題材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yàn)。到20世紀(jì)90年代中期在又一波政治斗爭(zhēng)過去若干年之后,全民投入到一整套經(jīng)濟(jì)說辭中,國家話語終于發(fā)現(xiàn)在92年講話后的經(jīng)濟(jì)高漲中,一種共同性的精神被經(jīng)濟(jì)大潮沖擊殆盡。吉爾茲(Clifford Geertz)所認(rèn)為的研究意識(shí)形態(tài)的社會(huì)決定因素的兩種主要的路徑——利益論和張力論——能夠極好地解釋決策者助推主旋律電影創(chuàng)作和創(chuàng)作者進(jìn)入其中的動(dòng)機(jī)。吉爾茲認(rèn)為,從利益論看來,意識(shí)形態(tài)乃是一種面具或武器;而對(duì)張力論來說,意識(shí)形態(tài)則是病癥和處方。以利益論來看,意識(shí)形態(tài)的主張要在爭(zhēng)取優(yōu)越的廣泛斗爭(zhēng)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依據(jù)張力論,則是在修正社會(huì)心理失衡的漫長(zhǎng)努力背景中來考察。在前一種背景中,人們是追逐權(quán)力,在后一種背景下,人們則是逃離焦慮。90年代中期開始,來自國內(nèi)外的經(jīng)濟(jì)力量沖擊越來越強(qiáng)烈使官方和民眾都感到了震撼和猶疑,這時(shí)候雙方至少是其中的一者感到需要一種力量來凝聚作為一種集合的存在。這時(shí)候沒有什么比復(fù)習(xí)國族受難史更加有效了。《紅河谷》《我的1919》《國歌》《太行山上》這類作品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在這十年間努力向前探索,但是顧慮重重。創(chuàng)作者竭力尋找意識(shí)形態(tài)所準(zhǔn)許的罅隙,在其間游刃。馮小寧自陳創(chuàng)作《紅河谷》時(shí)“每寫一句話、一個(gè)情節(jié)都要仔細(xì)想想,符合不符合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符合不符合藏族人民的利益?符合不符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不是在弘揚(yáng)人性的真善美?”耐人尋味的是,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規(guī)律(如果把“弘揚(yáng)人性的真善美”看作對(duì)人物刻畫的追求)被作者放在三個(gè)巨大的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的“符合不符合”之后思考。創(chuàng)作之時(shí)的顧慮可見一斑!
創(chuàng)作者們?cè)谶@個(gè)探索的過程當(dāng)中有意無意地采用了一些共同的敘事策略——他者視點(diǎn)。所謂他者視點(diǎn)的主要作用,無非是提供一個(gè)相對(duì)客觀的視角而已,但是在主旋律電影的敘事過程當(dāng)中,由于其敘事動(dòng)機(jī)的特殊性往往是借用這個(gè)貌似客觀的外殼來抒發(fā)一種純粹主觀的情緒。在這里創(chuàng)作者別具匠心地選擇了外國人來作為這個(gè)歷史的見證人——無論他們?cè)跀⑹庐?dāng)中是作為侵略者還是作為中國革命的友人出現(xiàn)——最后必將為中華民族及其文明的巨大魅力所折服!
在這些電影里外國人被描畫為東方文明(中華文明)的探索者,以這樣那樣的原因被卷入中國革命史(及其史前史)。《紅河谷》中后來跟隨進(jìn)攻藏區(qū)的英軍隨軍記者瓊斯在出場(chǎng)的時(shí)候就通過旁白交代了人物的精神前史——一個(gè)受父親影響深重的對(duì)東方文明有強(qiáng)烈興趣的英國記者。瓊斯的精神狀態(tài)在整個(gè)劇情的進(jìn)展變化是微妙的。電影一開始通過他的視角把藏區(qū)奇特的人文景觀加以展示,這里只是一種獵奇的心態(tài)。他在藏區(qū)養(yǎng)病期間深切地感受到藏文明(東方文明)的迷人和藏族頭人的女兒(東方女性)的魅力。當(dāng)他傷愈歸隊(duì),跟隨羅克曼再次攜洋槍鐵炮攻入藏區(qū)的時(shí)候,一時(shí)間鐵馬金戈、血雨腥風(fēng)……最后的交戰(zhàn)在古堡的大爆炸中結(jié)束。但在藏軍覆沒之際,瓊斯這個(gè)戰(zhàn)勝國的代表卻精神分裂地走向雪山,在藏區(qū)奇景的又一次展示中跪拜在“圣山”意境之中。劇作者在這里賦予藏區(qū)的奇特自然景觀以人格力量,中國雖然在具體的戰(zhàn)爭(zhēng)中失敗了,但是在更深層次的精神領(lǐng)域取得了永遠(yuǎn)的、對(duì)敵人徹底的勝利。敘事到此如何能不讓人激動(dòng)萬分且熱血沸騰?!雖然不免有一種精神勝利法的危險(xiǎn),但因其通篇高漲的浪漫主義情懷,使得這個(gè)最終敘事——中華民族的精神是巨大不可戰(zhàn)勝的——也能讓人接受,《紅河谷》成為當(dāng)年可圈可點(diǎn)的作品。
與《紅河谷》可互為參照的是2005年制作的,是同樣表現(xiàn)中華民族抵抗外來侵略的《太行山上》。作為抗戰(zhàn)勝利60周年的獻(xiàn)禮片《太行山上》成為第11屆華表獎(jiǎng)的大贏家,且列第八屆夏衍電影文學(xué)獎(jiǎng)榜首。但除卻其中眾多的特技制作(很多并不高明——如日軍首領(lǐng)的乘機(jī),阿部規(guī)秀火焚日兵等段落的特技制作,其動(dòng)感和逼真性的水準(zhǔn)很有待提高),在劇作層面問題重重。與《紅河谷》在劇作設(shè)置一致之處在于《太行山上》的敘事中也加入了一個(gè)外來者——國際友人史沫特萊女士。史沫特萊成為這段歷史的見證人與瓊斯的見證不同在于:首先,史沫特萊始終是一個(gè)游歷式的人物,她在敘事中的角色是為寫作《朱德傳》收集材料。考究作者設(shè)置這個(gè)人物在劇作上的動(dòng)機(jī)無非也是要借客觀之口贊評(píng)朱德及中國共產(chǎn)黨挽救民族危亡的偉大,在劇中史沫特萊女士也確實(shí)說出了這種對(duì)主人公的贊譽(yù)之情。但,絲毫不令人感動(dòng)!《太行山上》這個(gè)劇作的失敗當(dāng)然是劇作讓步于意識(shí)形態(tài)的明證!在《紅河谷》中英國人瓊斯有血有肉——前史上他是一個(gè)對(duì)東方文明有強(qiáng)烈向往之情的東方迷,在敘事中他得到藏人的幫助和關(guān)心,對(duì)頭人之女產(chǎn)生愛戀之情,但國家命運(yùn)把他推到侵略者的位置上——這個(gè)客觀視點(diǎn)直接進(jìn)入戲劇矛盾之中,所以瓊斯的震撼是真實(shí)可感的,當(dāng)他歌哭的時(shí)候自然激起了我們對(duì)自己國族的情感。《太行山上》把焦點(diǎn)直接對(duì)準(zhǔn)那個(gè)時(shí)期的中共黨人,面面俱到,唯恐遺漏——開國十帥竟在劇中出現(xiàn)六位——史沫特萊的出現(xiàn)沒有任何必然性的依據(jù)和需要,當(dāng)戰(zhàn)事緊張不便再帶著這位偉大的國際友人時(shí),在曠野中史沫特萊與朱德以中國軍人的方式握別并飽含熱淚地說出:我愛八路軍。一個(gè)絲毫沒有進(jìn)入戲劇矛盾的客觀視點(diǎn)人物發(fā)出這種感慨實(shí)在令人咋舌!
這類題材的主旋律電影往往以女性的犧牲作為敘事進(jìn)入高潮的序曲和契機(jī),而高潮段落又往往以一種飽含詩情的方式噴薄而出。高潮的表述方式往往是以放棄敘事來實(shí)現(xiàn)的。在《紅河谷》中第125~133場(chǎng),頭人之女丹珠被捕、受辱、引爆炮彈與敵同亡把雙方的戰(zhàn)事推向最后的高潮,敘事在后面古堡爆炸這個(gè)情節(jié)點(diǎn)達(dá)到高潮并結(jié)束。《國歌》的敘事策略也與之相同,第50~55場(chǎng)梅香等革命女青年?duì)奚谌哲姷呐诨鹬校?6場(chǎng)田漢在回憶往昔崢嶸歲月的大寫意段落中最終完成《義勇軍進(jìn)行曲》的歌詞創(chuàng)作。這些段落無不在某種程度上激蕩著觀者的心扉,而這個(gè)時(shí)刻就是意識(shí)形態(tài)成功命名的時(shí)候。意識(shí)形態(tài)命名情境結(jié)構(gòu)的方式是包蘊(yùn)其內(nèi)的對(duì)待這些情境的態(tài)度乃至一種承諾。其風(fēng)格是華彩的、生動(dòng)的和有暗示性的:通過科學(xué)所回避的語義學(xué)手段來表達(dá)道德情操,它追求喚起人們的行動(dòng)。
三、后革命英雄時(shí)代的贊歌
這類影片講述當(dāng)代軍人生活居多,主人公生活的時(shí)代在1949年之后,不涉及真槍實(shí)炮的階級(jí)斗爭(zhēng)和反侵略英雄史。他們作為普通軍人或經(jīng)年累月地在路險(xiǎn)人罕之地運(yùn)輸物資(《高原如夢(mèng)》),或隱姓埋名消失在遼闊國土一隅進(jìn)行秘密研究(《橫空出世》),或在自然災(zāi)害橫虐的時(shí)刻挺身而出(《驚濤駭浪》)……最極致者也不過是在異國他鄉(xiāng)進(jìn)行非常人的軍事訓(xùn)練,并手握鋼槍和恐怖分子玩玩警察抓小偷般的游戲(《沖出亞馬遜》)。
與革命歷史題材電影所不一樣的地方是,這類電影中的主人公們頭上的至高而純粹的光環(huán)漸漸消失了。由于一般不涉及重要領(lǐng)袖人物,創(chuàng)作者們的自由度相對(duì)大一些。主人公除了是一個(gè)士兵以外,作為普通人的層面被大大加強(qiáng),我們看到他們真實(shí)而具體的生活:車技高超的模范兵卻是個(gè)婚姻失敗者(《高原如夢(mèng)》張仲良);政治進(jìn)步的抗洪戰(zhàn)士對(duì)企業(yè)管理也頗有心得(《驚濤駭浪》林為群);武功高強(qiáng)的特種兵內(nèi)心卻有一段辛酸往事(《沖出亞馬遜》王暉)。
由于主人公們生存境遇的特殊性,這些劇作在展開的時(shí)候往往采取在一定現(xiàn)實(shí)生活基礎(chǔ)上把人物懸置起來,這些人物與他同時(shí)代的人生活相比有一種苦行僧的味道。這種苦行僧的生活成為他們異于常人的資本,后來者面對(duì)他們的時(shí)候只能為他們的經(jīng)歷行注目禮,英雄的命名式因此而完成。《高原如夢(mèng)》中年輕且有個(gè)人見解的新兵于小北在跟隨老兵張仲良跑過一趟川藏線后被后者折服。張仲良明顯代表了一種道德風(fēng)范,這種風(fēng)范是被一種秩序形態(tài)所期許和標(biāo)注的,人物不由自主地投入其中,而且在這個(gè)巨大形態(tài)之下,所有的個(gè)人恩怨情仇都幾無所謂地臣服其中。那些具體生動(dòng)、真正痛徹心扉的情感在這個(gè)崇高中握手言和——實(shí)質(zhì)是對(duì)古典主義戲劇的繼承:個(gè)體為集體利益理所應(yīng)當(dāng)?shù)貭奚?/p>
這類劇作對(duì)人物的塑造往兩個(gè)完全不相同的方向同時(shí)前進(jìn):群像式的描摹(如《橫空出世》《驚濤駭浪》)和個(gè)別英雄的塑造(如《高原如夢(mèng)》《沖出亞馬遜》)。但不管是哪個(gè)方向他們所歌哭和標(biāo)注起來的英雄形象都是以男性為主角,而英雄們的妻子也好,情人也罷,只能遠(yuǎn)遠(yuǎn)地注視著他們投入國家基石的序列當(dāng)中。
四、經(jīng)濟(jì)中國的模范傳奇
應(yīng)該說主旋律電影中真正貼近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是這類電影:它們敘述了今日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見證那些發(fā)生在我們每日起居飲食中的點(diǎn)滴變化。相形之下這些電影才是真正在面對(duì)真實(shí)生活。萊辛在18世紀(jì)就告誡劇作者:把紀(jì)念偉大人物當(dāng)作戲劇的一項(xiàng)使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這是歷史的任務(wù),而不是戲劇的任務(wù)。他還說:王公和英雄的名字可以為戲劇帶來華麗和威嚴(yán),卻不能令人感動(dòng)。但是要在主旋律電影中描摹普通人的生活還是有它自己的一套法則,它的主人公雖非帝王將相但一定要有過人品質(zhì),在這類劇作中女性往往能夠成為敘事焦點(diǎn)所瞄準(zhǔn)的對(duì)象。這些女性不論來自遙遠(yuǎn)的歐羅巴(《瓦格納的愛情》芬妮——成片易名為《芬妮的微笑》)還是生長(zhǎng)在西北高原(《美麗的大腳》張美麗),無不體現(xiàn)出一種堅(jiān)貞不渝的品格。
這類電影劇作把主人公依附到某種文化的體系(當(dāng)然是中國文化的某一部分)中,除了讓人感到他們的性格力量外,同時(shí)還會(huì)被他們深厚的文化體系折服。而主人公們則時(shí)常處在她的婚姻陰影之下(寡居)。
平凡而文化程度不高的張美麗固執(zhí)地獻(xiàn)身西部教育的時(shí)候,付出的不只是自己的青春還有愛情。劇作者驚人地一直讓女性承受著愛情的缺失,以此來彰顯一種道德的勝利者姿態(tài)(張美麗最終在學(xué)生王勇敢的要求下放棄了自己與王樹的愛情)。個(gè)人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永遠(yuǎn)得是在為群體奉獻(xiàn)而且個(gè)人越不幸才越能成就一種偉大,并且這種事業(yè)會(huì)因之而發(fā)揚(yáng)光大而后繼有人(北京志愿者呂薇離婚來到張美麗所在的村莊)。這種舍己為人、一心為公的精神正是我們民族文化中提倡的,且在今天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比如所謂世風(fēng)不振,一切向錢看)有其被人期許的一面。將劇作人物依附在這樣的價(jià)值體系上自然是能夠引起人共鳴,使劇作向成功的方向推進(jìn)的。
應(yīng)該說劇作者究竟為他的人物選取了一個(gè)什么樣的文化價(jià)值,必將決定作品本身的品質(zhì)。在《瓦格納的愛情》里劇作者明顯是失敗了。來探訪芬妮的蘇珊是一個(gè)離婚的歐洲女性,當(dāng)她傾聽芬妮的愛情傳奇的時(shí)候呈現(xiàn)出一種對(duì)歷史老人的禮敬。這種禮敬是中國婚戀觀對(duì)西方的撲獲——?jiǎng)∽髡咴谶@里極其冒險(xiǎn)地把東方文明的力量夸大,無視一個(gè)20世紀(jì)90年代的歐洲知識(shí)女性已有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和民族文化力量,蘇珊像一個(gè)不滿三歲的小女孩一樣在東方愛情神話里完全陶醉。在蘇珊婚姻失敗和芬妮老人自足自得的比照中中華文明又一次獲得了永恒的勝利。劇作者為芬妮這個(gè)中心人物選定的文化坐標(biāo)是一個(gè)中國神話——牛郎織女的故事。在這個(gè)無邏輯的愛情神話里,沒有提供牛郎織女相親相愛的動(dòng)機(jī),卻把有邏輯推理習(xí)慣的西方人迷得一塌糊涂。芬妮陶醉在這個(gè)愛情神話中走向人生的暮年并因之成為豐碑。《瓦格納的愛情》將古老的牛郎織女故事折射成一種力量,并讓芬妮在現(xiàn)實(shí)中Cosplay一把。耐人尋味的是,在神話中的性別設(shè)置在現(xiàn)實(shí)中被倒置,芬妮扮演著牛郎的角色,為愛情踏向遠(yuǎn)離人間的不歸路。
五、結(jié) 語
主旋律電影越來越成為當(dāng)今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的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已有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有成功也有失敗。無論把電影作為產(chǎn)業(yè)還是把它作為一種教育國民的工具,有一點(diǎn)是很明確的:必須遵守藝術(shù)規(guī)律。在今天這個(gè)瞬息萬變的時(shí)代,我們會(huì)感到有一種歸屬的需要,一種身處某個(gè)社會(huì)“階層”的需要,盡管這種需要很難察覺。實(shí)際上這種需要也許是想象性地被賦予的。我們所有人都真實(shí)地需要一種社會(huì)存在,一種共同文化。大眾媒介在某種程度上就提供了這一需要,它能在我們的生活中(潛在地)實(shí)現(xiàn)一種肯定的功能。
主旋律電影創(chuàng)作在這一特殊階段之后迎來了中國電影產(chǎn)業(yè)環(huán)境的新變化,伴隨著民營資本的介入,中國電影的創(chuàng)作也結(jié)束了某種自言自語的沉迷,劇作不再無限度地讓步退縮,主旋律電影創(chuàng)作作為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的表達(dá)也找到了新的出路。
注釋:
① 在本文中“革命歷史”和“革命歷史史前史”的區(qū)別在于前者指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后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中國革命史,后者指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來到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之前的中國革命史。
② 本文所涉及的具體場(chǎng)號(hào)皆以夏衍電影文學(xué)獎(jiǎng)評(píng)選委員會(huì)辦公室編選的《夏衍電影文學(xué)獎(jiǎng)獲獎(jiǎng)劇本集(1~6)》所收電影文學(xué)劇本為準(zhǔ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