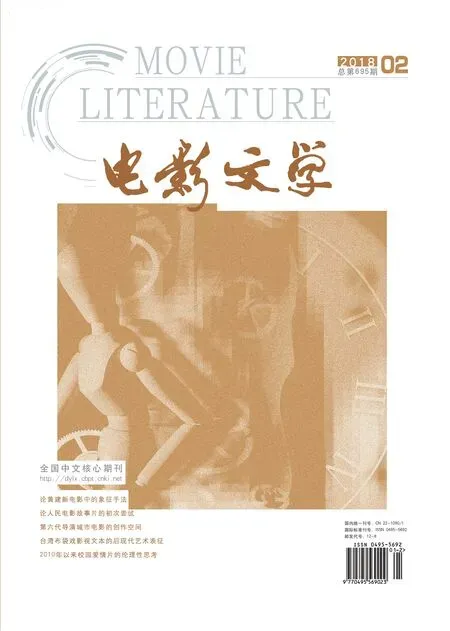希區柯克驚悚片中的懸念研究
王媛媛
(陜西職業技術學院,陜西 西安 710038)
一、驚悚片與希區柯克
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電影就已經出現類型電影,按照主題、風格等不同的元素劃分出了不同的類型電影,此時的類型電影更多地應用于電影發行和宣傳之中,指導觀眾觀影的意義大于其文藝研究意義。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后社會經濟動蕩轉型后,六七十年代的美國電影迎來了走向成熟的發展時期,此時對于類型電影的研究開始借鑒文學領域的研究方法,傾向于通過類型劃分對電影本身及其創制理念進行深度研究。隨著文藝理論的不斷發展,20世紀后期蓬勃發展的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結構主義等研究理論也被引入電影研究領域,再次掀起了關于類型電影的研究熱潮。本文所論及的驚悚片已擁有近百年的發展歷史,在美國影壇驚悚片曾是恐怖片的亞類型影片,直到20世紀中葉才逐漸發展成為獨立的類型影片,迅速點燃全球觀眾的觀看熱情。
對于驚悚片,我們很難用簡單的定義來規范其內涵和外延,不同于傳統類型電影,驚悚片產生并發展于美國電影內部裂變融合時期,單純的文字定義不僅難以全面概括驚悚片,還會抹殺驚悚片發展的可能性。所以,本文將在研究之前采用對比的方式對驚悚片進行定義。正如上文所述,驚悚片曾為恐怖片的亞類型影片,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恐怖片和驚悚片都擅長運用暴力敘事,通過對暴力事件和殘酷性情的呈現帶給觀眾以害怕、焦慮的觀影體驗,從而達到釋放壓力的觀影效果;與恐怖片不同的是,驚悚片雖然從未拋棄血腥畫面、畸形人性,但更加注重心理層面的言說和精神層面的價值,如果說恐怖片是一種劇烈的感官刺激,那么驚悚片更像是一種具有深遠影響力的理性恐懼。
眾所周知,電影是一種集合了多種表現方式的新興藝術形式,在聲、光、電、影的交相配合下能夠在更大程度調動觀眾的觀影積極性,其中也包括調動、激發、放大觀眾已經有的情感體驗,而驚悚片所調動的就是恐懼的情感體驗,充分調動觀眾的觀影積極性、喚起以往情感體驗的重要方式就是設置懸念。提到驚悚片中的懸念設置,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自然是首屈一指的導演。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出生于19世紀末的英國倫敦,擁有英國和美國雙重國籍,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獨立執導影片,憑借《訛詐》《三十九級臺階》等驚悚片確立了他在英國影壇的地位,同時初步形成了其獨立的風格。1939年,希區柯克來到美國好萊塢發展,真正踏上世界懸疑大師養成之路,憑借影片《蝴蝶夢》榮獲第13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獎;后又憑借《后窗》《西北偏北》等影片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銀海貝獎等重量級獎項;執導的影片《精神病患者》使全世界了解到了驚悚片不同于恐怖片和犯罪片的獨特魅力,為現當代電影中的精神分析開辟了先河,等等。在希區柯克從影的半個世紀中,20世紀20年代的《永遠告訴你的妻子》《房客》《水性楊花》;30年代的《謀殺者》《秘密間諜》《失蹤的女人》;40年代的《蝴蝶夢》《辣手摧花》《愛德華大夫》《美人計》;50年代的《后窗》《西北偏北》;60年代的《精神病患者》《艷賊》;70年代的《奇案》等五十余部作品基本都是驚悚片,甚至有評論者認為,驚悚片的獨立發展就開始于希區柯克。事實上,無論是驚悚片造就了希區柯克,還是希區柯克造就了驚悚片,我們都無法否認希區柯克在驚悚電影史上的至高地位,也無法忽略其在懸念設置及運用方面的開拓性探索。1979年,希區柯克榮獲奧斯卡獎終身成就獎;1980年被授予爵士封號,同年在美國洛杉磯逝世。本文將立足希區柯克的驚悚片創作,在簡要界定驚悚片特點的基礎上,從懸念構建和懸念價值兩個層面對希區柯克驚悚片的懸念進行研究。
二、希區柯克驚悚片中的懸念構建
作為一個重要的影視術語,懸念是指利用觀眾對故事情節走向和人物命運發展的好奇心理和審美期待,在劇情推進過程中設置懸而未決、疑而未解的矛盾沖突。成熟的懸念設置不僅能夠持續吸引觀眾的注意力、調動觀眾的觀影熱情,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影片的敘事節奏、布排影片的敘事結構,是一種極具表現力和可能性的藝術手段。總的來說,電影中的懸念要具備兩個基本要素,其一是主人公與敵對力量之間的沖突或主人公之間的矛盾,這些沖突和矛盾會隨著影片故事情節的發展而不斷激烈深化,從而保持懸念的基本吸引力;其二是影片要有設置開放性結局的可能,需要注意的是懸念可能在影片結尾處全面解除,也可能部分解除,但無論影片的結局是否唯一,懸念都需要在開放式的空間中才能彰顯其價值和魅力。
在“懸念大師”希區柯克的電影中,懸念的構建因不同的影片故事題材和敘事主題而變化,但總的來說具有一定的構建特點可尋。縱觀希區柯克的驚悚片,不難發現這些影片的故事內容較為簡約,無論是單線敘事,還是雙線并行,其驚悚片的框架都圍繞著主人公脫險這一核心內容推進。在影片《美人計》中,女主人公艾麗西亞加入了美國情報局,并與德福林產生了朦朧的情感。在父親曾為德國間諜的愧疚心的驅使下,艾麗西亞同意到巴西工作,接近曾經愛慕她的富商并竊取情報。然而就在二人走入婚姻后,富商卻開始對艾麗西亞產生懷疑,艾麗西亞的間諜生涯會迎來什么樣的結局,以及她與真心所愛的德福林的感情將會何去何從,成為影片的兩條故事主線中的最大懸念。此外,在《后窗》《西北偏北》等希區柯克經典的驚悚片中,故事情節也都比較簡約,相對簡約明了的故事情節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集中觀眾的注意力,避免因情節或人物的混淆而出現削弱懸念效果的問題。
提到希區柯克的懸念設置,不可繞過的就是“麥格芬”。“麥格芬”是希區柯克在驚悚片創作過程中的獨創詞匯,源自其經常講述的一個故事,開始出現于希區柯克的早期電影《三十九級臺階》中。簡而言之,“麥格芬”就是指一個無關故事主線,但在影片中處于核心位置的存在。在《三十九級臺階》中,驚悚故事圍繞著名為“三十九級臺階”這一間諜組織展開,但事實上觀眾對“三十九級臺階”組織知之甚少,希區柯克在影片中并未介紹這一組織的來龍去脈;在《美人計》中,酒窖之中的鈾礦瓶子也是典型的“麥格芬”,影片中的間諜故事主線和愛情故事主線均與鈾礦瓶子不存在直接聯系,但鈾礦瓶子卻成為影片敘事的重要核心。此外,《蝴蝶夢》中的瑞貝卡、《房客》中的復仇者、《后窗》中的謀殺案件也都是希區柯克驚悚片中頗具代表性的“麥格芬”。
在“麥格芬”之外,希區柯克在其驚悚片中的懸念構建還具有適度預示真相、巧妙設置偶然等特點。在《奪命狂兇》中,希區柯克就將犯罪事件的真相提前于結局展現出來,這一大膽的打破傳統懸念設置的方式取得了不俗的效果。雖然影片已經預示了真相,但在主人公命運起伏的呈現中設置懸念,使影片更加具有引人入勝的力量。在影片《西北偏北》中,主人公羅杰是一個安分守己、文質彬彬的廣告商,在紐約過著平靜的生活,在一次黑幫追捕卡普蘭的過程中,恰巧出現在同一地點的羅杰竟陰差陽錯地被認為是卡普蘭,從此他的人生被徹底改變。黑幫大哥對他窮追不舍,間諜組織將槍口指向羅杰,警察也開始通緝羅杰,因符合現實邏輯的偶然的發生,《西北偏北》的故事才得以推進,同時偶然本身也成為影片最核心的懸念。
三、希區柯克驚悚片中的懸念價值
在希區柯克的“懸念”敘事之前,驚悚片始終作為恐怖片的亞類型存在,從這一角度而言,希區柯克對于懸念構建的執著,從某種程度上促進了驚悚片的獨立發展。美國著名導演斯蒂芬·斯皮爾伯格曾高度評價希區柯克對美國電影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希區柯克是美國電影懸念運用、恐怖敘事的至關重要的開拓者”。不僅如此,希區柯克于20世紀60年代推出的影片《精神病患者》更是開啟了電影領域精神分析的先河。在《精神病患者》中,男主人公擁有嚴重的戀母情結,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說,男性的戀母情結即俄狄浦斯情結是普遍存在的,但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因親睹了母親和情人慘死的畫面而走向了戀母的極端。《精神病患者》將男主人公“精神病患”身份的緣由和經歷設置為懸念,在用懸疑之力吸引觀眾目光的同時,帶領觀眾走進男主人公畸形的精神世界,從而引發關于個體心理和個體精神的深沉思索。在《精神病患者》之外,影片《艷賊》中瑪爾妮無法戒掉的偷竊癖;《愛德華大夫》中愛德華的臆想癥;《后窗》中杰弗瑞的偷窺癖,等等。不同類型的“精神病患”及其身上的懸念構建不僅引導觀眾關注精神世界,也代表著個體陰暗心理的普遍性,或許在快速轉型、不斷發展的社會中,個體的內心深處均存在著一些陰暗角落,而希區柯克在這些影片中所凸顯的不僅是關于陰暗的認知價值,更重要的是陰暗的釋放價值。
在將精神分析引入驚悚片的同時,希區柯克驚悚片中懸念設置的價值還在于影片對人性之惡和復雜人性的呈現。在影片《西北偏北》中,卡普蘭先生始終是一個關鍵的存在,男主人公羅杰先生平靜的生活之所以被打破,成為黑幫、間諜組織以及警察等多股勢力圍追堵截的對象,其原因就在于羅杰被誤認為叱咤風云的卡普蘭先生。《西北偏北》中的懸念不僅在于羅杰作為一個普通人能否擺脫困境、怎樣擺脫困境;還在于卡普蘭先生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為什么會被多方追捕,但當懸念“破曉”時,卻超出了觀眾的審美期待,原來卡普蘭先生根本不存在,只是間諜機構虛構出來的人物,是為了引蛇出洞進而打敗敵對勢力,代表正義的間諜機構不惜將羅杰先生這樣的普通人推到危險的邊緣。此外,與羅杰互生情愫的女間諜也遭遇了羊入虎口的困境,其原因只是政府命令其完成間諜任務。隨著《西北偏北》故事的推進,當觀眾發現卡普蘭先生只是一個虛構的人物形象時,人性的幽暗與狡詐不言而喻。同時這部影片也通過這一巨大懸念的設置探討了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對所謂的“英勇就義”的必要性提出了質疑,這也是《西北偏北》懸念構建的現實價值所在。在希區柯克的驚悚片中,人性的復雜也借助懸念設置進行體現,比如影片《知道太多的人》中的女主人公放任另一惡性事件發生的原因是綁匪綁架了她的孩子,她盡管因自己的選擇而備感痛苦,但對自己孩子的保護欲望還是勝過了正義之心。再如影片《辣手摧花》中的警察本來是正義的化身,卻為了掩蓋女友殺人的事實并幫助她脫罪而制造了另外一起惡性案件,等等。無論是《知道太多的人》中的母親,還是《辣手摧花》中的警察,都面臨著情感與理智的斗爭,身陷道德困境無力自拔。
四、結 語
在希區柯克的驚悚片中,故事主線清晰,情節相對簡約,人物形象也并不豐富,其重點著墨之處幾乎都在懸念的構建之上。可以說,在希區柯克從影的數十年間,懸念始終伴其左右。盡管希區柯克的時代已然遠去,但希區柯克式的懸念卻成為驚悚片創作過程中的“常青樹”,包括《精神病患者》《西北偏北》在內的驚悚片已經成為后世導演效仿的經典范本,希區柯克的驚悚片創作及其懸念構建,無疑對后世許多電影導演的作品產生了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