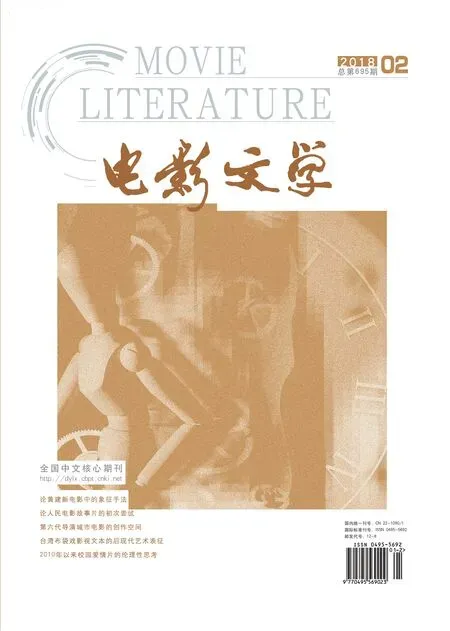《功夫熊貓》系列與大眾文化
李 巖
(渭南師范學院,陜西 渭南 714000)
由夢工廠精心打造的《功夫熊貓》系列電影包括馬克·奧斯本和約翰·斯蒂文森執導的《功夫熊貓》(2008),以及由呂寅榮執導的《功夫熊貓2》(2011)和《功夫熊貓3》(2016),由于這三部電影在票房上取得的佳績,該系列的第四部也已經在緊張地制作當中。在美國動畫長片中,由同一人物、同一世界觀主導的一個系列故事能夠拍攝到第四部電影是并不多見的。應該說,《功夫熊貓》系列成功地生產與傳播,是其主動擴大自己的受眾范圍,迎合大眾文化的結果。
一、大眾文化內涵與《功夫熊貓》系列
自19世紀以來,包括法蘭克福學派在內的諸多學者都從不同的角度對大眾文化進行了定義和研究。有學者認為,“大眾文化是在工業社會中產生,以都市大眾為其消費對象,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傳播的無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復制的、按照市場規律批量生產的文化產品”。從這一標準出發,我們不難發現,《功夫熊貓》系列,正是在大眾文化影響下創作出來的,它是一種具有商品性質的,處處體現著市場原則的精神產品。
作為一部必須獲取利潤的電影,票房是《功夫熊貓》系列創作的主導。奧斯本和斯蒂文森在拍攝《功夫熊貓》時,所考慮到的消費狀況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在世界范圍內掀起的“中國熱”和“體育熱”有關,因此在世人尤其是西方社會眼中最能代表中國形象的“功夫”和“熊貓”元素被恰到好處地結合,與美式動畫產品的創作慣例建立起了聯系。由于迪士尼等動畫巨頭之前在這一領域的空白,《功夫熊貓》推出之后很快給予了觀眾驚喜。在票房佳績的刺激下,《功夫熊貓2》的創作很快正式納入夢工廠創作日程。《功夫熊貓2》和《功夫熊貓3》的拍攝面臨的已經是另外一種外部環境,但消費社會這一大背景并沒有發生改變。此時北京奧運會已經落幕,但是“功夫熊貓”本身已經被創建為一個品牌,擁有可觀的潛在消費者。觀眾對于這一品牌的認知包括具有中國水墨風格的清麗畫面、精致震撼的視覺特效以及一個以胖胖的熊貓阿寶為主人公的武俠故事。而呂寅榮等主創也極力滿足著觀眾的審美期待。
電影的模式化和易復制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三部《功夫熊貓》都是中國文化包裹下的美式平民英雄電影。每一部劇情的主線都是阿寶與一個破壞力極大的反派(太郎、沈王爺、天煞)的戰斗,而具體的戰斗過程都不是一帆風順的,阿寶總是先受挫,然后再憑借如烏龜大師等人的幫助以及自己的靈光一閃擊敗對方,使得劇情既跌宕起伏又符合觀眾對“大團圓”結局的青睞。大眾在阿寶的成功中能夠暫時忘卻現實生活帶來的失意或不滿。該系列每一部電影都灌注著一種具有強大滲透力的、能博取大眾認同的“邪不勝正”和“傻人有傻福”的思想觀念。同時,在阿寶的身邊,還有如悍嬌虎、鵝爸爸等親友配角起著或解讀劇情、或插科打諢的工具式作用。可以說,只要這一模式能夠繼續使社會大眾獲取感性愉悅,保持對大眾文化品位的適應,那么制片方就可以無限制地復制下去。
二、《功夫熊貓》系列的大眾文化特性
(一)世俗性
與大眾文化相對的是精英文化,后者的賞析需要一定的素養與財力,因此難以具備廣泛性和普適性。而大眾文化則不然,它有著強烈的世俗性傾向,在趣味和利益的立足點上緊緊跟隨著大眾,而并不試圖對事物的深層意義進行思考。《功夫熊貓》系列在對人物情感進行表達時,是符合普通觀眾的內心世界的。如阿寶作為一只有著滾圓身材的熊貓,對于吃有著難以割舍的執念,這使得他連攀登高聳入云的殿堂前的石階都極為困難,更不用說吃苦練武。而他的養父鵝爸爸平先生作為一個單身父親則顯得有點婆婆媽媽,他并不完全理解阿寶在做大俠方面的追求,他表達自己對兒子的愛的方式就是不停地說“我喂你”,總是拼命地用食物來滿足阿寶,唯恐阿寶受餓而不顧阿寶早已肥胖臃腫。除此之外,電影中的一系列日常生活細節,也與世俗有著高度契合之處。如在《功夫熊貓2》中隨處可見的取材于成都的錦里、寬窄巷子的街道,以及街道兩邊寫著“擔擔面”的招牌,阿寶和狼的追逐戲中出現的雞公車等,還有鵝爸爸苦心經營面條店,用阿寶這個“神龍大俠”來作為店鋪的廣告招徠生意等。即使是非中國文化背景的觀眾,也能敏銳地感受到上述元素中的煙火氣息。
(二)娛樂性
在以世俗性來拉近電影與觀眾之間距離的同時,電影又必須創建一個狂歡的語境,來取悅大眾,幫助大眾實現身體的舒緩和精神的宣泄。這就要求電影必須有一個充滿趣味的世界觀體系,以及基于觀眾審美的視覺奇觀。在《功夫熊貓》系列中,動物們所生活的世界有其一套既與人類社會類似又獨特的運營模式。從整體上說,這是一個類東方世界,由動物組成,而神奇五俠、浣熊師父、太郎等人的社會屬性、職業和性格等又帶有風靡華人文化圈的武俠世界的意味。在視覺上,動畫的優勢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人物的動作、形體等得到了充分的夸張與變形,如沒有四肢的小青蛇憑借身體的伸縮成為武術高手,甚至可以打破物理意義上的時空束縛,如《功夫熊貓3》中神奇的“氣”等。除此之外,各類中國風元素也是電影令人交口稱贊之處。如《功夫熊貓2》中講述巫卜故事時美艷而神秘的皮影戲過場、行云流水般的中式武打動作設計等。
(三)商業性
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后現代理論家讓·鮑德里亞在其《消費社會》中所指出的:“消費是一種積極的關系方式,是一種系統的行為和總體反應的方式。我們的整個文化體系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而作為商業電影的《功夫熊貓》系列也處于這種積極的關系之中,是消費者接受的精神消費的一種。在鮑德里亞看來,在消費社會中,消費者不再以一種被動的姿態來接受、購買產品,產品對于人們來說不再只是滿足個體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消費者有了充分的選擇的余地,也能夠更加自如地表達自己的消費喜好。生產者必須關注消費者消費意愿的風向標,以市場需求來決定自己的生產。在《功夫熊貓》中,看似平庸而能夠后來居上的阿寶,滿足的是觀眾對于平民英雄的審美需求。在《功夫熊貓2》中,觀眾已經不滿足于阿寶僅僅是擊敗如太郎這樣的赳赳武夫,因此阿寶依然顯得顢頇肥胖、好吃懶做,而他的對手則變成了妖嬈修長、五彩斑斕且身份高貴的沈王爺。第一部中的寓意“以柔克剛”也被上升到更為豐富的“功夫勝于槍炮”“和諧勝于暴政”“寬厚善良勝于陰鷙狹隘”“青山綠水勝于工業污染”等方面上,以適應不同觀眾的心理需求和價值觀。另外,第二部中已經明顯地通過鵝爸爸的回憶埋下阿寶身世的伏筆,這便是電影主動刺激觀眾對第三部電影的消費欲望,引導觀眾消費選擇的體現。
三、《功夫熊貓》系列的大眾文化反思
我們必須認識到,大眾文化是一把雙刃劍,電影在通過迎合大眾文化獲取商業利益的同時,又有可能因為基于商業規律的創作而付出在創造力和審美價值上的代價,并且這種代價有可能隨著生產的推進而日益增長,最終導致生產者商業利益的受損。在《功夫熊貓》系列的三部電影已經取得了傲人的票房成績之后,第四部有可能出現創作上的窘境。對于絕大多數的系列電影而言,在面對這一狀況時,電影主創往往由于人物關系已經基本得到了開發,加入新的人物,構建新的人際關系,并由此開發新的矛盾沖突。如《冰川時代》《海底總動員》等莫不如是。而部分真人與動畫結合的電影,如《變形金剛》系列等,也在后期出現了嚴重的創作疲態。在《功夫熊貓3》中,一個全是由圓滾滾熊貓組成的熊貓村以及阿寶真實的熊貓父親的出現,給予了觀眾新的刺激,但是在阿寶身世這一點上很難再有繼續展開的可能。盡管當前《功夫熊貓》系列并未宣告落幕,甚至還有繼續拍攝第五部、第六部的可能,但是我們并不能無視其在與大眾文化結合時,值得反思和警惕的一面。
從觀眾的角度而言,正如德國社會哲學家馬克斯·霍克海默所指出的那樣,大眾文化在某種程度上由于對商業的妥協而成為“反文化”。霍克海默認為,大眾文化商品的大量產出,使得消費者面對的是缺乏營養和內涵的文化快餐,最終造成的是消費者,也就是觀眾人格上的片面性。在《功夫熊貓》系列中,主創在配角上的塑造是遠遠不如對熊貓阿寶那樣用心的,以至于相對于迪士尼動畫而言,《功夫熊貓》的配角有平面化之嫌,難以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只有在阿寶的身上,人物有著較為深刻的心路歷程:第一部中,阿寶身上體現的是“對自我的重塑”;第二部中,電影通過阿寶意識到自己不是鵝爸爸的親生兒子而進行了“重新認知自我”的表述;第三部中,阿寶則是通過正視自己的熊貓身份而“做真實的自我”。可以說,除了阿寶以外,沒有任何一個人物被賦予了如此深的內涵。這也就使得觀眾在每次觀影中都習慣性地將自我的感情投射在阿寶的身上。而對于電影,觀眾往往只能產生單維度的解讀,以及對阿寶不斷取得勝利、不斷增強實力等略顯世俗化和平庸化的期待。
而從制片方的角度來說,觀眾在熟知電影的創作模式以及復制性后,自然便會陷入一種審美疲勞,失去繼續消費的欲望,直接有損片方的經濟效益。在三部《功夫熊貓》中,最令觀眾為之感動的主要有三點:熊貓形象本身的招人喜愛,阿寶和鵝爸爸之間跨越了種族的真摯親情,以及阿寶作為一個武林中的小人物的成長。但是這三點又幾乎被挖掘到了極致。熊貓村的加入意味著阿寶作為獨一無二的熊貓的特殊性在整個世界觀中不復存在,尤其是在阿寶學會了像其他熊貓一樣翻滾前進等特有技能后;阿寶和鵝爸爸之間的親情在被高度張揚的同時,也因為阿寶的另外兩個父親(生身之父李山以及授業恩師浣熊師父)的加入而被淡化;而阿寶的成長則是一次又一次地圍繞著神龍大俠這個身份展開,在阿寶最終在村民和爸爸的幫助下得道,雄姿英發地顯出神龍真身后,劇情也似乎很難有再進一步拔高的可能。如果電影再繼續復制下去,那么制片方一來難以再創作出與阿寶匹配,同時又符合整體世界觀的反派人物,二來也將使電影陷入無限“打怪升級”的循環。而由于觀眾早已建立起了阿寶將最終獲勝的審美期待,那么劇情對于觀眾來說無疑將失去吸引力。
夢工廠僅僅誕生了二十余年,就可以在動畫長片這一領域與有近百年歷史的迪士尼相抗衡,在其崛起過程中,《功夫熊貓》系列與《馬達加斯加》系列、《怪物史萊克》系列可以說是功勛卓著的三大系列電影。在充分考慮到消費時代最廣大觀眾審美趣味的前提下,《功夫熊貓》從創作到發行的每一階段都盡可能地融入大眾文化的潮流之中,呈現出世俗性、娛樂性、商業性的特征,在展示出藝術品質的同時,也征服了中美等國的觀眾,取得了令人歆羨的經濟效益。而我們也需要承認的是,在大眾文化主導之下的藝術生產,作品的藝術價值實現有可能為商品生產過程所取代,長此以往,系列電影創作的內在活力便有可能消失。這既是《功夫熊貓》有可能遭遇的,也是我們應審慎反思和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