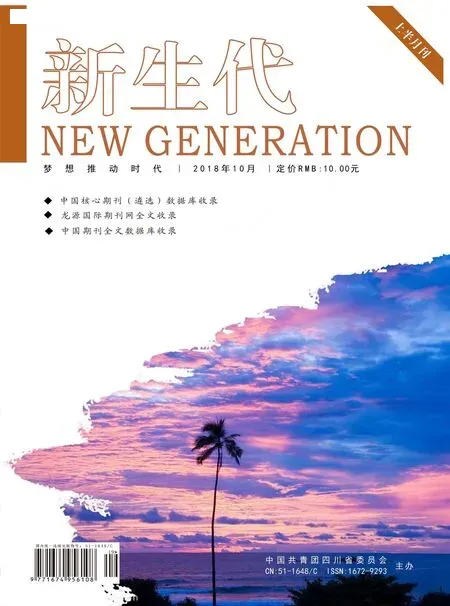淺論中立幫助行為
馬超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所謂中立幫助行為,是指一種外表無害的、“中立”的、客觀上卻對正犯起到了幫助作用的行為。在德國、日本地區,這類行為被稱為“外部中立的行為”、“日常生活行為”、“職業典型行為”或“中性業務行為”等。例如,商店的老板向正與人爭執的顧客出售菜刀;P2P技術服務的網絡平臺服務商預料到會員會利用此服務侵犯他人著作權仍然提供此服務;的士司機明知乘客在后座吸毒仍然搭載直至其吸毒完畢等。與傳統幫助犯不同,中立的幫助行為具有反復持續性、日常性、可替代性,且大多是民事行為等特征,如果將它們一概作為幫助犯加以處罰,難免造成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公民行動的萎縮,甚至導致整個社會交往的癱瘓,人人陷入岌岌可危的狀態。因此,一方面要實現法益保護的目的,另一方面又要維護社會的發展,在法益保護和自由保障之間如何妥當地劃定中立的幫助行為的可罰性范圍,一直是理論和實務中富有爭議的課題,也是本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理論研究回顧
德、日刑法理論界最近幾十年來就中立幫助行為問題展開了深入持久的討論,理論上存在全面處罰說與限制處罰說兩種觀點。全面處罰說認為,只要符合傳統幫助犯的成立條件,即具有因果關系與故意,就應以幫助犯進行處罰。這種觀點由于根本不考慮中立幫助行為的特殊性,因而不當限制了公民的自由,如今在德、日等國少有支持者。限制處罰說認為,應嚴格限制中立幫助行為的處罰邊界,原則上不成立幫助犯,以保護現代社會交往中公民的業務自由、日常活動自由等利益,如今已成為德、日學界共識。根據學者梳理,限制處罰說內部又主要有如下學說:
(一)主觀說
在判斷中立行為是否制造了不被法所容許的危險時,德國學者Roxin認為應區分兩種情形:一是幫助者確實地認識到正犯的犯罪計劃的場合,即直接故意(確定的故意)的場合;二是幫助者只是認識到自己的幫助行為有為他人犯罪所利用的可能性的場合,即間接故意(未必的故意)的場合。前者原則上成立幫助犯。后者原則上適用信賴原則,除非他人實施犯罪的傾向十分明顯。德國學者克勒(Kêhler)也持主觀說觀點,他指出,對于幫助犯的成立而言,僅有未必的故意是不充分的。行為人必須具有通過其正犯的意圖,即預見到正犯行為不可避免,并致力于此。主觀說遭到了不少質疑,根本原因在于,中立幫助行為的特殊性本體現在客觀行為本身上,故應在違法性階段解決中立幫助行為的處罰邊界問題,而不應從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入手。如果直接摒棄對客觀行為的考察,而直接對行為人惡的意圖進行探討,顯然有主觀歸罪之嫌。
(二)客觀說
1、禁止溯及論。德國學者Jakobs認為,雖然行為客觀上促進了正犯行為,但如果該行為的意義并非取決于正犯行為,而是本身具有獨立的社會意義,則禁止將正犯行為及其結果回溯到之前的促進行為,只能由正犯獨自承擔責任。據此,明知對方購買螺絲刀的目的是用于人室盜竊仍向其出售的,不成立幫助犯;面包店老板知道顧客購買面包的目的是用其投毒仍向其出售的,不構成殺人的共犯。可以看出該觀點與Roxin觀點的差異在于,行為的社會意義不應受行為人的主觀認識所左右。
2、假定的代替原因。德國學者Frisch根據客觀歸責原理,在判斷是否存在危險增加問題上考慮假定的代替原因,看正犯是否很容易從第三人處得到同樣的幫助。例如,在出租車司機知悉他人犯罪計劃還將犯罪人運至犯罪現場的情形,犯罪人如果不乘坐出租車,乘坐公交車也能到達犯罪現場,因此不應當處罰司機的搭載行為。日本學者島田聰一郎也持類似的觀點,其認為如果介人假定的代替原因,發生同樣的結果仍具有高度的蓋然性,則應否定危險增加,從而否定幫助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這種觀點受到的批評是,刑法中的因果關系本來就是現實的行為與現實發生的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假定的并不存在的“虛擬”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取代現實的因果關系的判斷值得商榷。
3、利益衡量說。德國學者Hefendehl提出,應從利益衡量的角度限制中立幫助行為的處罰范圍,即權衡受德國基本法所保障的潛在幫助者的行為自由與被害人的利益。當行為本身還不存在威脅法益的明顯傾向時,即本身無害的前提行為被他人的犯罪行為恣意利用時,屬于正犯的故意行為導致的自我答責的領域,其前提行為應屬于受基本法所保障的一般行為自由的范疇。不過,若與共犯存在共謀關系,或者援助者對于應受保護的法益存在特別的注意義務,以及存在需要保護的特別重要的法益時,為了保護法益,對自由的剝奪才是合理的。
4、社會(職業)相當性說。德國學者韋爾策爾(Welzel)以社會相當性理論為出發點,認為即使某一行為導致了法益侵害結果的發生,但只要他完全處于正常的、歷史形成的社會生活范圍之內,就不具有構成要件符合性,因為他們是被社會所接受的相互作用行為。在社會相當性說的基礎上,德國學者哈塞默(Hassemer)對中立幫助行為問題中的運用進行了系統研究,結合中立幫助行為所涉及的各個職業領域,對社會相當性的判斷標準進行了具體化和精確化的加工,形成了職業相當性說。
(三)國內理論研究概述
張明楷指出,應當通過綜合考慮正犯行為的緊迫性,行為人(幫助者)對法益的保護義務,行為對法益侵害所起的作用大小,以及行為人對正犯行為的確實性的認識等要素,得出妥當結論。如果只是大體估計對方將來可能實施犯罪行為的,對于日常生活行為不宜認定為幫助犯。反之,向正在斗毆的人出售利刃的,則成立幫助犯。
周光權指出,日常生活行為是否成立幫助犯,要從客觀上看行為是否具有明顯的法益侵害性,主觀上看行為人是否對他人可能實行犯罪有明確認識,從共犯的處罰根據看,行為對正犯行為的影響是否達到了足以被評價為幫助的程度。
黎宏的觀點接近于假定的代替原因說,他認為應站在事后的立場上,將有該中立幫助行為與沒有該中立幫助行為的情形進行對比,看該行為是否導致了構成要件結果的重大變更,是否增加了正犯侵害法益的危險或者強度。若有這種變更,就能肯定二者之間具有因果關系而成立幫助犯,否則只能宣告無罪。
孫萬懷、鄭夢凌認為,在對中立的幫助行為的可罰范圍進行界定時,原則上不應考慮主觀方面,而應當從客觀方面入手,通過對幫助行為與正犯行為之間的物理、心理因果關系的限定,以限制中立幫助行為的處罰范圍。
陳洪兵先是提出客觀歸責論,在他看來,要否定中立幫助行為的可罰性,只能從否定幫助犯的客觀構成要件即違法性人手,因此,只要中立幫助行為本身沒有制造不被允許的侵犯法益的危險,就不應當處罰。近年來,他又進一步提出基于利益衡量的客觀說,認為只要不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行業規范的要求,行為人就不負有法益保護義務與危險源監督義務,此時應當尊重和保護公民的交易交往自由。因此,即便是店前吵架而使得法益侵害的危險出現緊迫的場合,五金店老板也不負有法益保護義務與危險源監督義務,不應要求其必須拒絕出售菜刀,因為使用其出售的菜刀殺人,完全屬于他人“自我答責”的領域。
張偉認為,應當堅持以犯罪構成理論為指導,以幫助犯的處罰根據為基礎,分析行為的主客觀方面以及行為的危害性即法益侵害性,進而厘定中立幫助行為成立幫助犯的范圍。首先,從客觀上講,要考慮中立的幫助行為的對法益侵害的增加是否有實質作用,幫助行為是否是合乎行業法則的業務行為,幫助行為的稀缺程度(可替代性)以及幫助行為的時空性。其次,從主觀來看,必須具有明確的主觀認識。
姚萬勤從客觀歸責理論出發,總體上來說,主要是基于危險升高即用發生結果的概率來確定某結果是不是可以歸屬某具體行為,只有行為人的中立幫助行為不僅“制造了不被允許的危險”,且“實現了不被允許的危險”時,才能對其科以罪責。
二、本文觀點:堅持客觀歸責和主客觀相統一
按照傳統的幫助犯的構成要件理論,明知正犯的犯罪意圖還提供中立的幫助行為的,則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的故意,客觀上有幫助的行為,當幫助行為與正犯行為、結果之間的物理因果關系不容否定時,便符合了幫助犯的構成要件。但是,如前所述,考慮到對國民生活行為自由和社會交往秩序的保護,必須對正常的業務活動和日常生活交往加以保護,而不能一概將符合傳統幫助犯構成要件的行為作為幫助犯進行處罰。純粹的主觀說存在主觀歸罪之嫌,筆者從結果無價值出發,更贊同客觀說的觀點,同時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立場。應當承認,沒有一種理論觀點是完全合理、無懈可擊的,每一種理論都有其不足。但是,理論的目的是為了指導實踐,由于其他理論存在抽象性、難以把握的問題,從可操作性的角度,筆者提出如下觀點:首先,立足于客觀歸責論,從違法性層面排除不具有可罰性的中立幫助行為,不具有侵害法益危險性的中立行為,不具有幫助行為性,因此應當排除處罰;其次,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在通過違法性篩選的中立幫助行為中,只處罰那些有明確認識的幫助行為,從而進一步限制處罰的范圍。
客觀歸責理論的判斷包含三個基本原則:制造不被允許的危險、實現不被允許的危險與構成要件的效力范圍。而這三個基本原則的適用,主要通過兩個判斷步驟完成:第一,行為人的行為制造了不被允許的危險,且符合構成要件的結果實現;第二,由不被允許的危險實現的結果須在構成要件的效力范圍內。進行具體操作時,還應考慮是否存在優越的利益需要保護,是否存在注意義務違反等。
第一,中立幫助行為是否制造了不被允許的危險。由于直接從正面探討存在困難,因此不妨從反面入手“劃定范圍”。
首先,未制造危險的中立幫助行為應當被“過濾”掉。如何判斷行為未制造危險,需要結合禁止溯及論,即對于那些行為本身就具有獨立的社會意義,因其行為本身并未制造對法益的侵害,只能由正犯獨自承擔責任。比如,提供食宿等類型化的民事行為,即使是為犯罪分子提供食宿,由于提供食宿本身并未對法益產生實質危害,因此不應當被歸責。再如向犯罪分子歸還欠款,導致其得以潛逃,還款行為本身是為了履行民事契約,因此也不應當處罰。但是,如果制造了實質的危險,就應當認為其具有違法性,這時主要考慮幫助行為是否具有時空緊迫性和難以替代性。比如,五金店老板目睹馬路上兩人正在斗毆,仍然向其中一人出售刀具,應當對此出售行為進行處罰。而藥店老板明知購買者意欲毒害他人仍然向其出售毒藥則不能處罰,一來出售毒藥具有高度可替代性,此家不賣,彼家也可購得;二來不具有時空緊迫性,出售毒藥并未直接現實地對法益造成緊迫危險;三來增加了交易成本,如果藥店出售毒藥均要購買者出具用于正當用途的保證,而這顯然無法做到。
其次,降低危險的中立幫助行為也應當排除。所謂降低,是指該行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險,但是與他人意欲實施的危害結果相比,又明顯降低了危害結果的損害程度,那么就不能對該種行為進行客觀歸責。反之,如果幫助者所賦予的危險升高了危險,就不能排除責任。比如網絡服務商具有監管的義務而未能履行該義務導致危險結果發生的,典型例子如“快播案”, 從客觀歸責理論視角出發,網絡服務商不能以技術中立作為抗辯事由,故不應免除其刑事責任。再如出租車吸毒案,乘客一天之內不間斷地打同一輛車進行吸毒,雖然司機是在履行正常的職業行為,而且該行為的替代性很高——如果被拒載,吸毒者可以選其他出租車。但是,因為本案中出租車司機在提供運營服務時,已經相當于變相地為他人吸毒提供了一定的場所,故應當認為升高了危險。需要強調的是,雖然容留他人吸毒是正犯行為,但其本質上只是吸毒的一種幫助行為,只是為了打擊毒品犯罪的需要,刑事立法才將該類幫助行為予以正犯化。
最后,行為人制造了允許的危險的情形。所謂“允許的危險”,是從實質上判斷社會和法律是否能夠容忍。一般來說,對于那些合乎法律和行業規范的行為,我們認為所造成的危險是可以容忍的。比如,司機明知乘客是脫逃的竊賊仍然將乘客運往目的地,由于司機從事的是合乎法律的職業行為,本身并不具有制止義務(否則社會將變成人人都是警察的社會),而且幫助行為的可替代性很高,竊賊不搭乘本車,也可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到達,所以司機的幫助行為不應當被處罰。再比如商店向賭場出售撲克牌、麻將等賭博用品,雖然客觀上對經營賭場起到了幫助,但出售是正常的經營行為,對法益沒有造成實質侵害,也不應當予以苛責。
第二,結果是否由不被允許的危險所引起。如果行為人對結果的發生賦予了一定的危險,但是并非該危險造成了某種結果的發生,而只是由于該行為與該結果存在某種偶然性的關聯,那么就不能對其進行歸責。比如,甲出租房屋給乙,后得知乙在房屋中開展電信詐騙活動而未阻止,是否應當處罰甲?換言之,自甲知悉情況起,其是否有阻止義務?我認為,此時需要運用利益衡量說來詳細判斷,只要不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行業規范的要求,行為人就不負有法益保護義務與危險源監督義務,此時應當尊重和保護公民的交易交往自由。房東雖然知曉房客利用出租屋開展電信詐騙,但對法益的侵害并不是由出租行為所引起。房屋租恁是正常的民事活動,不能因此苛責甲具有防止乙借助房屋犯罪的義務,否則將極大地增加交易的成本,因為交易雙方為了知曉對方交易用途,而不得不想方設法增加了解。不過,由于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容留賣淫罪與容留吸毒罪,故而僅在法律明文規定時,房東方有危險源的管理義務。
在完成客觀歸責的“過濾”后,對于那些仍然符合違法性要件的中立幫助行為,還需要從主觀方面予以考慮是否應該處罰,從而避免處罰不當擴大。從認識要素角度講,只能限定為明確的認識,即中立的幫助者清楚地知道他人即將或正在實施犯罪行為,其行為將客觀上有利于正犯者實行行為的完成或犯罪計劃的實現。從意志要素上看,則至少需持放任心態,即間接故意。這是因為,在清楚地知道他人的犯罪計劃且知道自己的幫助行為會有力地促進犯罪的完成后,仍對犯罪的發生持積極的追求態度或消極的放任態度的,已經明顯違背了日常生活的目的:“不論是日常生活行為抑或業務行為,其目的最起碼都是正當的,即有益于社會共同體的,最起碼是無礙于共同體成員生活安寧的,而認識到行為的有害性仍然幫助已經背離了共同生活的目的。”但是,對于沒有明確認識的情形,就不能予以苛責。因為綜合考量各種細節情況,推測行為人是否行將實施犯罪或者系罪犯,這是公安、檢察機關的任務,而非普通公民的義務。
三、結語
如果不限制中立的幫助行為的處罰范圍,顯然會導致社會交易的停滯以及個人自由行為的萎縮,甚至導致社會經濟秩序出現混亂。如何限定處罰范圍、明確處罰邊界,是學界一大理論課題。客觀說相較于主觀說,從違法性層面出發討論中立幫助行為的可罰性問題,更具有科學性。目前來看,客觀說內部還分為不同觀點,但均存在過于抽象與操作性差的問題。本文認為,應當先通過客觀歸責理論在違法性層面上排除不值得處罰的中立幫助行為,即通過“行為制造了危險”、“結果由危險所引起”兩個階段判斷,只有行為人不僅 "制造了不被允許的危險”,且 "實現了不被允許的危險”,才能對其科以罪責,從而使大多數案件由于排除客觀歸責而不構成犯罪。接下來,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只能對那些對法益侵害有明確認識且主觀上至少為間接故意的幫助行為予以苛責,從而防止社會變成“人人都是警察”的社會,在法益保護與個人自由之間尋求較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