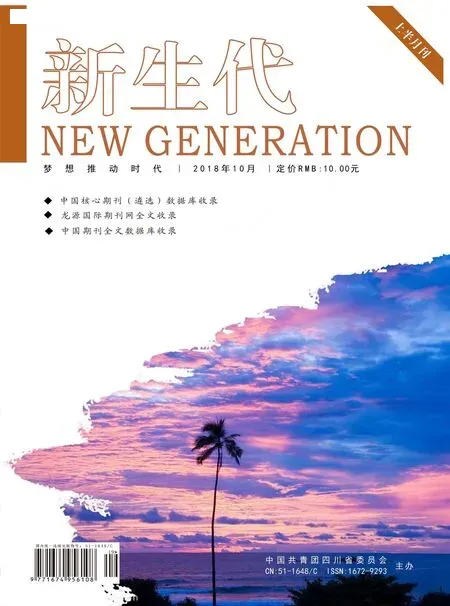關于藏族天葬習俗中天葬師角色歧視的成因探索
李靜 四川大學 四川成都 610065
一、概述
藏族的喪葬習俗種類多樣,而天葬是在藏民之中普遍實行的一種葬俗。這種獨特喪葬形式的起源、演化以及社會功能早已引起世界范圍的廣泛關注而成為藏文化研究者們長期探索的課題。目前,學術界有關天葬的研究成果已相當豐富,但對于天葬儀式中“碎尸”這一必不可少環節的執行者——天葬師的研究卻非常有限。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天葬師在西藏社會的身份:比如《天葬漫談》的作者丹珠昂奔認為天葬師在藏族是受人尊敬,不被歧視的,但這并不相符于天葬師的真實生存境遇;劉志楊在《鄉土西藏文化傳統的選擇與重構》一書中,具體介紹并分析了一位名叫米瑪的天葬師的生存狀態,較為客觀地反映出了天葬師受歧視的狀況;閆振中在《西藏秘境》一書中花了較大篇幅對天葬作了比較全面的探討。在談及天葬師時,作者指出,按宗教教理來講,天葬師的地位不屬下賤,但一般人仍認為他們地位低微。總體說來,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天葬師在西藏社會是遭受了歧視的。
對于天葬師遭受社會歧視的生存狀態,學界雖已有詳細描述,但卻并未出現過追蹤式的深入研究和報告來解釋這種狀態產生的原因。筆者結合自己兩次徒步藏區之所見所聞以及相關文獻資料的閱讀,以基于天葬起源探討的階級對立說為主要敘述對象,整理出了現有的或可作為參考原因的假設,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二、基于天葬起源探討的階級對立說
對于天葬起源的探討,霍巍先生將各家之說歸為三點:1、印度來源說。2、本土起源說。3、“原始天葬”發展為“人為天葬”說。在此基礎上,湯惠生先生又將其簡歸為兩種:印度來源說和本土來源說。盡管目前對于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取得比較一致的看法,但如果撇開母體文化與現代意識所帶來的先入為主的影響,我們會發現天葬一樣是早期民族文化演化的結果,是藏民族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相結合的產物。葉遠飄[]認為,在此演化過程中,“碎尸”執行者這一角色也相應發生了變化。
喪葬最核心的文化內涵是死亡觀,而死亡觀的建立是以宗教的靈魂信仰為基礎的。在現今廣布整個藏區的藏傳佛教看來,肉體于生命而言是短暫的,而靈魂卻是永恒的。人死之后,遺體若能迅速消失,將有利于靈魂的轉世。相對于其他葬式,天葬對遺體的處理更快而且干凈,因而是最有益于靈魂轉世的葬式。但事實上,佛教產生之初并不認為人有靈魂,那么藏傳佛教今天所承認的“靈魂轉世”實際上是無法從原有的佛教教義中找到源頭的。唯一的解釋便是佛教在向西藏傳播的過程中,為了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所以有選擇地吸收了本土宗教(也就是苯教)的一些教義觀。在佛教傳入西藏之前,苯教就已經有了“靈魂外寄”的觀念。“靈魂外寄”是指通過一系列法術讓某人的靈魂暫離自己的身體。佛教在青藏高原弘揚的后期,很有可能吸收了苯教的“靈魂外寄”觀念,為自己的“輪回說”找到對應的主體。再說到苯教的葬式,文獻記載:“雅隆……大王止貢贊普之時,請來達瑟、阿豺的本波,他們用兩塊黑石同肢解了的肉塊和成一團,將死人皮從灰白色的魂之所依( 指尸體) 上裁割下來。”雅隆是后來整合成吐蕃政權的三個重要部落之一,可見剖尸葬在苯教時代的藏地上層社會是非常流行的,而現今天葬的儀軌也吸收了苯教的碎尸手法。
搞清楚了這兩點,現在我們回過頭來再看,在天葬儀式中出現的天葬師,他們在苯教中是否能找到對應的存在呢?在苯教中,最早從事剖尸工作的人即是上文文獻中提到的本波。[]苯教的產生本就與王權密切相關,到第八代贊普“絕地天通”事件發生以后,苯教開始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正式進入為王權統治服務的時代。從文獻我們可以看出,執行剖尸葬的本波,實質上就是為藏族的貴族統治階級服務的,上文所提到的“大王”、“贊普”就是極好的佐證。《隋書·附國傳》中曾有記載:“死家殺牛,親屬以豬酒相遣,共飲啖而瘞之。死后一年而大葬,其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在等級極其森嚴的奴隸社會,苯教所倡導的喪葬儀式是相當奢華的。然而在藏地自然條件本就惡劣的條件下,平民階層溫飽尚成問題,又如何能做到死后動則殺馬數十匹,享受剖尸葬呢?因此他們在死亡以后,尸身多被扔之于江河山野之中,而這有可能就是水葬、野葬的源頭。
自佛教傳入西藏,佛苯之爭便未止息,直到最終佛教得勝。此時吐蕃社會的生產力也有了一定發展,人們越來越重視“人”的價值。苯教的喪葬儀式在花銷上不但不能為普通百姓所承受,并且還伴有大量人殉與動物祭祀的現象,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社會需要迫切地改革喪葬風俗來適應大多數人的需要。據《大唐西域記》記載,佛教倡導的葬式有三種:“一曰火葬,極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飄散;三曰野葬,棄林飼獸。”其三正好與貧民死后所進行的野葬不謀而合。為了最大限度爭取民心,完成在地化,佛教很容易選擇投民所好大力推行野葬。不過如前文所述,佛教在這個過程中吸收了包括“剖尸”在內的許多苯教的儀軌。“剖尸”這一儀式,在當時的社會看來,仍然是只有統治階層才能享受到的,無疑是“高貴”的象征。佛教以“剖尸”為民眾找回丟失的“靈魂”、以肉體“布施”拯救自然界的一切生物以求靈魂轉世的教義是通過對苯教儀軌的大量吸收創新演化而來的。而這一做法使得原本低賤的野葬最終變得“高貴”而“神圣”,使各種形式的天葬開始在藏地大放異彩。在天葬的普及過程中,那些原本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剖尸者(本波)逐漸變成為平民服務的天葬師。也就是說,天葬師與平民原本就站在對立的階級立場上,就算他們不再為高高在上的人效力,也難以真正融入到平民的階層中去,這或許正是根源上社會對他們抱有歧視的一大原因。
三、其他角度
對于天葬師遭受社會歧視的根源,無疑以上假設只能作為一家之言。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別的角度也值得我們思考。
例如:舊西藏拉薩驅鬼活動中的“背鬼人”所遭受的社會歧視和排斥相比天葬師更甚。這二者所事之事皆關乎生死鬼神,且都是由藏族社會中出身低下的貧苦之人才會選擇去做,其間是否有什么相關或相似的因素?
又如:在藏族的潔凈觀念中,天葬師、鐵匠、屠夫等都被歸為污穢階層,“他們從事的是不潔的職業”。此外宗教的神圣原則和內外有別原則也指示出越是接近宗教便越是潔凈,越是遠離宗教就越是污穢。[]從這一角度而言,天葬師作為協助死者靈魂順利轉世儀式關鍵環節的執行者,顯然是與與宗教緊密相連,不至于被說成“污穢”,甚而應該被視為“神圣”的。從“碎尸”的外在形式看,天葬師工作的前提顯然也異于屠夫,他們面臨的是已亡之人,而非屠夫刀下的鮮活生命。但不管怎么說,天葬師既在其位,便要持刀、剖尸、碎尸,長久地與因各種原因所導致的死亡之身打交道,其間不免有意外和因病而亡的人;筆者在藏區也曾聽藏民說起過,如果做惡太多,死后連禿鷲都不愿意吃你的肉,那樣你的靈魂是無法完成飛升進行轉世的。這樣一來,是否說明藏民們是否有著普遍共同的意識,認為一部分非正常死亡以及生前品性不好的人,他們的尸身上承載著在世時的疾病、不詳、不幸以及邪念等污穢之物?而天葬師在工作的過程中是離這些污穢最近的,這是否會使藏民認為他們因此也難免沾染而對其避而遠之?
四、結語
無論如何,縱觀現今國內外藏學人類學民族志研究狀況,尚未出現對天葬師的民族志研究。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藏族社會傳統觀念對天葬師規避,導致學者們都不愿觸碰雷區,引起不必要的麻煩而去接觸天葬師并對其做深入的調查與研究;并且,研究“人”,是需要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去做田野調查的,天葬師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使得穩定的田野調查進行起來相當困難,若其它民族和國外學者有語言上的障礙,這一調研就會難上加難。但文化說到底是關于“人”的文化,對“人”的研究應該是人文學科的中級使命,所以筆者認為有必要深入研究天葬師在藏族文化中身份定位的矛盾,關注其特殊的生命體驗,同時也更完整地理解天葬這一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