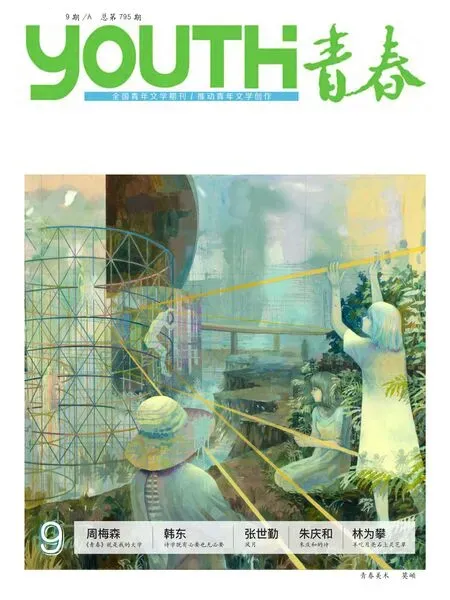詩學既有必要也無必要
詩學既有必要也無必要。必要在于,它是一種儀式,和宗教活動中的情況類似,其儀式是為吸引注意力而設的。詩學將人們的目光吸引過來,使之朝向詩歌的方向。
作為詩歌活動的儀式部分,詩學被要求有一定的規模、程式,權威而莊重,是可以加入并且可以為之之事。它暗示了某種更高價值的存在,自身并非這一價值。由于詩學的龐大或精微,背后的東西一定更加顯赫,值得詩學這么去做。從一種外觀去猜度詩歌內在的神奇,在詩學是必然的,也是它的任務。
詩學是對詩歌的渲染。如果拋開詩學,讓我們直接面對詩歌,很可能發生視而不見的情況。赤裸的詩歌或詩歌的核心秘密,看上去實在平淡無奇,貌不驚人,極易被忽略,或被認定為無足輕重。詩歌的核心秘密是灰色的,說灰溜溜也不為過,而詩學卻光芒萬丈。詩學強調了詩歌的重要性,雖然只是從外觀而非體驗的角度。
詩歌不僅是詩歌,它還是一種世俗文化,是文化事業。從作為文化的詩歌著眼,詩學就顯得尤其必要,在詩歌文化中所占的比例甚高。詩歌文化中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成分是由詩學和詩學的衍生物以及延伸物構成的。如果詩學不局限于書本、專著、觀念和理論,它就包括了有關的討論、活動、組織和運作。詩學正是單純的詩歌(詩歌藝術)和社會生活的連接部分。詩歌的世俗化是在詩學范圍內展開的(這一點是和通常的看法相左)。
詩歌也可以單純化,作為獨立的文本。既獨立于詩歌文化也獨立于所涉及的詩歌,讓自身成為審美對象,詩歌只是作為題材運用。如此,討論二流詩歌可成就一流詩學,或者批評一流詩歌仍可獲得某種圓滿。正確或者合理與否在這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詩學文本在文學價值上是否成立。以寫詩的方式寫作詩學顯然不夠(如所謂的“詩話”),還必須達到和詩歌同樣的品質要求。
詩學亦可以理解為思考、觀念,不一定非要形成文本不可。它可以是關于詩歌的“思”的部分。這一部分對寫作而言極為重要,并不能直接導致作品的面貌,但是一個集中注意力的過程。關于寫詩的所思所想一般都不算數,都會被否定,再否定,但只有通過這一緊張、辯證的過程,你才真正來到了詩歌寫作的前沿。思考的結論無關緊要,思考本身卻意義重大。此外,關于詩歌的思考和寫作的理性是同質的,甚至是同流向的。理性的寫作也是一種“思”,只是不是以邏輯、概念為主導的體系之“思”。
無論詩學再正襟危坐,它都起源于一種人性本能,亦即閑聊、議論的本能。我們不僅寫詩、讀詩,還需要談詩。從此意義上說,詩學就是談論或議論詩歌,是關于詩歌的談論。作為談論的本能無法禁止,自古有之,詩歌以外的一些領域、專業亦然(例如競技體育)。有關的談論可塑造為專業,一種談論專業的專業;詩學準確地說就是關于詩歌的專業談論,是由自發地談論詩歌塑形而來的。
所謂的專業化或者專門化首先是儀式化,因為,儀式對詩歌公眾而言意義更大。對專家來說,詩學是一個職業飯碗問題,但之于公眾卻是一項嚴肅的娛樂,其自我是可以在此安家和生活的。專家們的物質生活取決于詩歌人群的精神生活。這也不錯,滿足了很多人對詩歌提供精神食糧的愿望。就像在宗教生活中絕大部分的信眾只到宗教的儀式、儀軌為止,對詩歌的追索大部分人也只到詩學為止。
下面談詩學的沒有必要。
對把握詩歌的核心秘密而言,詩學一無所用。在讀與寫之間橫亙著作品,詩歌意義的實現只有通過寫作作品和閱讀作品。無論是寫作還是閱讀只有一種可能的方式,就是直觀,其間插入詩學,不僅多此一舉,也構成了障礙本身。
所謂的直觀,就是直接面對。不限于詩歌,實際上對任何藝術的把握都必須通過直觀。藝術其實就是付諸于直觀的創造,就是直觀藝術,除此之外并無其他的藝術。藝術是為直觀而設、而存在的。即使是觀念藝術也不是為了推理,得出結論,也必須付諸于直觀、引發某種身心共鳴才能得以成立。
直觀并非直覺,不是事前的預感,而是最終捕獲的東西。直接面對,全神貫注,假以時日,在你和對象之間沒有任何路徑,也無法借助任何工具。之后便會產生位移現象,在某一時刻或者瞬間,你就和對象合二為一了。的確神奇,也很神秘。對詩歌真正的理解或把握本質上就是一種類似于宗教體驗的覺悟。
直接面對之際,在你和對象之間會出現大片的空白,難以理喻的空虛茫然,我們出于本能,或者某種尋找捷徑的算計,會求助于方便之物。詩學作為路標和指南,作為一種引導于是便應運而生。直接面對不僅消耗心力,也令人極度不安,甚至陷于深深的絕望、痛苦,此時一切緩解手段(只要可供緩解之用)都會乘虛而入。問題在于,一旦你借助了某種手段,目標就會變成這一手段,號稱具有引導功能的手段已經將你帶往另一條道路,迷失在所難免。給了你一種可以抵達甚至已經抵達的幻覺,實際上早就離題萬里。詩歌的核心秘密原則上無路可抵,也無跡可尋。
詩學對于真正想了解詩歌奧秘的人而言,不僅不起作用,還相當危險(如果你深陷其間)。它向你伸出援手,一旦拉住這只手你就萬劫不復了。習慣性依賴是其一,還給了你一種所獲甚多的錯覺。相對于一無所獲,獲取的感覺總是讓人寬慰,以假亂真是其后的邏輯必然。
從這一角度說,無論寫作詩歌還是閱讀詩歌都是一種冒險。沒有既定道路,沒有依憑,并且得面對蠻荒空間(距離造成的空白)的壓力,只是為了一次名副其實的結合。這并非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承受的。這里所謂的抵達、捕獲、結合是同樣的意思,就是對詩歌核心秘密的把握。
就像在宗教活動中有普及部分和核心奧秘部分一樣,詩歌活動中的詩學,無論如何高深體面都屬于詩歌的普及部分。詩歌的奧秘(或秘密)部分只有通過個人的直接面對才可能把握,它脫離了理論、觀念的描繪范圍。普及部分是眾人之事,集體行為,秘密部分則屬于個體的孤獨之旅,可以交流但無法彼此替代。實際上,對詩歌的秘密部分加以描繪純屬多余。但既然我們要思考詩學,劃定有關的界限就是必要的。只有在核心秘密之外,詩學才是可行之事,才可能具有某些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