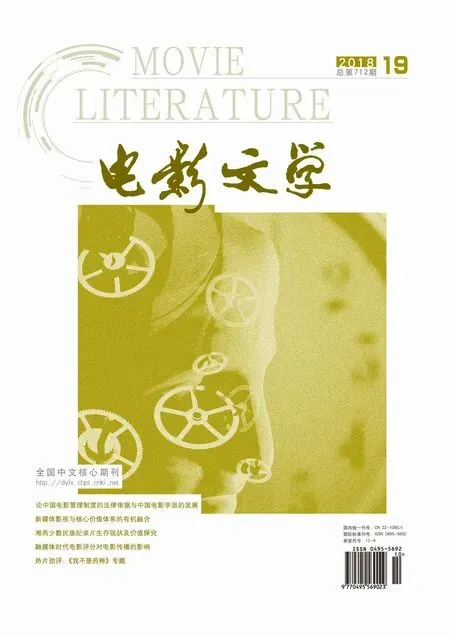在矛盾和不確定中探尋欲望與命運的本源
——論《春去春又來》的模糊美
楊建生
(常州工學院 教育與人文學院,江蘇 常州 213022)
韓國著名導演金基德執導的《春去春又來》給觀眾留下了太多的思考空間,令人回味無窮。當我們企圖去清晰地梳理影片的思路和特征,并從理論上做出某些總結和表述時,我們發現這個過程是極為艱難的。每次我們試圖做這種努力時,總會有一種“詞不達意”“言不由衷”和“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感受,本人就曾經感覺到“影片思路上的某些紊亂與模糊”。也曾閱讀過一些關于金基德電影評論和研究的文字,它們對于影片中的每一個細節和意象的解讀,可謂眾說紛紜,各執一詞,觀點甚為豐富。對這些觀點做整體性綜合思考時,我突然發現,正是由于金基德電影具有一種“模糊美”的特征,才留下了如此多的“空白點”來讓我們反復把玩、思考、填充,也許這正是金基德電影藝術上的一個美學特征吧。
以柏拉圖、黑格爾和尼采為代表的傳統觀點把語言的模糊性看作是語言的缺陷,希望限制它,消除它,對事物往往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斷。接受美學的產生極大地顛覆了這種觀點。藝術作品的“召喚結構”“啟示結構”“未定點”“意義空白”等概念的提出,極大地迎合了讀者的心理需求,影響深遠。一部優秀的藝術作品在創作中,雖然無意于去迎奉這種理論,卻總是暗合這種理論,這是一種必然,也是藝術創作的規律,因為模糊美是藝術存在的必然,只不過在有的藝術品中體現得比較明顯,有的體現得比較隱晦。我們在分析《春去春又來》的美學特質時就發現,這是一部“模糊美”特征體現得尤其強烈的影片,模糊性為作品增添了更為豐富、多樣化的審美想象空間,具有極高的藝術欣賞價值。
什么是“模糊美”?王明居在他的《模糊美學》中闡明了模糊美的內涵,它具有相對性、互滲性、包孕性和亦此亦彼性等。胡和平在《模糊詩學》中也論述了其基本理論范疇,包括象征、隱喻、反諷、悖論、空白、未定性等。在《春去春又來》中,作品的語言、意象、情節、結構等都帶有諸多的不確定性,具有極強的概念外延性,由生活現象到藝術世界,在能指和所指之間,充滿著空白與不定,留下了巨大的彈性空間,既增強了藝術的表現力,又能夠最大地調動讀者再創造的想象力,具有獨特的審美潛能。這些美學因素可以極大地喚起審美主體審美意識中的聯想、體驗和感悟。這些不確定性為接受者提供一種理解的張力,使不同的讀者可以通過不同的創造性思維來賦予作品不同的理解,這種模糊性既調動了審美主體,也擴大了審美客體,從而擴大了藝術審美空間。
在影片當中,庵門能自動開合;水中孤寺可以漂移;小船可以在老僧的意念控制下往來于水間;老僧隨手扔出去的一粒石子能輕易砸中水中的易拉罐,而持槍的警察卻屢擊不中;靈蛇也違背冬眠的習性,成了衣缽的守護者。這些細節都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突出了一種非真實性,干擾了我們對于慣常的真實性尋求,作為影片,這種虛構無可厚非,“電影藝術,作為人類的一種審美活動,必須要以創造的主體性去超越現實的客觀性”,任何藝術創造的本質也都在于對現實的超越與重構,與神話一樣,電影對人類世界的描述方式也是超現實的。所以我們不必用現實的邏輯來衡量這些細節是否合理,這些只是一種理念的傳達——甚至傳達的理念也具有不確定性,呈現出一種模糊美。不可否認,這些細節有一種把我們引向禪意的“企圖”,時時刻刻向我們傳達禪的“意念”,但是,這種意念是很難用明確的語言來表述和傳達的,或許,這正是細節模糊美的魅力所在。也正是由于這些細節的神秘,讀者從其中也同樣能感覺一種“不確定”,即人生的不確定,生命的不確定。在人的一輩子中,有很多東西是超出我們預期之外的,是難以控制和把握的,它的存在不能用偶然或者必然來界定,在生命當中隱隱約約地存在,這種存在就是生命的模糊美。有人把這種不確定稱為人生的虛無和虛幻,實際上,從美學的角度來講,這就是生命的模糊美,人生就是一種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統一體,二者相互包孕和滲透。
故事沒有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影片中的人物也沒有來歷,沒有姓名,沒有關系介紹,身份信息等都不詳。實際上,他們是一種“普適性”人物,也就是說,在他們身上并沒有作為個人存在所展現出的獨一無二的特征,只是作為一種“類型化的人物”或者符號而存在,這也是出于一種藝術傳達的需要,好處之一就在于這類人物易于辨認,接受者可以輕而易舉地認知、識記和理解。這一點在“冬”的片段中體現得尤其明顯。如,雪夜托孤的女人在系圍巾時,向我們展現的只是她的背影,中年和尚把女人從冰湖里撈出來,解開圍巾的一剎那,導演也轉換了鏡頭,刻意隱藏了女人的面孔,始終沒有交代女人的身份。她到底是誰?為什么要蒙面?她與中年和尚曾經有過什么瓜葛嗎?所有這些問題,導演刻意回避著,觀眾越是不知道就越想去探求,觀眾越是想去弄明白吧,導演卻偏偏不讓你弄明白,就這樣讓你欲罷不能,被一再強化的是那種不必知和不可知的模糊性。導演似乎也并不著意從“典型人物”身上來體現“典型性格”,而是把重心放在探索這些人物符號存在的價值上,要去探尋人物身上所體現的生命本源意義。在這些不確定的人物本身向我們展示一種神秘和模糊時,導演所傳達的理念更具有豐富性、多層次性、神秘性。這就跟傳統繪畫和雕塑藝術特別喜歡選擇人的裸體形象來描繪和刻畫是一個道理。一方面,人體本身毫無疑問是地球上最美的,是自然美的最高級形態,也是最高雅的感性藝術品;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裸體人的身份、職業都是不確定的,這就更具有最廣泛的包孕性、代表性,可以指代需要指代的任何人群或個體,其概括性、寓意性就更豐富,闡釋空間也就更大,藝術傳達的效力則更強,該藝術產品的文化消費價值自然就更高了。在《春去春又來》中,不但人物關系、來歷模糊,人物的活動范圍同樣是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統一體。一扇庵門把人物的活動范圍劃分成兩個世界,即佛界和俗界。中年和尚走出寺廟后,隨欲望的驅使去追尋他俗世中喜歡的女人,后又犯下了殺妻之罪,這中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復雜過程,夫妻日常生活的瑣碎與情感生活的紛紜詭譎,影片并沒有做詳細的交代,只是在師父面前發泄憤怒和抱怨時透露出一鱗半爪,這就給讀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
作者在影片中著力探求人性的本源,和尚在往返于佛界與俗界之間,最終是回歸了佛界,整部影片充滿了禪意。但是,影片中“彌足珍貴”的對白和一些細節卻又超出了“禪”之外。小僧雖然生活在佛門之中,但是并沒有得到佛理的熏陶,身在佛門,佛在心外,并沒有領悟佛法真諦,在游玩當中對小動物實施虐待,長大之后又犯了殺妻之罪,青年殺妻不過是童年虐待動物的一種延續。開始,小僧還處于欲望的最底層,出于簡單的童趣而虐待動物,當年歲漸長,欲望開始膨脹,最終淹沒了人本身。老和尚的教導并沒有使小和尚由“惡”導向“善”。小僧在夏日的湖水里面進行了多次佛性與欲望的較量,但最終拋開了佛門禁忌投入到情愛的河水中。當年輕和尚和治病少女在上船時產生身體接觸的那一剎那,他內心的欲望已經開始潛滋暗長,就像湖水的漣漪一樣,開始不斷向外蕩漾開去,膨脹起來,最終把心中的佛性滌蕩得一干二凈。對于這種戀情,老和尚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說:“只有愛情才是治療你這種病的最好良藥。”佛門作為清修之地和“禁欲”之地的大眾化觀點基本上就被老和尚的這句話給徹底消解了。年輕和尚和少女之間由戀情進一步發展到“交媾”,寺廟的威嚴形象也被徹底顛覆了。而且,這種交媾是一種“拼命”式的,二人缺少必要的、充分的情感醞釀、交流,有的只是內心欲望的釋放和外泄。片中人物的舉動和故事發生的地點改變了人們的慣性思維,干擾了欣賞者對于故事的常態的真實性尋求,眼前的寺廟由“禁欲之地”變成了“世俗之地”,這是一種“陌生化”的故事敘述技術,能夠造成一種所謂的“間離效果”, 正因為其模糊性,反而令人產生強烈的破譯沖動,從而大大拓展了作品藝術欣賞的時空緯度,使作品獲得更大的審美效應,進而把欣賞者的思維導向一個更高的境地——去思索人性的本源問題。
換個角度,在形而上的層面上講,正如寺廟里有門沒有墻一樣,廟本身是作為一個象征性的符號而存在,導演所要側重傳達的并非描寫發生在寺廟里的事情,寺廟作為“禪意”和“出世”的符號,是與世俗相對立而存在的。整部影片雖然充滿了濃濃的“禪意”,但是,導演的終極目的不是向我們宣傳佛教,介紹佛教,而是把佛教作為一個載體來探討人的命運歸宿問題。影片中的寺廟只是作為物質性的存在,作為渲染“禪意”的工具而存在,實際上并沒有作為承載佛教精神的場所而存在。因為生活在寺廟里的生活和世俗的生活并沒有兩樣,同樣是充滿了俗欲。影片告訴我們一個真諦,佛只有真正進入心中,人才能得以超脫,外因必須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佛理和與世隔絕的環境并不能抑制人的欲望的膨脹。日本神學大師鈴木大拙說:“禪存在于個人的一切經驗之中。沒有個人的經驗的背景,思想便難以傳達。”禪尚未被年輕的小和尚所經驗,師父的教誨就阻止不了小和尚的欲望,他最終還是歸入了塵世,只有經過個人內在的經驗、洗禮,重返佛門時,中年和尚才不再是以“我”觀佛與世,而是以“佛”觀世與我。夕陽中,僧人以石磨為基座,將佛像置于山頂,冰封的湖面不過山地石臼大小的一汪,這是超越欲望之上來看欲望,顯示了對欲望的徹底超脫。
老和尚的死也很值得深思。他選擇了“自焚”,而且是五官“緊閉”。老和尚是看透塵世而覺無所留戀了?還是對人的本能欲望無法抑制感到無奈,而對內心“佛”的轟然倒坍所做出的消極回應?抑或是他已經預見到了中年和尚有回來的那一天,自己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他的死顯得撲朔迷離,朦朧模糊,難以確定。可以肯定的是,老和尚選擇閉五官而死,傳達了他對“欲望”的反對與否定這一信號,但是,他為什么又肯定情愛的合理性?在這些肯定與否定之間,影片所傳達的理念的矛盾性和模糊性顯得特別豐富。正是由于這些不定性的模糊區域,才為接受者制造了障礙,提供了再創造的藝術空間。這些不定性會在接受者與作品的雙向交流作用下,有效生成別有意味的審美世界。康德也說過:“模糊觀念比清晰觀念更富有表現力。……美應當是不可言傳的東西。”因為好奇心和求知欲是人的天性,對于模糊美的不斷追求和探索既能滿足人的天性需求,又能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內涵,在藝術審美的主客體雙方相互吸引、相互作用中,藝術魅力便應運而生。恩格斯也說:“辯證法不知道什么絕對分明的和固定不變的界限,不知道什么無條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學的差異互相過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適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在影片中,諸多充滿隱喻和象征的意象都沒有陷于簡單抽象的“非此即彼”,而是具有一種不確定性,都是明晰與模糊的統一,靜態與動態的統一,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統一。
和尚的一生經歷了童年殺生—少年色戒—中年作孽—老年超脫四個階段。在充滿“禪意”的寺廟,小和尚的欲望并沒有因為這些意念的熏陶而得以抑制,反而得到了更為強烈的爆發,佛界的教化靜心功能遇到塵世的“欲望”時,顯得無能為力,不堪一擊,很快敗下陣來。小和尚生理與情感的浪潮沖垮了佛門的堤壩,離開清修的廟宇而踏入塵網。但是,中年和尚在犯下殺妻之罪以及后來刑滿釋放后,都選擇了回歸寺廟,如果說前一次的回歸是一種逃避,那么后一次回歸則是真正的“出世”。中年和尚在面對塵世而無以解脫時,選擇了尋求佛教,得到了生命的升華和超脫。這一次,在和塵世的較量中,佛教占據了上風,徹底征服了塵世。金基德在影片中一如既往地在思考人在滿足和追求欲望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巨大危險。在探索如何擺脫欲望的道路上,影片仍然顯得矛盾和迷惘,雖然最后仿佛也給出了答案,即皈依佛教,但是這種答案顯得極為軟弱和牽強。實際上,這并不僅僅是導演內心所呈現出的矛盾,也正是擺在整個人類面前的矛盾,即人類如何擺脫自身的欲望?或許,人類在不斷探索,但永遠沒有答案。金基德的矛盾也是整個人類的矛盾,沒有確定,充滿了模糊和不確定性。實際上,金基德所涉及的命題,人的欲望以及命運等命題,都具有一種本源的意義,不可能得出確定和明晰的答案,導演用模糊性的表達方式能更深刻地探討人性本源的命題,接受者也能在更為廣闊的空間中理解此類命題。
中年和尚回到寺廟以后,為了洗臉而鑿了一個冰窟窿,托孤的女人在深夜離開寺廟時,神情慌張,掉進了這個冰窟窿。如果說青年和尚犯下的殺妻之罪是故意為之,那么這次的“殺人之罪”則是一種無過,正是這種無過體現了人生的無常、虛無和不確定,有時候,“為”或者“不為”得到的結果是一樣的,中年和尚在命運之神的詛咒下飽受內心的煎熬,陷入了宿命的怪圈。縱觀整部影片,導演在不同的季節安排不同的人飾演和尚,但在結尾中卻用同一個孩子飾演童僧,前面的不同暗示了人人都有成為僧人的可能,最后的相同卻讓人明確感受到了輪回的宿命,老僧是否也經歷了人生的春夏秋冬?影片的環狀結構昭示了命運的輪回,人只是命運的一個棋子,開放式的結尾給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實際上,金基德的影像世界也是個符號化的世界,這些視覺符號充滿了復雜而豐富的意義,具有強烈的象征性和抽象性,充滿了哲思和隱喻,顯得凝練而意味深長。他運用了更為廣義的影視語言,畫面構圖、特定場景的設置、道具、色彩、光效、音樂等,更加充滿了隱喻性和延展性,突出了一種模糊美。有成就的藝術家總是善于以模糊手法創造出具有更廣泛包容性的藝術形象,唯其模糊才更有魅力。綜觀《春去春又來》全片,金基德用西方的思維提出了一個命題——原罪,又用東方的思維做出了回答——皈依佛教,實現了中西雜糅,亦此亦彼,相互滲透,真可謂此處模糊勝清晰。
欲望和命運本源問題的探尋是藝術創造中的一個永恒主題,《春去春又來》整部影片充滿了大大小小矛盾和不確定的關于人類生命的隱喻和象征,其模糊性、未定性和無限性能始終吸引觀眾去做無盡思考和解讀,顯示了特有的藝術張力。“生命美學”代表人物潘知常先生說過:“在我看來,審美活動就是以‘超越性’和‘境界性’來滿足人類的‘未特定性’和‘無限性’的特定需要的一種生命活動。”是的,金基德的《春去春又來》正是這樣一部帶領我們享受文化消費盛宴和探索生命之美旅行的經典影片,余味不盡,百讀不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