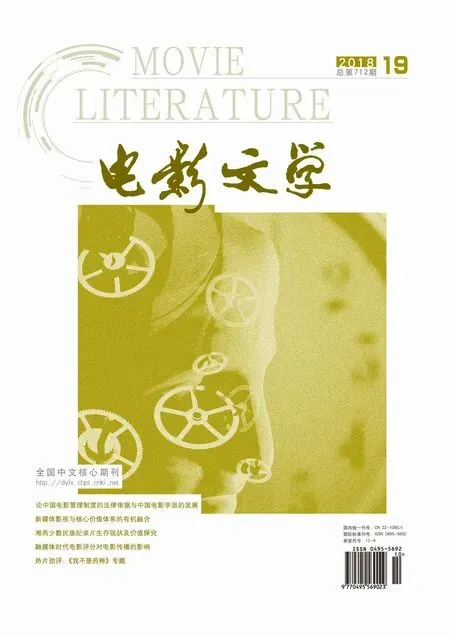婁燁作品中人物的悲劇性解讀
劉 迅 丁 琳
(成都理工大學 傳播科學與藝術學院,四川 成都 610059)
婁燁,中國第六代導演。他的個人影像在國內市場步履維艱,卻堅持“電影是我表達個人的唯一出口”。在他從影的二十多年中,不踏入主流的洪荒,向大眾傳遞的是與主流相抗衡,再現真實生活的情感訴求。每部影片都注入了他對邊緣人物的關注與思考;從不單純講愛情,而是在愛情的框架下衍生出多種非主流的性別關系與人性的多面;對于邊緣化人物的塑造是他故事的核心與欲望的展開點,站在關懷者的視角去訴說著他們的故事。婁燁站在攝影機后、大銀幕前與觀眾對話,幾乎處在一種記錄人物日常瑣碎生活的視角中完成返璞歸真的創作。
一、人物塑造個體的悲劇性呈現
(一)欲望驅使與欲望落空
欲望是潛藏在人物心里不可窺視的存在,而人又是在欲望的驅動下產生行為,成為推動自我發展的永動機。人在產生欲望時個體是快樂的,人們會將欲望變成一種想象的投射。而在欲望落空時人會不自覺產生求而不得的失落感或是無可奈何的無助感。
婁燁在《頤和園》中運用強烈的對比手法對余虹欲望落空產生的悲劇性完成了最理想的塑造。余虹與周偉在頤和園泛舟的場景,婁燁認為這是最美好的愛情,故將影片名定為《頤和園》。導演同樣用大量鏡頭描摹余虹與周偉的理想愛情范本,在觀眾心中埋下了對二人愛情的期待。當二人十幾年后再次重逢,觀眾的期待值被放到最大化,但是導演卻用極為詩意的鏡頭宣判了愛情結束,與觀眾期待形成落差。這種欲望的落空直接造成了觀眾期待毀滅,悲劇性由此而達到頂峰。在《推拿》中,婁燁將視角放在了邊緣人群盲人的身上。在塑造沙復明這一角色時,導演用一種明快而輕松的影調來完成對他的風格化定位。沙復明心中并不羨慕健全人,他可以做任何健全人能做的事情,但是當沙復明每每聽到客人對都紅“美”的贊嘆時,他撫摸著都紅的臉近似癡迷地想知道“美”究竟是什么。這里沙復明對于都紅“美”的執念是他心底對于光明的渴望,很多事物看不到便成了永遠也解不開的謎,他的絕望感給觀眾帶來了強烈沖擊并感同身受。婁燁在影片塑造中將人物欲望潛移默化地傳遞給觀眾,當觀眾在某一契合點上對人物產生期待并達到峰值時,便會急轉直下,不按照常規處理方式滿足觀眾,而是將欲望落空。雖然產生了欲望落空的悲劇,但是卻真實展現了現實中的人物情感、人物關系或是人物處境。雖揭露了生活狼藉的一面,卻讓我們觸碰到了最原始現實的模樣。
(二)自我尋找與自我迷失
拉康認為,“自我是在與另外一個完整對象認同的過程中構成,而這個對象是一個想象的投射,人通過發現世界中某一可以認同的客體,來支撐一個虛構統一的自我感”。黑格爾在他的悲劇理論中闡述,將悲劇的產生歸結為“沖突說”,沖突有三類,其中一類是“由心靈的差異面產生的分裂”。如果在自我尋找的過程中,有外力打破或無法繼續時,人物便會開始否定自己所認同的客體,對自己產生質疑,陷入一團迷霧之中,不能前進也無法后退。這種境地消磨了人對自己的認同,極易生發悲劇。
《蘇州河》中的美美便是一個從自我尋找過程中走向迷失的角色,她是一條沒有自我意識的水族館“美人魚”,長期處于被觀賞被窺視的位置。其后牡丹成為她認同的客體形象,美美也認同了童話愛情的存在。但最終結局徹底打破了她對純粹愛情的向往,使她陷入迷失,心里那份虛構統一的自我感被擊垮,她所認同的自我遭到了毀滅。婁燁在《頤和園》中對李緹的悲劇性塑造既是強烈的又是潛移默化的。從李緹的人物動機來看,她一直覬覦余虹的男友周偉,但導演婁燁卻用清醒的方式擊碎了李緹心里自我認同的幻想,她無論怎樣竭力去配合周偉,他們之間的情人關系依舊無法維系,內心虛構統一的自我感不堪一擊,導演用更加殘酷的死亡來揭示李緹迷失自我的悲劇性后果。當某一獨立個體為了某種虛幻想象選擇走進迷失的泥潭中,就要有勇氣承擔后果。
(三)人物孤獨感
孤獨感是個人內心所產生的一種主觀悲劇效應,是在某個時間或空間中,心靈得不到倚靠和陪伴,將自己封閉在自我空間之中。叔本華將這一類悲劇定義為“某一劇中人本身就是悲劇的肇事者”。他們處在自己的世界里獨自感受孤獨、痛苦和無奈,折磨著原本就脆弱的內心和軀體,沒有人理解這種不適與痛苦,在掙扎中即使有人伸出援手,但也無法填補心里那一塊空白,從而喪失了愛與被愛的能力。
余虹在婁燁的鏡頭下成了悲劇色彩的代名詞,而悲劇的肇事者就是余虹的內心。余虹不愿再袒露內心去愛別人,想要他人主動接近主動了解,但試圖了解她的人對她內心的打開方式是錯誤的。她將自己禁錮在孤獨的囚籠之中,別人進不去自己也出不來。熱烈而真誠的余虹失去了愛與被愛的能力,與先前對愛情狂熱追求的她形成了鮮明對比,流露出一種無力挽救的悲劇感。《春風沉醉的夜晚》中自殺的王平,江城的離開對他如抽絲削骨,離開的不僅是伴侶更是唯一的港灣,王平成了孤獨的個體,最終選擇自殺。劇作中,將主人公認為最重要的東西(情感、愛人、信仰、夢想等)拿走后,人物便會產生強烈的反應。作為一部同性戀題材影片,婁燁呼吁大眾不要將同性戀作為奇觀而讓他們喪失生存的社會空間,不要將他們妖魔化,應包容更多的愛情存在形式。
二、人物與世界的悲劇性關聯
(一)人物處境的進退無所
人在長時間的社會生存與成長中會形成人物特有且相對固定的生活處境,迫于很多外力人會不愿意甚至不能打破生活的平衡,因為他們承擔不起打破平衡的后果。當人物處于不平等或是被控制的處境時仍無法擺脫困境,人物悲劇性便展現了出來。
《浮城謎事》中的桑琪,婁燁對她是有悲憫之情的。桑琪作為喬永照穩定的婚外情伴侶,所有經濟來源皆倚賴喬永照,她卑微地接受著施舍而成為喬永照欲望的發泄口,導演將她的悲劇性基調奠定了下來。其后因桑琪沒有遵守承諾影響了他的家庭,喬永照對桑琪進行了毆打和強暴式的性行為。劇情的發展慢慢滲透著桑琪處境的卑微,她沒有人物選擇權,須逆來順受接受著對方的施舍或發泄,她不敢打破這樣的處境,一旦打破她的生活便會陷入更糟糕的境地。《春風沉醉的夜晚》中,江城是一個在愛里妥協的人,一直接受著愛人的安排處于被控制、被選擇的地位。江城最大的悲劇來自現實社會,在遭到林雪報復后,他蜷縮著倒在血泊中,過路人冷眼旁觀這一切,就如銜接鏡頭中路人冷眼旁觀狗的尸體一般。路人看到這樣的場景表現為好奇觀望、冷漠相待,即使這個生命與你無關,婁燁也希望在社會中多幾分人文關懷。亞里士多德定義悲劇時指出“悲劇引起憐憫與恐懼而得到情感的凈化與陶冶”,而悲劇創作的目的就是喚起人們的憐憫之心,婁燁也正是想通過這樣的人物處境來激發觀影者的憐憫之心和關懷之情。
(二)人與人的失效溝通
人從出生起就注定會產生個體性格或觀念差異,在不同的成長環境或是不同的人生經歷下,每個人的訴求是不同的。在人與人相處時,如果個體訴求無法得到對方的回饋,個體內心便無法獲得滿足,亦會產生對對方的不信任,彼此之間便無法建立有效溝通,進而致使人物關系走向破裂,人物關系的悲劇性由此產生。
婁燁在《蘇州河》中一早就埋下了牡丹和馬達走向悲劇的種子。他們生活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因一場交易相識。兩人相愛后牡丹無法面對馬達為了金錢綁架她的事實,她將愛情視為無價,一旦變質只能走向毀滅。她沒有給馬達任何解釋的機會,仰面墜入蘇州河,用這種方式堅守著純凈的愛情。導演通過美人魚的童話故事揭示現實,雖親手搭建美好愛情,卻將這份愛放置于現實社會中,那么純凈的愛一定會沾染上雜質,便親手將愛情推向了悲劇。《浮城謎事》中夫妻關系破裂出于兩人無法建立有效溝通,揭露社會家庭關系存在的普遍問題。陸潔與喬永照的婚姻太過相敬如賓,夫妻生活成為一種形式,喬永照用謊話一直欺騙著陸潔,維系著兩人搖搖欲墜的婚姻。面對丈夫的出軌,陸潔隱藏自己知道實情的真相,選擇用偏激的行為來捍衛家庭。兩人無法建立有效溝通,婚姻關系最終走向破裂。
三、人物悲劇的意象性表達
(一)被“異化”的身體意象
巴塔耶認為:情欲并不像傳統道德所歪曲的那樣,恰恰相反,性和情欲具有帶領生命進行自我滲透和自我反省的特殊功能。電影好比一面鏡子,透過人的身體讓我們更多地感悟生活,這才是探討銀幕身體的價值所在。婁燁電影以其自有的方式再現生活中的悲劇,在人與人無法建立有效溝通時,便放棄了精神交流的可能性,陷入極度失望中,無奈將溝通簡化為身體行為,婁燁借此來展現身體意象的悲劇性。
《頤和園》中的余虹是身體意象最典型的人物。余虹的愛情觀是與身體粘連在一起的,她極度缺乏安全感,選擇簡化溝通的方式試圖用身體去獲取對方的信任與了解,余虹的悲劇性赤裸裸地展現出來。《春風沉醉的夜晚》中婁燁用具體意象——江城身上的蓮花文身來表達悲劇性。江城經歷了王平的自殺、羅海濤的背叛、林雪的中傷、路人的冷漠,他用真誠的愛盡力與生活對話,但依舊被選擇、被控制、被傷害,他與外界的溝通是失效的。而蓮花便象征江城對生活的向往,同時他也想表達出一種對世俗倫理的鞭笞,被世俗所異化的人在有形與無形中承受著悲劇人生。錯亂的愛情關系不代表不可以被世俗接受,他們依舊可以保持內心的平靜,希望在某個春風沉醉的夜晚,可以與愛的人一起散步,不論年齡,不論性別。而電影中身體的展示并不是嘩眾取寵,往往承擔敘事功能,投射人物內心。裸露的身體不是奇觀,不做窺視,不是觀眾欲望的投射,不必費盡心機隱喻,只需在符合人物情景與情節發展時表達內心。
(二)荒謬無力的暴力意象
人和動物都是游離于生死兩極本能之間的。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視角來看待死亡的本能,死本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種是其能量向外投放表現為破壞性、攻擊性、侵略性等,并以暴力、戰爭等形式釋放出來;另一種是其能量向內投放,表現為自責自罪、自我懲罰、自我毀滅等,是以內爆的形式對身體實施暴力。而暴力悲劇的演變是有過程的,人物在積蓄了很多無法宣泄的情緒,或是通過很多方式無法解決困境時,暴力的因子會讓人失去理智走向悲劇。
《春風沉醉的夜晚》中的喬永照,他是悲劇的始作俑者。保證喬永照婚外情與家庭關系互不影響是他的底線,桑琪一旦越界,隨之而來的會是喬永照拳頭的懲罰。他其后對拾荒者的暴行是出于拾荒者無底洞般的敲詐,最終選擇用極端方式徹底解決問題,暴力成了人與人溝通失效的不良異化方式。《推拿》中的盲人王大夫,他無法和正常人一樣進行溝通,他嘗試了很多辦法都沒奏效,無計可施選擇了身體暴力,通過用血和肉的方式償還弟弟的賭債,刀口和血液是那樣真實,這個辦法是奏效的,他嚇退了討債的人,但讓觀眾看著比死亡還要揪心。婁燁通過無奈而血腥切割身體的方式,望大眾不再做眼不盲而心盲的冷漠路人甲。暴力成了主人公擺脫困境的方式,無論是對他人的暴力還是自暴的行為,用直觀殘忍的方式講述著主人公內心哀傷。然而當暴力成為一種宣泄的時候,那么受虐者或自暴者本身就形成了一種自我傷害的惡性循環,所有的困境都通過暴力手段解決,生活的悲劇會演繹成惡性的輪回。
婁燁作品大多關注社會主流文化邊緣命題中的邊緣人物,這些人物是處于社會歷史背景下的集體記憶,所代表的是一種復合的、立體的心靈世界。悲劇在婁燁的作品中展示出獨特的美,通過悲劇性寫實讓觀者產生更深刻的心靈撞擊,在論證悲劇性的同時也在不斷思考著當下社會人的悲憫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