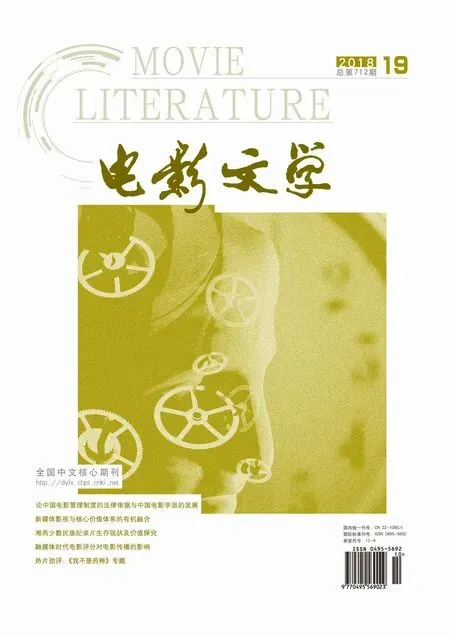哈薩克族電影《永生羊》對族群認同的建構
梁新榮
(伊犁師范學院 人文分院,新疆 伊寧 835000)
《永生羊》是一部以新疆哈薩克牧民生活為題材的電影,哈薩克族作家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編劇并擔任副導演。《永生羊》曾參加第34屆加拿大蒙特利爾電影節電影處女作競賽單元的評選,并成為所有參賽影片中唯一入圍,而且進入競賽單元的中國電影。這部影片除了男女主演外均采用了新疆當地的非職業演員,以原生態的影像全景般地展示了哈薩克族游牧人生活的風貌,為觀眾呈現了一個質地凝重深厚的人文新疆。
文化具有地域性,特定的地域文化圈因其特定的生態環境而具有獨特的文化特征和發展方式。作為中華民族多元文化圖譜中的哈薩克族文化因其地域、生活方式、宗教,而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對于哈薩克族——這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而言,人和草原、自然關系不同于他者。在他們眼里,人與自然以及包含牛、羊、駱駝、馬甚至狼在內的草原生態系統,不存在彼此的差異和相互對立,而是都具有等值的生命價值。《永生羊》電影以其史詩般緩慢的節奏向觀眾娓娓道來,畫面盡善盡美,給人以詩歌般的意境,其間不乏創作者對傳統民族文化的眷戀和反思,同時堅守哈薩克族文化的獨立性和純粹性。這樣的影像表達以新疆地域文化為特色,為哈薩克民族文化立此存照,對于整個哈薩克族文化的書寫是極其有意義的。
一、原生態影像表達下的哈薩克族群文化
“原生態”是指沒有經過特殊人為加工和刻意雕琢,并存在于自然狀態下的質樸本真、自然純凈。對于民族電影中的一員——哈薩克族電影而言,哈薩克族群文化的原生態影像表達是以多樣的電影藝術表達方式、濃郁的民族元素展開電影敘事的。《永生羊》作為哈薩克族原生態電影的代表之一,在創作注重呈現哈薩克牧民的真實生活,在演員選擇上除主角外全部用本民族非職業演員,在對白上運用母語同期聲,向觀眾呈現出新疆的絢麗草原和冰雪世界的多彩景觀,真實地反映了哈薩克族的游牧生活。
(一)《永生羊》在電影藝術表達方式上具有獨特的哈薩克族特色
《永生羊》從哈薩克族群的視角切入,散發出自然而純粹的本民族意識。哈薩克族人的游牧生活和社會記憶是逐水草而居,在周而復始的轉場地點中發生。地理的遷徙構成了哈薩克族一種獨特的生存方式。羊群正是在地理的遷徙即牧民的轉場中獲得生命的延續和循環。哈薩克族也正是在這種地理的遷徙中代代繁衍,生生不息。導演為呈現哈薩克族人這種獨特的時空觀,在《永生羊》的影像表達上,獨具匠心地利用轉場來表現空間的遷徙和時間的流逝。哈薩克族牧民的轉場有固定的路線,遵循四季的變化,有不同的牧場。這種轉場行為是一種遵照族群記憶和習慣的循環遷徙,每一次的出發是為了下一次的回歸。在電影的敘事結構上,《永生羊》沒有采用一般電影慣用的以時間變化為軸的表達方式,而是通過四種空間的轉換,即“春牧場—夏牧場—秋牧場—冬牧場”進行敘事,使人物的情感變化隨著空間的轉換而得以呈現。在春牧場,小男孩哈力遇見紅臉老人,并接受了紅臉老人贈送的薩爾巴斯;在夏牧場,奶奶和叔叔凱斯泰爾為小哈力舉行成人禮儀式,烏庫芭拉在自己的婚禮上愛上花騎歌手阿赫泰后逃婚;在秋牧場,烏庫芭拉守寡后被人陷害,遭受丈夫家族的酷刑,并被丈夫家族驅逐后再嫁凱斯泰爾;在冬牧場,烏庫芭拉忍痛離開哈力一家,去守護自己的孩子;再到春牧場,奶奶離世。四季的遷徙轉場是一種生命的輪回,在這種周而復始的生命過程中表現了哈薩克族的生活態度及民族精神。
(二)《永生羊》展現了濃郁的哈薩克民族元素
影片中夏牧場拍攝地點選擇了阿勒泰的那仁草原,位于我國新疆的最北端,與哈薩克斯坦、蒙古國、俄羅斯隔山相望。秀麗迷人、寧靜致遠的自然草原風光,體現出了哈薩克族群文化中的靜默氛圍,讓人領略到了那種在寧靜中蘊蓄的民族審美張力。哈薩克族是“馬背上的民族”。這種春夏秋冬不停游牧遷徙的生活方式,決定了其生活用具的特點。在《永生羊》鏡頭中出現的易拆易搭的氈房、收納衣物的木箱、防潮隔濕的地氈、方便拆裝的兩頭高木床等生活用具正是哈薩克族人日常生活離不開的家什。影片中這些拍攝道具的歷史真實性和客觀性,進一步再現了哈薩克民族的生活記憶。還有溫暖寧靜的冬窩子一方面烘托了人物的思緒情感,另一方面也呈現了哈薩克人與自然和諧的自然觀。服飾是特定民族和時代的形象表達,《永生羊》影片以中間灰、紅土底、松樹褚、炭火黑、橄欖綠等彩色為主基調的哈薩克族服裝為電影提供了重要的形象空間。哈薩克語的使用是電影突出身份認同的又一重要表現。該片全部采用哈薩克語對白,并配有中文字幕。哈薩克母語的使用既可以喚起哈薩克族觀眾內心強烈的身份認同,又能將“自我”族群存在傳達給他族觀眾,強有力地構建出了哈薩克族群原生態文化。
電影影像也是一種文化解釋,當我們把電影影像看作是文化解釋的另一種特殊文本時,其中所展現的各種文化也隨之或淺描、或深描地呈現出來。《永生羊》編劇兼副導演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以其特有的鏡頭語言真實地展現了她對于本民族文化的理解、認同與堅持。電影《永生羊》通過虛構與現實的混合還原了新疆哈薩克民眾的日常生活。哈語對白、哈薩克族非職業演員出演、實景拍攝,生活化地展現了新疆哈薩克族牧民真實的生活。《永生羊》導演非常高超地將哈薩克文化隱沒在日常的瑣碎中,從而引起文化觸動,這是作為具有族內視角的民族電影影像所獨有的魅力。這部大范圍用原生態演員的民族電影,貫穿整部影片的溫情、隱忍及堅強,極具滲透力和表現力。它直白坦誠、淳樸鮮活的影像表達特性,使這個平和靜謐的電影在眾多世界優秀影片中成為加拿大蒙特利爾電影節電影處女作競賽單元的一個意外驚喜。
二、傳遞哈薩克族草原文化情感邏輯與生命哲學的影視節奏
節奏即律動,是事物有規律的運動。《禮記·樂記》疏說:“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斗轉星移,春去秋來,花開花落,這是宇宙萬物普遍運行的節奏,這種萬物運行的自然節奏內化在電影藝術中則形成了精彩的影視敘事節奏。電影是由活動的影像畫面構建而成,電影節奏就是電影藝術家們將他們的思想感情和情節、鏡頭的綜合運動以藝術的方式結合起來的運動形式。
(一)敘事節奏
電影的敘事節奏是指在電影劇情中矛盾沖突的發展節奏,它對整部作品的節奏有著充分的影響。凱瑟琳·喬治在其《戲劇節奏》一書中認為:“劇作家用文字向我們提供最終將出現在觀眾面前的內容。而其他的藝術家則起著把紙上的文字變成話,呈現給觀眾的作用。他們都必須對節奏(劇作家的節奏)具有敏感,必須在他們各自的藝術領域里運用節奏。”這段理論雖然是針對戲劇節奏的理論,但在電影領域也同樣適用。電影《永生羊》通過哈薩克老人哈力少年時的回憶,用史詩般的敘事節奏,講述劇中人物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將觀眾帶進了哈薩克小男孩的世界。導演將鏡頭對準華美壯麗的喀納斯,再加上悠揚的配樂,讓觀眾領略到濃郁的新疆自然風光及哈薩克族的人文情懷。攝影機游離在新疆阿勒泰草原上,所有的演員以及被包容在電影中的每一個細節,都緩緩流淌出所有關于哈薩克文化的信息:慈悲、寧靜、和諧與包容。《永生羊》敘事節奏是緩慢的,它扎根于哈薩克族文化的寬廣草原,致力于表現哈薩克民族的人文歷史變化,努力讓電影回歸本位,用淳樸的哈薩克牧民和并不曲折復雜的故事情節去講述,用哈薩克族的日常生活和古老民俗去發聲,用平淡自然的節奏去發聲,讓觀眾在真實的長鏡頭中,去體味時光靜靜流逝的過程。宰羊的獻祭儀式如潺潺細流貫穿于《永生羊》全片中:影片開場小哈力以巖畫的方式在巖壁上再現了這一儀式;在小哈力的成長儀式上,凱爾泰斯念著“你死不為受罪,我生不為挨餓”的祭祀語實行了獻祭;叔侄二人在冬牧場偶遇一群凍死的母羊,并在風雪中對即將垂死之羊實行了獻祭儀式;許多年后,長大的哈力為去世的奶奶實行了羊的獻祭。老年哈力在影片結尾處說:“生命世界原本就是循環往復的。縱使有太多的薩爾巴斯為我們犧牲,依然有更多的薩爾巴斯延續著它的生命。”《永生羊》的敘事節奏基調如一部哈薩克族人的抒情史詩,沒有大起大落的故事情節與波瀾壯闊的矛盾沖突,卻有著寧靜的韻味,如同靜靜流淌的額爾齊斯河。
(二)影像節奏
影像節奏對于電影,也是極其重要的。法國著名電影理論家萊翁·慕西納克曾說:“很少有人懂得賦予一部影片以節奏和賦予畫面以節奏有著相等的重要性……電影就是節奏,不然就是死亡。”《永生羊》導演采用靜止的長鏡頭去講述故事,影像節奏是緩慢而充滿詩意的。影片沒有花哨的構圖、絢麗的色彩等時髦的鏡頭處理,大部分鏡頭都是依靠緩慢的長鏡頭來完成的。悠長而緩慢的鏡頭運動路線和大幅度的鏡頭調度和拍攝角度使得演員的走位、表演得以完美呈現。草原大戶人家蘇丹的女兒烏庫芭拉美麗多情,被父母強行許配給母親家族中的人。她在婚禮舉行過程中,與前來赴宴的花騎歌王阿赫泰一見鐘情并私奔。哈力的叔叔凱斯泰爾深深暗戀烏庫芭拉,卻羞于啟齒。后來烏庫芭拉丈夫因病去世,她獨自撫養兩個孩子,卻受到丈夫家族的猜疑和欺凌。哈力與莎拉奶奶救下了落難的烏庫芭拉,并撮合了烏庫芭拉和凱斯泰爾。但強烈的母愛驅使烏庫芭拉主動放棄來之不易的幸福,重返前夫家。《永生羊》中每一幀畫面,以及潛流于鏡頭底下的情緒張力,在某種深層意義上闡釋了哈薩克族草原文化的情感邏輯與生命哲學。影片的一個經典鏡頭就是凱斯泰爾叔侄倆宰羊祭祀的儀式,叔侄二人、羊和草原呈剪影狀,為祭祀儀式提供了莊重、神圣的視覺感。導演用細膩精妙的鏡頭去呈現這一段,并沒有十分刻意地去表現環境,而是讓人物的情感自然而恰當地流溢在每一個與自然環境有關的鏡頭里,從而使影片的整體觀感純真質樸。《永生羊》電影中的新疆影像是民族電影文化敘事的一支,也是新疆歷史敘事的一部分。
在中華民族的文化版圖上,少數民族電影是一支中國與世界對話不可或缺的文化生力軍。影片《永生羊》有著濃郁的地域元素,用新疆本土化的語言,承載了哈薩克族的傳統精神,具有民族電影特有的地域文化特性。電影《永生羊》營造了一個質樸真實的哈薩克族的影視表達空間,讓觀眾心靈進行了一次凈化之旅,同時也讓人明白了對世間所有生命的尊重與關懷。《永生羊》中這種大自然和哈薩克民族所賦予的平衡性,使觀眾感受到一種對生命的虔誠與和諧,其反映了哈薩克人對待生與死、對待愛、對待親情和對待生活的一種平和、謙卑之態。在當前全球一體化又日漸多元化的語境之中,尤其是在以商業片為主的影視傳媒語境中,邊疆民族電影漸趨邊緣化,游離于主流文化之外。因此,邊疆少數民族電影的身份認同對于解決邊疆少數民族電影發展的市場困境、弘揚民族文化、鞏固邊疆地區的穩定與團結有著重大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