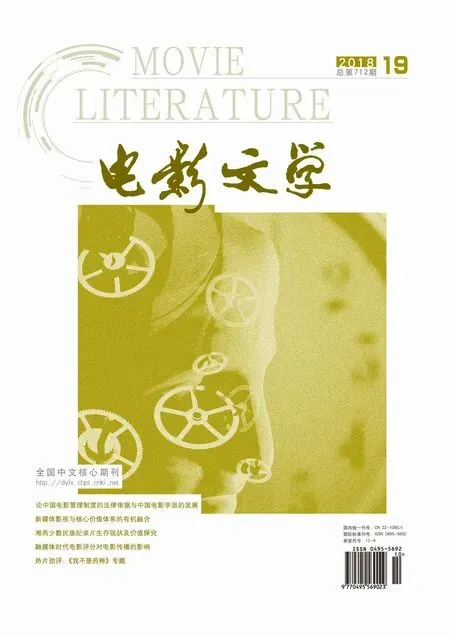《貓與桃花源》的個性化敘事
陳衛平
(廣州大學 美術與設計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經由長期的創作實踐以及對市場反饋的總結,人們早已認識到,動畫電影需要貼合人類的共同情感,以喚起觀眾的共情,以及呈現出一種個性化的,本真的面目,以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縱觀近年來逐漸迷失的國產動畫電影,我們不難發現,大量功利性目的明顯的作品出現了千篇一律,難以打動觀眾的現象。
從《小門神》(2016)到《阿唐奇遇》(2017),再到《貓與桃花源》(2018),由王微帶領的追光動畫團隊可謂是一再以優質內容給予了觀眾驚喜。尤其是借鑒了前兩部作品經驗的《貓與桃花源》,其對細膩情感的刻畫,對人物精神自我實現這一深度的追求,更是讓觀眾眼前一亮,與部分或被詬病為低幼,或是淪為硬性說教的動畫有著明顯的區別。當人們不斷探尋國產動畫的敘事體系時,成功實現了個性化敘事的《貓與桃花源》無疑為業界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一、主體意識與主觀情感
《貓與桃花源》的個性化敘事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其中的主體意識與主觀情感。只要對追光的動畫電影稍作了解就不難發現,王微在這些電影中基本上都扮演了一個“作者”的角色,從《小門神》到《貓與桃花源》,電影均為王微自編自導,它們都摻雜了王微作為作者的主觀思想,包括某種認知,價值取向和態度判斷(如對門神等傳統文化的態度等)。只是在電影中,電影作者并不是抒情和敘述主體,他深切而微妙的生命體驗與生活感悟是寄托在一個個人物身上的。
在《貓與桃花源》中,毯子和斗篷父子,以及黑貓等角色就成為抒情與敘述主體。在電影中,隨著金剛鸚鵡的到來,毯子說起自己向往的桃花源,并且欺騙愛子斗篷他的母親就在桃花源里。對自由的向往以及對母親的想念,促使斗篷幾次三番離家出走,最終憑借著自制“火箭”從高樓一躍而出,跨過江面,落入一個陌生的世界中。而由于父子情深,毯子也不得不在金剛的幫助下開始了尋子之旅。這一次歷險實際上對于父子二人都是一次找尋自我、重拾自我的旅程。毯子重新認識了“桃花源”這個理想國,重新定義了自己內心中的美好生活,而斗篷則在成長中改變了對于“貓不能飛”的認知。對于桃花源,毯子的態度是“夢想—失望—重燃希望”。多年以來,桃花源是毯子心中的圣地,但在冒險之后,黑貓告訴他桃花源并不存在,一切只有一個湖。而在動物們坐玻璃船潛下湖底后,大家真的發現了一個美好的世界。由于妻子的死,毯子一再告誡斗篷“貓不是鳥,貓不能飛”,而斗篷則不甘心地鉆研著各種飛翔和滑翔技術,嘗試著用蘇打水、螺旋槳等飛行,它最終懷著“也許貓真的會飛”的信念決定四處闖蕩,他說母親也許并沒有死,她終將和自己相遇。這并非斗篷的自我欺騙,而是他作為年輕人不愿停留,追求自由的活力和熱情的體現,這也是人生需要一次次超越自我,實現理想的某種象征。父子倆盡管遭遇過痛苦、脆弱和絕望,但都變得更為成熟。
電影中的貓不被限定為人類豢養的“寵物”,是在衣食無憂的情況下依然渴望飛行,向往大自然的靈性生物。“桃花源”更是意指人們內心的凈土,人們可以以“此心安處是吾鄉”之心待之,如毯子最終還是決定回到養育自己多年的主人身邊,這意味著當人們已經獲得心靈平靜時,隨處即可是“桃花源”。可以說,這種立意是頗具高度的,同時也是極為主觀的。王微等主創將個人的思考傾注到畫面之上,并表達出了非常明確的情感立場和價值判斷。
對于其余電影人來說,《貓與桃花源》具體的思索和感慨固然無法因襲,但是如其主創一般,對電影敘事采取介入態度,卻是完全具有可行性的。
二、個人體驗與移情
在《貓與桃花源》中,由于主創這個“我”的在場,也就導致了諸多角色并不是只是一個單薄的功能性角色,而能帶給觀眾一種真實可感的,具有代表性的生活體驗。在生活的磨礪中,毯子逐漸失去了對外界的向往,在溫飽不愁的生活中得過且過,但在這次奇妙的冒險中,毯子的心靈得到滌蕩,他從失去妻子的痛苦之中走了出來;玻璃廠老板則在藝術才華受到商業社會制約的情況下,隨著工廠年復一年地沒落而陷入到迷失、焦躁乃至瘋魔的狀態中;浣熊則代表了社會中最為圓滑世故的一部分人,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助紂為虐,狐假虎威,幫玻璃廠老板捕捉、羈押動物,隨意破壞黑貓酒吧中的財物,但是當玻璃廠老板失勢時,浣熊果斷投向了動物們一方,表示“我早就不想跟他干了”,并且緊跟想重開酒吧的黑貓,說“酒吧不需要一個合伙人嗎”;黑貓則長期自我放逐,無力阻止舊主人的日益墮落,又不舍得離開舊主人,而只能開一間酒吧自我麻痹并在能力范圍內保護如斗篷這樣的小動物,并最終在勇往直前的斗篷身上重新找回了赤子之心,跟著斗篷一路高歌猛進。
電影中的大部分角色都是現實社會中一類人的縮影,有著和普通人一樣的基本感情和困惑,觀眾對他們必然產生較為復雜的感情。這種對現實生活體驗的移植正是“擬人和移情”(與之相對的則是“寫物主義”的擬物和泛情)敘事模式的體現。電影中角色作為客體被主體化,觀眾則在“物性”中發現“我性”,直視角色的內心深處,將個人感受注入對電影的理解中,審美主體和對象之間實現“我—你”而非“我—它”的良好的對話。而這些在個人體驗豐富的角色,在大量人物扁平化,人物設定或高大全或奸惡,人物背景罕有交代的動畫中是罕見的。
而必須說明的是,除了作惡多端的玻璃廠老板以外,其他幾個角色均得到了積極、樂觀的結局。這并不能被簡單地用以指責電影拋棄個性,迎合大眾,這一方面是電影主創最主觀意愿進行理想化表達的產物,另一方面則與動畫與現實之間具有反構關系有關。絕大多數的真人電影和現實之間是同構關系,即真人電影是對現實的一種模仿,真人電影中的虛構在創作之初就已確定了對現實是靠攏而非取代的關系。而動畫電影則最大限度地脫離了現實的束縛,為觀眾構建了一個新的空間,并且這一空間飽含了人類的共同情感和普遍理想,這就導致了想象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比現實更為“真實”,觀眾在觀影過程中能夠暫時性地遺忘現實的結果,這就是動畫電影中的虛構對現實的一種取代。在動畫電影提供的反構世界中,人物與人物之間的情感往往是真摯的,人際關系是溫暖正面的,一言以蔽之,動畫電影更貼近人類兒童時期對外部世界簡單而美好的好奇,理解與幻想。這種反構世界也是動畫電影能夠對備受現實困擾的成年觀眾依然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
三、悲劇意識
缺乏悲劇意識,缺乏批判精神,是黃發友指出的“寫物主義”敘事傾向的嚴重缺陷之一。盡管這是源自文學批評的論述,但其同樣適用于動畫的敘事。在近年來的國產動畫電影中,這種傾向是存在的,動畫電影向著奇觀化、時尚化和消費化的方向發展,動畫人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3D等技術之中,在敘事上,觀眾看到的是類型化的人際關系,空殼化的人物情感,以及被反復復制的皆大歡喜的,令人無須回味的大團圓結局。而在《貓與桃花源》中,由于主創投入了真實、強烈與自發的情感態度,電影也自然地流露出了某種悲劇意識,這也是電影充滿個性,避免落入“快餐化”窠臼的亮點。
在《貓與桃花源》中,由于電影并沒有給出斗篷母親死后的樣子,同時人們又對于貓能夠高空墜落而不死的“貓有九條命”的認識,觀眾往往會產生斗篷母親將在電影最后露面的審美期待。然而在斗篷黯然面對桃花源中的其他小貓有母親疼愛時,他的母親并沒有出現。在電影的設定中,斗篷的母親確實摔死了。而斗篷此后對她的尋找也將是沒有結果的。一心找到兒子的毯子最終也不得不和兒子分開。這種悲劇意識早年在如林文肖的《雪孩子》(1980)等動畫中曾經出現過,無數觀眾正因為惋惜雪孩子的死而對這部動畫印象深刻。近幾年出現的《大圣歸來》(2015)、《大護法》(2017)等,善良的江流兒被殺,意志覺醒的小姜被殺,也能讓人感受到其中耐人尋味的悲劇意蘊。而玻璃廠盡管被毀,但是老板人格扭曲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他還將生活在藝術商業不能兩全的痛苦之中,他盡管就住在桃花源的地理位置旁邊,但又是注定到不了桃花源的。電影的批判精神也由此產生。正因為主創并未將自己置于一個旁觀者的位置,在創作中流露了對世間諸事不能盡如人意,對人在命運之前軟弱無力的悲憫,才能夠設置出這樣能讓觀眾移情的略帶傷感的,并不完美的結局。相對于主人公過于順利,人物的經歷和轉變等被概念化圖解的敘事而言,這種設置有著一種不可抗拒的、一枝獨秀的力量。
四、《貓與桃花源》個性化敘事啟迪
毫無疑問,動畫電影并不應該排斥個性化敘事,反之,只有主創勇于嘗試,推陳出新,進行“我”的思想結晶或藝術取向“在場”的表達,國產動畫才有可能大放異彩。如林文肖的電影,除了前述《雪孩子》以外,以及她的《夾子救鹿》(1985)和一系列“小兔淘淘的故事”等,就被認為是國產動畫電影個性化敘事的典范。強烈的抒情性壓倒戲劇性,就是林文肖動畫的個性之一。“就如《小鯉魚跳龍門》……國產動畫片中的佳作,大多也是以講述故事為主要目的的。編導者都是在盡力把故事的情節編撰得曲折豐富、引人入勝,力求通過故事敘述傳達教育主題。而《雪孩子》中,我們發現,林文肖寧可用大段的場景動作結合音樂來描寫雪孩子在冰雪世界里玩耍,也沒有把精力用在為雪孩子制造一些‘感人的事跡’上,可偏偏就是這些‘沒意義’的抒情段落打動了觀眾,讓他們記住了、喜歡了雪孩子,甚至多年難忘。”可見,帶有強烈個性的敘事動畫,往往更能讓觀眾心動。
另外,不可否認的是,當下,教育性敘事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國產動畫電影的萎縮。自我國動畫電影誕生之日起,教育性敘事的理念就已存在,動畫電影往往負載著在品德、科普和文化三方面的教育作用。這是無可厚非的,尤其是對于低齡受眾而言,動畫電影為他們營建了一個可以獲取經驗驗證,以及本土優良文化熏陶的第二世界,有低級內容的動畫電影無疑會對其產生不良影響。只是由于難以處理好“教”與“樂”的關系,部分電影的可看性大大降低,與主創個人思想相關的對世界、人生的多元理解,與主創藝術個性緊密相關的深遠意境、創新意象等,都不得不讓步于功利性極強的說教。主創與受眾之間并非平等交流的關系,而是主創處于居高臨下的位置,觀眾成為被灌輸者。這必然導致國產動畫幼稚、重復,個性泯滅,無法與大部分觀眾產生共鳴,最終喪失成人這一龐大的動畫產品消費市場。在目前人們對《貓與桃花源》的反饋中,不乏成人看到追逐夢想的可貴,兒童意識到家庭、父愛意義,或意識到勇敢面對困難等的正面評價,可見即使主創在敘事中展露個性,不進行硬性說教,教育功能同樣是可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