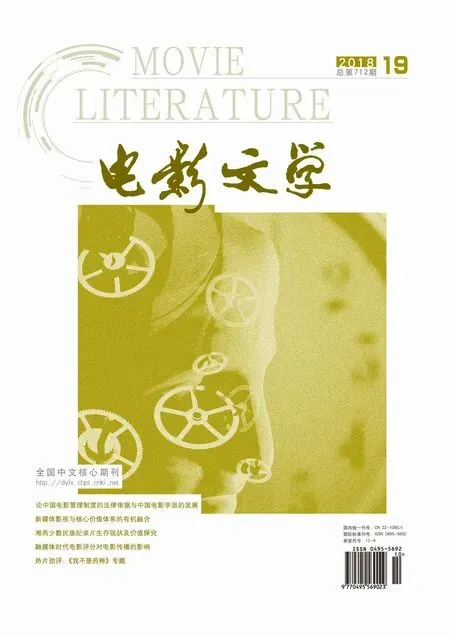《第三度嫌疑人》中新歷史主義文本敘事
干瑞青
(山東政法學院 傳媒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是枝裕和導演的電影作品《第三度嫌疑人》,雖有懸疑成分,卻缺少推理的環節;雖有法律體制、人性的拷問,卻缺少深層的社會反思。影片在一次次探尋三隅殺人動機的過程中,把律師重盛拖入了真相敘述的旋渦中。影片也許是導演提交給觀眾的一次新歷史主義的文本敘事,因為其中蘊含著新歷史主義式的批評,目的不在于“實現歷史現實的回歸,它只能提供對于歷史的又一種闡釋”。
一、三隅殺人事件是一個孤立、片段化的歷史事件
歷史是關于過去的某種東西,其目的是還原一種真相,它們類似考古學中某個石碑、某個遺跡或不可名狀的實物等,期待當代的人類去復現、去分析和解讀,它或是一種細節描述,或是一種具體記錄,但作為記憶在證實某種過去的存在。三隅殺人事件是一個歷史事件,因為三隅高司作為殺人犯已經被關進監獄,而且影片展現了一定的片段性的本源性事實基礎和眾多的孤立的過去事實的痕跡在確認這個歷史事件的存在。
(一)三隅殺人事件的片段性的本源性事實基礎
律師重盛朋章和助手川島輝來到河岸邊的殺人現場,尸體被焚燒后遺留的十字形印記表明這里曾經有一個人被殺死和焚燒過程。帶有汽油的錢包、錘子等物質證據表明這些與受害人死亡有一定的關聯。出租車記錄的“三隅高司坐入車中”影像和“去調布車站”錄音,以及受三隅所托,重盛帶給美津江和咲江的致歉信,這些構成了殺人事件的本源性事實基礎。尸體遺留的痕跡、錘子、錢包、錄音錄像及致歉信作為一種物質實在,成為一個殺人事件的重要構成部分,因為它們是“‘延遲’和‘保留’的跨越式結構,其中有著它自己的過去和未來的幽靈”。雖然其中沒有線性組接關系或因果邏輯的順序,但卻以痕跡的形式證明了一個殺人事件確實存在過。
(二)三隅殺人事件中其他孤立性的事實痕跡
三隅殺人事件中其他的事實痕跡涵蓋了其過去及家庭、曾經租住房屋、山中食品廠等。律師重盛的助手川島輝對櫻井的問詢證明了三隅與被害人山中存在的雇傭關系。房東太太帶著重盛進入三隅曾經租住房屋,簡陋的家具、花生醬、鳥籠及鳥的墓冢都在訴說著三隅在此生活的時光。冰雪覆蓋的北海道小鎮,老警長渡邊手中報道三隅30年前殺人的事件的報紙,夜店中店主關于三隅女兒香里聽惠的講述,這些都證實三隅高司出身北海道、曾經殺過人、有一個討厭他的女兒,這是三隅高司的個人歷史,無論是否為滿足觀眾的好奇心去進行殺人動機的探尋,它確實存在過。這些事實痕跡在律師重盛及其助手引領下具有再次語境化的渴望,它們試圖進入三隅殺人事件的歷史中,導演期望它們構成殺人過程的鏈條,為不斷搖擺的殺人事實奠定物質基礎。
電影中交代的三隅殺人事件的本源性事實及其他事實痕跡都帶有瞬間的狀態,這樣確實符合新歷史主義的視點,這些帶有瞬間特點的事實在呈現自主自在或純粹性時帶有一種神秘性,它們需要一種解釋,無論是向前的指涉或是等待被改變。
二、三隅殺人事件呈現的是一個新歷史主義的文本
當福柯運用“斷層”“差異”來攻擊傳統歷史批評方法時,人們發現了人類以自身的想象性邏輯來代替事物之間的聯系,用語言的闡釋來抹除事物之間的“差異”和“斷層”,其實我們用以考察和把握歷史觀念及原則的只是一種話語,或是一種再次進行闡釋的文本罷了,這就是新歷史主義的歷史的文本化。許多大家對新歷史主義都做出過解釋,無論是去權力化、去政治化,抑或小歷史化,都不要忘記“‘歷史文本’并不是一個關于‘虛無’的文本,……而是一個對于曾經實實在在地發生過的‘事件’的記錄、敘述和闡釋”。殺人事件在三隅的自我闡述、律師重盛及檢察官等的解析、女孩咲江的揭露中呈現出真相的多樣性,也證實了導演要進行的歷史文本化的敘事實踐。這絕非羅生門化,作為一個歷史文本,殺人事件在不同角色的闡述中都依托了一定事實依據,并把它們串聯起來,好像自然而然地發生在過去。
(一)三隅高司的自我闡述中對殺人事件的涂抹修改
三隅在闡述中出現了大量的“大概是”“記不清”等模糊詞匯,并且在承認與否認之間多次徘徊,體現出他有意隱瞞事件真相,并對殺人過程進行多次的涂抹修改。首先,三隅對自己殺人動機的多次修改。三隅在第一次見到律師重盛時,首先承認人是他殺的,殺人動機是要錢賭博,而且是酒后一時沖動殺了人,否定了之前的蓄謀殺人的說法。在第二次見到律師重盛時,承認自己對雜志說,受山中社長夫人美津江所托,是為了保險金;與美津江的通話證據是“不要說出我的事、我不會做對你不利的事情”。另外,三隅以隱語的方式涂抹自己的殺人動機。在第四次面對重盛的質問時,三隅“我覺得那種人被殺活該”“世界上有那種沒有被生下來才好的人”“重盛先生(律師重盛的父親)那邊不就這樣在解決問題么(指律師重盛的父親反對免除死刑這件事)”來反問律師重盛。尤其是在第五次會面時,三隅說,他羨慕重盛法官可以自由地控制人的生命。這些言辭都充滿了未能言說的殺人動機。其次,以隱喻的方式來模糊殺人過程。面對重盛質問金絲雀死亡的事,三隅說,就算現在放生,它們也活不下去,明示自己計劃了金絲雀的死亡。預交房租也在暗示自己有了入獄準備。最后,三隅對殺人事件的完全否認。在第六次見面時,三隅以經常撒謊來否認與女孩咲江的熟識,并否認50萬是封口費而非殺人報酬定金。三隅還吐露,因為警察、檢察官、律師的誘騙才撒謊。甚至被宣判死刑后,他也把保護咲江的說辭當成不錯的故事。
三隅對殺人事件的涂抹修改,其實是導演或三隅把殺人事件當成一個可任意裁剪、拼貼的文本。錢包、50萬存款與搶劫、高利貸賭博、殺人報酬定金、封口費之間可以根據需要進行不同的情節編排,以合理性的面貌呈現不同的事件敘述形態,只是其中蘊含了一種談判協商,“文本與社會存在的各種力量之間的互動、妥協”,三隅的真實殺人動機在警察、檢察官、律師、法官各種力量的撕扯中不斷地發生改變,在多次、主觀地修改和涂抹中,三隅殺人事件變得不可辨認。
(二)律師重盛及檢察官等在殺人案件解析過程中的排除與簡約
新歷史主義的文本敘事中揭示了歷史文本中存在一種排除和簡約的結構。由于受各種社會力量的制約,敘事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具有排除差異的潛能,而且總是由于“存在總被缺席和直接間接的語境痕跡所污染”而提示排除的存在。影片中,律師重盛及檢察官等在殺人案件解析過程中的存在排除與簡約,或是為了減輕三隅的罪行,或是為了法庭辯論,或是為了法官審判程序。首先,律師重盛只進行三隅殺人動機臆斷而對排除事實真相探尋。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律師重盛告訴助手川島輝沿著仇殺的思路去找線索;并且,在取得部分證據后,律師重盛及攝津等為了委托人的利益而預設社長夫人美津江為殺人主謀,排除了對動機的探尋,并據此進行法庭論辯模擬訓練。即使在第六次見面后,律師重盛等人也只是在三隅否認殺人和女孩咲江的真相敘述之間進行選擇、揣度,以確認哪一個更有利于法庭辯論術,而罔顧對事實真相的探尋。其次,律師重盛等人對三隅殺人動機簡約化。如擬定法庭論辯方案時,重盛把搶劫殺人變成殺人和搶劫,不管證據如何,僅僅因為似乎存在的工資糾紛就確定殺人動機是仇殺,并假設三隅因被開除而心生怨恨。重盛等人在質問美津江時,只關注保險金、情婦等問題,導致美津江的憤怒與拒絕。在庭審前第五次與三隅見面時,重盛建議三隅在面對質問時,要指認主犯是社長妻子。再次,律師重盛等人對證人的排除。律師重盛等人曾到北海道尋找三隅的女兒香里聽惠,在遭到三隅的抱怨后,他們再沒有繼續尋找,對親情證人的這種排除,其實是對三隅殺人動機的排除。即使面對女孩咲江出庭作證的要求,重盛等人以優先考慮怎樣挽救三隅為目的加以拒絕,排除了法庭展現女孩咲江關于殺人事件另類真相的可能性。即使因三隅否認殺人而休庭時,重盛等人默許審判人員繼續審判的行為,而沒有堅持從頭開始審判。另外,檢察官一方對短信的拒絕,排除了搶劫殺人或殺人搶劫的區別,而且與律師重盛等人一起默許審判人員繼續審判的行為,也是對案件真實方面的一種排除。
通過這一系列的排除和簡約行為,其實印證了攝津的話語:“大家都坐在同一艘叫作司法的船上。”律師重盛、檢察官、法官等不過是殺人事件文本中“特別意識形態傾向的代理者”。
(三)咲江及美津江關于殺人事件的另類文本
影片中女孩咲江的行為激發律師重盛的疑慮:一個被害者的女兒怎會去探望殺人嫌疑犯的住所,并對殺人嫌疑犯喜愛的花生醬感興趣,且即將就讀的高校選在殺人嫌疑犯的故鄉?為了給予這種種異常行為一個合理的解釋,導演或女孩咲江展開關于殺人事件的另類文本敘述。在第一次庭審后,女孩咲江告訴律師重盛等人,她曾遭受父親的性虐待,三隅為了救她而殺死了變態父親——山中社長。咲江不想如母親美津江那樣對這些熟視無睹,但是面對母親 “在法庭上不要說什么多余的話” 的警告,她也隱瞞了食品廠造假的事實。女孩咲江及美津江關于殺人事件的另類文本是對殺人事件的另類解構,是從源頭上對事件進行重述,它是一種充滿指涉意圖的存在,或是為了挽救三隅,或是為了掩蓋工廠造假……
三、三隅殺人事件文本的自我生產性
新歷史主義不但揭示了歷史的文本性,更點明了文本的話語結構特征。作為話語結構的歷史文本具有自我生產性,這不僅是權力運作、增值的要求,還是文本再語境化和延異。殺人事件在三隅高司的自我闡述及女孩咲江關于殺人事件的另類真相等都體現了其自我生產性。在影片中,關于30年前三隅殺人案件的再語境化,穿插其間的他人議論的并置使得三隅殺人事件文本呈現出延展特征。
(一)30年前三隅殺人案件的再語境化
三隅30年前殺人事件因為重盛父親的出現及渡邊老警長的敘述導致源語境的分解和殺人事件新語境的誕生。重盛父親以自責的狀態顯現,他在反省,因為“那時酌情判決的結果,又造成了別人的死亡”,而且以“殺人的人和不殺人的人有一條很深的鴻溝是否能跨越它,在出生時就決定了”的話語來定義三隅殺人的動機。渡邊老警長的對30年前審判的情景敘述,如“審訊的時候一遍一遍地改證詞,……三隅本人應該沒有什么個人怨恨吧,……就像空的容器一樣”。這種再語境化有利于律師重盛挖掘三隅殺人的真實動機,或是導演有意與當下的三隅殺人事件形成一種重復而發人深省。
(二)影片中有關殺人事件他人論述的并置引發的延展
殺人事件在各種層次的溯源中發生了一種延展,這種延展有關三隅本人,也有殺人過程的。例如在新聞報道殺人事件時,電視機前的攝津帶有譏笑的口吻說,看三隅的臉色就知道是干著呢呀(三隅與川崎夫人有通奸關系),而旁邊的女人馬上附和道,她看那女的一眼就明白了。這是一種補充的形式,它無疑增加了三隅殺人事件的更多維度。三隅所租住的房東太太對鄰居夫妻的八卦,雖然她稱三隅是很好的人,是一個連扔垃圾都很規范的人,但可以想象她是如何傳播三隅與年輕女孩子的故事的。田中食品廠工人似乎都有前科,櫻井的被嘲笑也可以為觀眾想象三隅殺人事件所引發的軒然大波以及它會被如何渲染。這些明顯或潛在的議論都使得殺人事件都到延展,并且會不斷地再生產。
四、結 語
影片《第三度嫌疑人》以特有的新歷史主義文本化的敘事實踐來展現導演對人性和社會法律體制的深沉思考,應該是技巧大于意義的電影嘗試。為了增強影片的吸引力或給予觀眾一種強烈的參與視角,電影把律師重盛朋章設定為了一個代理觀眾,試圖通過在對殺人事件的追尋中與角色一起去了解殺人嫌疑犯三隅,對他產生同情,最后甚至產生一種認同,而且有意設定重盛朋章有一個問題女兒,而且與女孩咲江一樣愛撒謊、有偷竊行為,這也許是對殺人嫌疑犯三隅的一種身份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