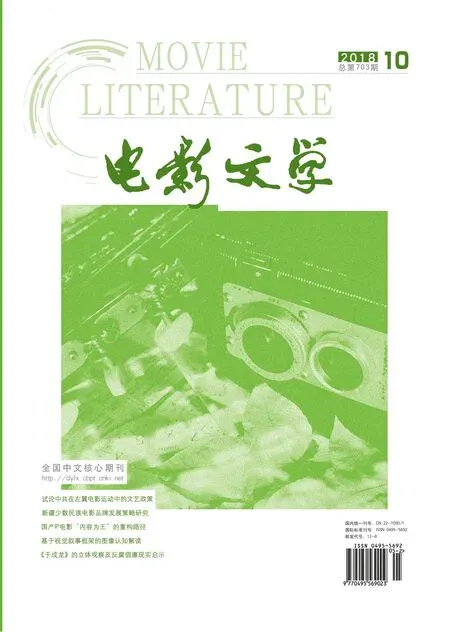試論中共在左翼電影運動中的文藝政策
金 虎 金宜鴻
(1.湖北美術學院 動畫學院,湖北 武漢 430205;2.武漢紡織大學 傳媒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3)
一、引 言
左翼電影運動是指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團結電影界左翼進步人士為創作主體,以國統區上海為中心,以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化、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電影革新運動。早期關于左翼電影運動的研究多從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展開,近來的研究又多從文化學和藝術學的維度介入。本文不揣冒昧,主要試圖在政治學與藝術學的領域深耕細作,探討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30年代左翼電影運動中的政策,特別是文藝政策,及其對中國電影發展的影響。愿拙文能拋磚引玉,就有道而正焉。
所謂政策,“即是政治策略,用規范的術語講,可以說是政策主體為解決一定的政策問題所采取的整治措施,主要體現為政策條文以及政策主體的有關規劃、設計和體制運作等,一般用來統一政策主體和規范政策對象的思想行為,調控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實現政策主體的政策目標”。這里的政策主體主要是社會群體的政治代表,即政黨或國家。其中的政黨既可以是全國性的執政黨,也可以是地方性的執政黨,還可以是在野黨或革命黨。顯然,當時同國民黨尖銳對立、擁有割據政權和軍隊的革命黨——中國共產黨也屬于政策主體,具有制定政策的功能。而文藝政策,既是一般意義上的政策,又是關于文藝這一特殊領域的政策,具有文藝領域的特殊性,是政策主體利益在文藝領域的具體體現,與政策主體所希望的利益協調和行為規范有關。
二、歷史背景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后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一時間,神州大地籠罩在腥風血雨之中。國民黨表面上仍標榜自己是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祭出反帝反封建的旗號,但實際上淪為一個由代表地主階級、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反動集團所控制的政黨。在其獨裁統治下,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并沒有改變,廣大人民群眾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沒有被白色恐怖嚇到,開始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并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走上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后,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猖獗進攻,國民黨反動派卻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繼續大肆圍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區和紅軍。這種倒行逆施激起了廣大民眾和愛國人士的極大憤慨和強烈不滿。作為黨領導下的左翼文化運動一部分的左翼電影運動,正是在這種大歷史背景下發生的。
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政治軍事領域同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你死我活的戰斗,而且在文化藝術領域也進行了如火如荼的斗爭。在當時白色恐怖統治下,國統區幾乎所有公開合法的新聞傳播出版媒介都被國民黨把持,相對于軍事政治領域的刀光劍影,文藝領域卻有相對的自由。左翼文化運動及電影運動開展之初,國民黨當局對意識形態和文藝作品查禁尚不嚴格,加之共產黨人巧妙地利用國民黨與己抽象相似但具體不同的某些政治理念與口號,左翼文藝作品得以順利流布,左翼思想和主張也得到傳播。鑒于文藝這一武器威力大效果佳,黨占領這個宣傳陣地,奪取意識形態高地,努力擴大自身影響,贏得廣大民眾的理解和支持是必然的選擇。恰如毛澤東在談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歷史特點時所指出的:“這一時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圍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時期。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
毋庸置疑,蘇聯左翼文藝也對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及電影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蘇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和左翼文學運動的發祥地和指揮中心是中國革命和左翼文學運動重要的理論來源地。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可以說,蘇聯文壇的每一次論爭,蘇聯文學理論的每一步發展變化都通過翻譯的渠道及時波及中國,并產生重大的影響,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發展過程與蘇共的文藝政策、文藝理論的變化息息相關。”中國電影也不例外。當時一大批左翼文化人如瞿秋白、王塵無和田漢等都積極學習譯介蘇聯電影理論,特別是電影武器論,如革命導師列寧“一切藝術之中,對于我們最重要的是電影”的指示,盧那察爾斯基“電影那是科學的宣傳的最有威力的武器,它是最強力的——直接想象與振動情感的煽動的東西”的觀點,聯共(布)第12—13次代表大會的有關精神:“電影必須經黨之手,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的啟蒙及煽動的有力的武器。”
黨領導的“八大聯”中,“左聯”無疑是影響最大的組織。從某種意義而言,電影小組是“左聯”在電影領域中的拓延,或者說是電影版的“左聯”。關于黨向電影界進軍的提議,當時黨內有不少反對意見,原因是利用資本家辦的電影來宣傳黨的思想與主張難度非常大,電影界風氣差,名聲壞,魚龍混雜,擔心年輕同志被帶壞,且黨內也缺乏電影方面的相關人才。考慮到電影的重要性,當時黨主管文化工作的瞿秋白高瞻遠矚,思考再三,謹慎地同意了阿英和夏衍等人的請求,盡管沒有抱過大的希望。1933年3月,中共電影小組在上海成立,成員是夏衍、阿英、石凌鶴、司徒慧敏和王塵無,其中夏衍任組長。就組織性質而言,黨領導的電影小組明顯區別于“左聯”“劇聯”和“社聯”等其他左翼文化聯盟的是,她完全由中共黨員組成,是黨領導左翼電影運動的工作班子,相當于左翼文化組織中的黨組織;而其他左翼文化組織除了共產黨人,還有大量其他左翼進步文化人。在組織結構方面,黨的電影小組直屬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領導;而其他左翼文化組織除了接受中央文委領導,還接受中央文委下面的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的領導。短小精悍的電影小組在推動左翼電影運動時,充分利用和組建了其他電影組織或與電影相關的組織,如“劇聯”“影評人小組”、中國電影家協會以及蘇聯之友音樂組。電影小組除了滲透到明星、藝華等電影公司去曲線工作,甚至直接掌控電通電影制片公司來推動黨領導下的左翼電影事業。
三、政策內容
中國共產黨在左翼電影運動中的政策是通過其對電影小組的指示,電影小組的綱領、決議,以及開展的各種斗爭活動如制片、影評和文章等體現出來的。黨在左翼電影運動中的政策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反帝反封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左翼文化運動的基本目標就是反帝反封建,作為其中一部分的左翼電影運動也必然是如此。先進的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出發,科學地判斷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最大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當時的革命任務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而國民黨則認為中國當時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封建社會,但帝國主義的侵略主要來自不平等條約,封建性主要是士大夫階級的封建勢力。他們主張中國必須發展國家資本和社會資本,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階級斗爭,主張階級間的協調和融合。盡管國共革命理念相互捍格,勢不兩立,但在反帝反封建這個問題上還是有近似或重疊之處的,這也為中共在左翼電影運動中推行反帝反封建的路線披上了某種合法的外衣。
中共電影小組的骨干王塵無指出,中國屬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前革命的主要任務即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電影領域,以美國好萊塢為首的外國電影對中國進行了經濟和文化侵略。他認為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后,中國電影的轉變突出地表現在“反帝和反封建”。接著,他對“目前中國反帝和反封建的電影所應該抓取的題材”做了更為具體的指示:“第一,是反宗教的。……要反帝,要反封建,非根本打倒宗教不可。”“第二,反地主高利貸者。”“第三,反軍閥戰爭苛捐雜稅。”“第四,反帝戰爭、反帝運動的史實。”“第五,反對帝國主義走狗的故事。”“第六,災荒的實際。……實際上,還是人禍而非‘天災’。”“當然反帝反封建的題材,一定不止以上幾項。”“只要電影制作者能夠把握住前進的觀點,他就隨時隨地能夠找到反帝反封建的題材。”
第二,反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肩負著消滅階級壓迫和實現民族獨立的雙重使命。中國共產黨代表著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是其重要使命。1927年國民黨右派發動反革命政變之際,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附和甚至參與過蔣汪的行動。因此,在大革命失敗后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打倒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是中共革命斗爭的重要內容,而黨領導下的左翼電影運動反對資本主義也是順理成章之事。事實上,國民黨對資本主義態度有些曖昧,它主張發展國家資本和社會資本,但國家資本是優先于民族資本的,私人資本最終是要受到節制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某些民族資產階級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國民黨壓制的,但它們同時又反對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這種復雜的局面為左翼電影運動的反資本主義主張多少提供了些討價還價的余地。
在中共電影小組的影響下,非中共黨員的鄭正秋,中國電影界的元老人物、明星公司三巨頭、資深編劇導演,也撰文發出了“三反主義”的喊聲。“當此全世界鬧著不景氣、失業問題尖銳化(蘇聯除外),而中國正在存亡絕續之交的時期,橫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越走越光明的生路,一條是越走越狹窄的死路。走生路是向時代前進的,走死路是背時代后退的,電影負著時代前驅的責任,當然不該再開倒車。我希望中國電影界叫出‘三反主義’的口號來,做一個共同前進的目標,替中國電影開辟一條生路,也就是替大眾開辟一條生路。什么叫作‘三反主義’呢?就是——反帝——反資——反封建。”事實上,鄭正秋就是中共電影小組領導或影響下的中國電影文化協會的發起人、執委兼總務部部長。一個非共產黨員的社會名流都能噌吰發聲高呼反資本主義,何況赤色的中共黨員呢?
第三,大眾化傾向。大眾化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在左翼文化運動中關注的重大問題,也是其文化政策的重要內容。大眾化問題的實質就是處理文化文藝與廣大民眾關系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代表著廣大工農群眾的利益,在廣大群眾中普及先進的文化知識,宣介傳播革命思想,是其革命斗爭的重要內容。
王塵無也大力宣揚電影的大眾化。他認為,中國電影“跟不上時代”的問題癥結就在于“是因為中國電影始終奠基在少數人身上而忽略了大眾,而時代卻是大眾的時代”。他提出要大量拍攝電影新聞片、電影都市片,擴大露天電影運動。電影新聞片能反映時代的需要,如十九路軍浴血抗日的電影新聞片,必然會像報告文學成為普羅文學主潮那樣成為左翼電影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電影的表現地域不止于都市,但電影與都市有著親和性。電影應該重點表現都市的底層生活,表現城市的新生產力。“露天電影就相當于壁報了”“露天電影運動是電影大眾化的一條正確的路線”。他還強調電影內容的“實感”,認為“排山倒海的革命勢力、澎湃奔騰的反帝運動和空前大水災后五千萬災民的流離蕩折,以及在封建意識、資本主義壓迫下所發生的種種慘劇”都是電影大眾化的重要內容。“到社會中找題材,到大眾中找人才,這是中國電影的唯一的出路。”“電影的內容,非盡量地引用大眾的真生活,拿大眾每天接觸的人物做主角不可。至于形式上,也應該非常明快地展開,多動作,少對白,千萬不要運用一切倒敘回憶等只有知識分子,或則看慣電影的人,才懂得的手法,就是暗示,也應該以大家每人看懂為限。象征的手法,是不必要的。只有如此,反帝反封建的影片,才能為大眾所愛好和了解。”而“短片的提倡”是因為充分考慮到了工人大眾們的工作生活特點,他們承擔著長時間的繁重工作,無暇觀看放映時間較長的長片。
第四,統一戰線。毛澤東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相對于左翼文化運動中的其他組織較為嚴重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左”傾錯誤,左翼電影運動在統一戰線方面成績相對較為突出,為中共在文化領域的統戰工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中共電影小組成員當時并不知道統一戰線這個名稱,但他們知道不得不搞聯合戰線。事實上,中共電影小組或多或少還是帶有“左”傾教條主義思想的,但瞿秋白提前就為他們打了預防針:“在目前的情況下,不可能拍出我們想拍的影片,但應于條件許可時,在資本家拍的影片中加一點進步的、愛國的內容,還要團結一批愛國的電影工作者。”當時復雜嚴峻的斗爭形勢也迫使電影小組不得不放棄那種不合時宜的“左”傾做法,轉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他們不僅要同電影公司老板、導演、編劇、演員甚至是國民黨電檢人員打交道,還要考慮到資金壓力、市場需求和觀眾喜好等。誠如夏衍所言:“而電影小組,參加大型電影公司工作,要團結導演、演員,甚至老板也要團結。在當時完全是中間派或舊藝人,不可能搞關門主義的。”電影小組的統戰對象包括電影公司老板、導演、編劇、演員等,還包括報刊媒體編輯記者,以至文學界、話劇界、音樂界和美術界的進步分子,總之是廣交朋友廣結善緣,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第五,具體策略。這里的具體策略主要是指中共電影小組在完成電影政治目標時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夏衍曾追憶過中共電影小組等左翼電影人的工作策略。“在黨的領導下,我們在十分困難和缺乏經驗的情況下,謹慎地進行了四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抓編劇部門的領導,自己寫劇本和幫助別的導演修改劇本,我們廣交朋友,給他們提意見,幫他們寫對話,慢慢地把幾個主要導演的編劇工作抓過來。第二是抓影評副刊,對電影觀眾進行思想工作,我們逐步地進入影評陣地,到1933年初,上海幾家主要報紙的電影副刊完全掌握在進步影評家的手里。第三是輸送新人,把文學界、話劇界、音樂界、美術界的進步分子介紹到電影公司去,逐漸地擴大進步力量,形成新的風氣。第四是大力介紹蘇聯電影,翻譯蘇聯電影大師們的著作,介紹蘇聯電影劇本,普多夫金的‘電影論’和蘇聯影片‘生路’的臺本,都是1933年前后出版的。”也就是說,第一要重視電影劇本創作,牢牢掌握住影片的主題和題材;第二要注重電影理論批評,占領輿論陣地,引導世道人心;第三要注意統戰工作,擴大進步力量,形成新的風氣;第四要積極宣傳蘇聯紅色文化。饒有意味的是,當年國民黨浙江省主席魯滌平向最高當局的密呈中歸納的中共利用電影進行宣傳的五大策略,與夏衍等左翼電影人日后總結的黨領導左翼電影運動的斗爭策略竟大致相同,這也從反面印證了中共電影小組當年的工作策略。
四、歷史評價
在中共文藝政策的正確引領和廣大進步影人的共同努力下,左翼電影運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其歷史成果遠遠超越了瞿秋白當年決策時的預期。根據吳海勇的統計,左翼電影運動中共產生了74部左翼電影,這是其最大的收獲。從政策效果上看,這些左翼電影在主題思想上大都反帝反封建反資本主義,暴露社會黑暗,揭示階級對立,鼓動階級斗爭和暴力反抗,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反帝救亡的影片主要是描寫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武裝進攻和經濟侵略,號召大家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如《中國海的怒潮》《肉搏》和《風云兒女》等描寫的是帝國主義的入侵和抗日救亡運動;《春蠶》《豐年》和《時勢英雄》等再現的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反封建的影片主要是表現土豪劣紳對廣大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尖銳的階級矛盾,以及封建惡俗迷信。如《鐵板紅淚錄》強烈暴露了地主土豪的罪惡,反映廣大農民的痛苦,尤其表現了農民奮起與地主武裝勢力對抗;《狂流》以大水災為背景,揭露了為富不仁的地主同廣大農民的矛盾;《鹽潮》和《到西北去》再現了農村地區尖銳的階級斗爭;而《飛絮》《飄零》和《凱歌》等再現的則是反封建迷信和婢女童養媳惡習。反資本主義的影片主要表現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以及他們之間的貧富懸殊和尖銳矛盾。如《都會的早晨》《上海二十四小時》和《姊妹花》等鞭撻了資產階級的腐朽沒落,表現了勞苦大眾的生存艱難與剛毅頑強,揭示了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一些左翼影片揭露社會黑暗,如《城市之夜》《漁光曲》《船家女》和《桃李劫》等,還有一些影片則是涉及婦女問題,如《三個摩登女性》《脂粉市場》和《女性的吶喊》等。事實上,這些左翼電影中的反帝反封反資等題材要素往往都互有交織,形象地揭示了廣大民眾的生活苦難及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對各強權階層和惡勢力予以無情抨擊,對被壓迫者、被剝削者寄予了無限同情,對黑暗的社會進行了泣血的控訴。
由于國民黨當局的大肆刪剪、電影市場的巨大壓力以及電影公司的諸多掣肘,相較于左翼文學、音樂和美術等其他左翼文藝,左翼電影顯得不那么“左”,與其說像社會主義革命性質的電影,還不如說似新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的影片。實際上,許多左翼電影被國民黨電檢當局刪剪得面目全非。在藝術手法上,左翼電影多平鋪直敘,通俗易懂,采用對比蒙太奇渲染階級對立和貧富差距,以人物說教、字幕和歌曲進行進步宣傳,以現實主義手法為主,但同時又不得不以象征隱喻手法以應對審查。當時軟性電影論者以探討電影藝術為借口對左翼電影進行了瘋狂的進攻,嗤點左翼電影只偏重思想內容而忽視藝術本身,其“紅色素,看看像是良血,其實是癆病患者的左肺陳血”。左翼影評是“被左翼文總劇聯當作執行政治的策略的主要路線使用著”。從純藝術的角度看,軟性電影論者的攻訐不無道理,但隱藏其后的政治文化立場卻是對左翼電影進步性的徹底否定。司徒慧敏曾對黨的文藝政策及左翼電影進行過反思,他認為黨的反帝反封反資及統一戰線的文藝政策無疑是正確的,但仍然存在“左”傾的錯誤,如有意將蘇聯國旗攝入影片,認為沒有明確在影片中反對國民黨就是投降等,這招致后來國民黨當局的瘋狂彈壓,造成左翼電影一度陷入低谷。某些左翼電影完全為政治服務,從主題出發,缺乏藝術性,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缺點明顯,鏡頭拖沓冗長,表演有舞臺腔痕跡,并有迎合小市民的傾向,影響至今。總的來說,黨在左翼電影運動中的政策是成功的,其目標基本達到,并為后來的斗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如統一戰線、題材決定論和理論批評等。如果左翼電影更加注重一下藝術雕琢,其藝術和宣傳效果或許會更好。
當然,考慮到當時的背景,中共電影小組是戴著鐐銬在跳舞,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夏衍所總結的那樣,“總體來看30年代的電影有這么五個特點,也可以說是五個弱點。一是在白色恐怖下搞起來的;二是黨在“左”傾路線領導下,我們都受到“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三是我們的起點很低,沒有一個專業隊伍;四是我們在資本家公司里進行創作主動權很小;五是我們都還年輕,都是外行。這五個客觀條件實際上就是時代限制、社會限制和個人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