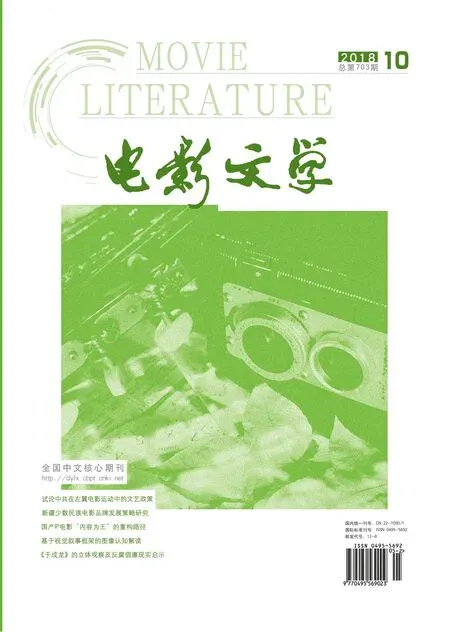開放空間中數字影像藝術的新美學敘事
彭 偉
(常州工學院,江蘇 常州 213022)
“新美學”概念最早由英國藝術家詹姆斯·布里奇提出,指物理世界中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的視覺語言的日益增長,以及數字虛擬世界和現實物理世界彼此作用產生的相關美學現象與問題,人與機、物理與虛擬是新美學概念的最核心要素。而開放空間中的數字媒體影像藝術,正是將“物理現實空間”與“虛擬數字影像”相互關聯形成新美學敘事的有效范本。本文研究范圍并不涉及商業影像,而是聚焦于開放空間中數字媒體影像的藝術創作及活動。
一、碰撞的可視化
可視化是數字時代新美學概念的重要特征之一,所有的虛擬信息都以圖形影像的方式變得具體可見,二維碼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產物。由于數字可視化是多元信息的可視化分解與集合,這使其開始具有自己的獨特魅力。而當數字可視化與物理空間中的傳統經典相遇時,科技、文化與審美的碰撞便被激發出來,分解和重構成另一種具有新美學特征的可視化結果。
早在20世紀60年代,第一代影像藝術大師白南準就開始將東西方文化經典與虛擬的影像融合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中。1963年的《禪之于電視》、1964年的《禪之于電影》等作品,都是將禪學思想與影像媒體相結合,反藝術、反商業化的思想,凸顯東方文化精神下的視覺表征。自白南準之后,藝術家們開始利用數字媒體技術,使傳統文化與現代數字影像產生碰撞,比爾·維奧拉就是其中之一。維奧拉的創作深受中世紀傳統宗教繪畫的影響,對于他而言,無論是宗教繪畫中耶穌那哀傷的神情,還是東方神像對情感的內斂表達,以及畫中所釋放的一股平和或波動的情緒,都讓他產生戚戚情懷。維奧拉投射在保羅蓋迪博物館外墻上的《驚愕五重奏》,其創作靈感就來自收藏的文藝復興時期北歐畫家希羅尼穆斯·波希的作品《加冕荊冠》。維奧拉充分利用數字影像技術手段,將影像進行了千倍慢速播放,營造出一種相互依偎卻又無限悲傷的氛圍,成功地在公共空間中實現了新美學的敘事表現。
隨著時間的推移,藝術家們對于數字媒體技術的運用也更加具有創造力,與之對應的文化和視覺碰撞結果也更加強烈。2011年,埃米爾·巴拉達蘭在羅浮宮內利用智能手機和增強現實技術,將世界名畫《蒙娜麗莎》與其預先制作好的52秒視頻影像結合起來,完成了作品《法式蒙娜麗莎》的創作。巴拉達蘭認為,達·芬奇筆下的《蒙娜麗莎》原本是一名意大利貴婦,但如今卻成為法國的文化標志。在巴拉達蘭的增強現實視頻中,隨手撥弄身上紅藍白三色頭巾的蒙娜麗莎,顯得波瀾不驚。頭巾源于穆斯林禮儀,而在不同文化里卻有著不同的解讀,比如“遮羞”“自由”“壓迫”等,而對于當代法國來說,頭巾卻成了“法國性”的避雷針,成了所謂世俗國家理想的視覺威脅。藝術家認為法國應當改變自己對于自我文化形象靜態的認知,并認為增強現實技術一方面完成了自我藝術創作實踐,也改變或影響了公眾對于空間關系和所屬領域的傳統認知,因為物理空間在藝術創作中并沒有發生任何改變。藝術家同樣用這次創作活動,對博物館展示方式和特權提出了挑戰。
除了經典藝術品,開放空間中的數字媒體影像藝術往往會與充滿文化特色的視覺要素結合展示。2016年,杰弗里·肖在印度孟買的賈特拉帕蒂·希瓦吉博物館創作了大型數字影像裝置作品《看看孟買》。藝術家在建筑頂部安裝了一塊直徑達6米的圓形屏幕,并在上面播放各類孟買傳統建筑頂部的視頻影像。屏幕下方設有環形沙發,公眾可以躺在沙發上觀看。當平日里不會抬頭仰望的各類建筑穹頂以高清的影像出現在公眾眼前時,人們不禁對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傳統建筑和傳統文化產生了新的審視。
事實上,回看當代藝術發展過程可見,新審美誕生并非與傳統審美和傳統經典的決裂,反而來自一次次新舊要素間的激烈碰撞。加里·希爾和約瑟夫·博伊斯都是雕塑家出身,白南準和約翰·凱奇是從古典音樂開始的,而在他們的作品中,也充分體現出這些藝術形式對他們后來作品創作的深刻影響。而當數字媒體技術與數字審美融入其中后,前衛與經典、技術與藝術、瞬間與永恒、虛擬與現實等碰撞要素,更為新美學敘事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二、在場的即時感
新美學是基于實時數據的生成和分配,基于互聯網的溝通渠道和思想交流而誕生和發展的。而互聯網技術的高度發展,同樣讓開放空間中的數字影像藝術創作呈現出一種在場的即時感,這是傳統藝術作品和創作不易實現,甚至難以想象的,因此也形成了數字時代獨特的新美學敘事特征。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凱特·加洛維和謝莉·拉比諾維茨創作的《空間中的洞》,就試圖通過放置在街頭窗口里的視頻會議裝置,用衛星轉播技術連接洛杉磯和紐約的觀眾。就當時的技術條件而言,這個案例絕對是開放空間中影像藝術的跨媒體創作典范。一方面,藝術家將視頻藝術的影像內容從錄像轉為實時畫面;另一方面,他們嘗試將公共空間重新設定為開放的溝通交流場所,以及感知城市居住空間差異性的所在。
《空間中的洞》所實現的異地溝通和在場體驗,在今天看來已屬日常生活常態,網絡為視頻影像藝術創作提供了廣闊的發布展示平臺,成為積極參與視頻藝術創作的媒介載體。2004年,岡瑟·塞利查通過互聯網,為開放空間影像藝術項目“第59分鐘”創作一部名為《害怕紅綠藍的人》的作品。塞利查在網上邀請網友用數字成像的紅、綠、藍三原色創作動畫,以此向抽象表現主義大師巴尼特·紐曼的作品致敬。由藝術家彼得·哈雷、卡爾·古德曼等人組成的明星評審團,在網友創作的600個動畫中選擇三個,并最終在紐約時代廣場播放。此作品源于塞利查,同時又是諸多藝術家共同參與選作、評判,廣大網民親身參與創作的作品。
互聯網的普及更進一步提升了這種即時在場的參與感,2010年,古根海姆博物館與全球最大的視頻網站YouTube合作,舉辦了一次名為“YouTube Play”的視頻藝術雙年展活動。YouTube希望通過該活動展示優秀的上傳視頻藝術作品,而博物館則將此次活動視作大眾文化產品的經典化過程。這次活動同樣制造了一個公眾將自己的作品在專業的藝術機構展示的機會,因為如果沒有博物館的認可,想在古根海姆這樣的博物館展示自己的作品并非易事。博物館將這些視頻在晚間于建筑表面的環形屏幕上播放,這樣就讓作品面向公共空間,展示在了公眾面前。以古根海姆博物館作為播放地點,一方面能夠大大地提升作品的被關注度;另一方面YouTube上同步的網絡播放,則能夠通過觀影人數、喜歡或不喜歡的選項和評論留言等交互內容,獲得最及時的信息反饋。與此同時,博物館還根據觀影需求,開放了相應的介紹作品的移動端手機app應用,讓觀眾通過手機就能完成與作品的互動或進一步了解作品信息。這次活動是現實空間與網絡空間多個平臺間的資源整合,也是視頻藝術走入開放空間的一次有趣的跨界實驗。
數字媒體技術帶來的在場體驗具有即時性,而提供在場的體驗方式則更為多樣,其發展方向無疑是更深度的參與感與更多層次的參與可能性。新美學視野下的數字化藝術創作早已真正打破了藝術家與公眾、藝術品與藝術創作行為之間的關系,這同樣與當代藝術試圖打破生活于藝術藩籬的初衷相符。
三、泛化的新影像
新美學并非對于數字媒體技術的一味推崇,反而著力研究其中的所謂“誤差美”。因為數字和機器本身的誤差都讓其更具有變化和可能性,更具有人性化的特征和要素也被新美學研究者稱為“缺陷本體論”。而這種誤差往往在虛擬對象和物理對象產生關系時隨機出現,這些誤差反而會對人們的審美體驗和視覺認知產生重要的影響。在開放空間中,虛擬影像與物理空間以及物理空間中的人和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了有趣的誤差,這些誤差則帶來了全新的新美學敘事表達,影像自身則被泛化。
數字技術的發展讓視頻圖像的獲取不再需要依靠攝像設備,開放空間中播放的許多影像藝術作品都是以數字動畫的形式出現的。2001年,紐約時代廣場上就播放了一段威廉·肯特里奇創作的1分鐘視頻藝術作品——《影子前行》。該作品用印紙板制作的褐色剪影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在這群剪影形象的隊列中,有駝背和瘸子,帶著他們的財物、牲口、家具、麻袋、馬車,從屏幕左側向右移動,仿佛在外流浪的人群。作品描寫的是因種族隔離而遠離故土的人們,他們長期顛沛流離,長期在暴力與辛苦的勞作中掙扎。在時代廣場上看到這些剪影的人們,不禁會為這看似簡單的形象所震撼,并讓當代漂泊勞碌的人們感同身受。
如果說肯特里奇的作品還需要運用動畫技術去制作實現,那么有的數字影像甚至不需要藝術家自己去創作。英國紐卡斯爾大學的藝術家們利用建筑投影的手段,將校園內的能量變化用光譜動態影像的方式投射在校內建筑立面上。不斷變化著的形狀和色塊看起來賞心悅目,但實際上流動的顏色代表了校內熱量消耗數據變化的高低起伏。這種能量數據可見的方式不但直觀有趣,也同時觸發了公眾對于能源問題的關注,雖然藝術家沒有動手去制作視頻內容,卻同樣得到了視頻表現和觀念主題俱佳的開放空間數字影像藝術作品。
而美國藝術家杰森·艾平科更是用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實現了自己在開放空間中的數字影像藝術介入。杰森·艾平科用泡沫芯和擴散材料制作出了一種被其稱為“像素繪圖”的發光盒子。他將這些盒子套在紐約地鐵入口處的大型商業廣告屏幕上,屏幕上的商業廣告似乎被像素化了,立刻變成了不斷變化著的色塊。艾平科對自己的創作也非常滿意,“高清的商業廣告視頻被變成了45個閃爍的、顏色變幻的方塊。我在這些跨國公司的幫助下,創造一件藝術作品,而他們甚至都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杰森·艾平科用這樣的方式得到了自己的數字影像,更重要的是,這些運動著的簡單色塊反而在精美的商業影像叢林中成功地脫穎而出。
當影像開始出現泛化后,藝術創作逐漸形成了脫離技術限制的新形態,這種泛化來自虛擬數字影像與物理空間和物品的融合,不但再次印證了新美學關于虛擬與物理作為核心要素的觀點,同時更拓展了藝術創作的維度。
四、結 語
數字人文學者大衛·貝瑞和詹姆斯·布里奇等人都曾多次提到,新美學不是批判,而是一種探索;不是運動變革,而是關于正在發生變化的時代的一個視角。由上述關于開放空間中數字影像藝術的新美學敘事研究可見,一方面,在新美學概念中虛擬與物理絕不是對抗關系,而是融合協作的未來重要發展線索;另一方面,我們不僅要了解數字技術如何實現了審美革新,更應該關注我們是如何理解和看待這種變化的。